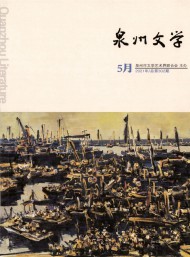文学批评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8 21:09:34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文学批评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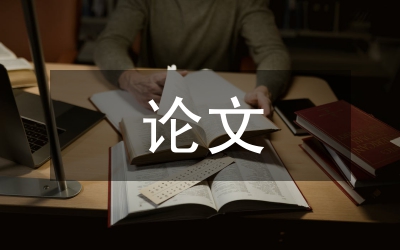
篇1
“新批评”作为最先进的西方文论之一传入中国,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语言意识的转变。瑞恰慈在他的文学批评思想中,对语言与思想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对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进行了划分。他认为,思想与语言之间是直接的因果关系,思想是因,语言是果,语言是表达思想的符号。而语言又可分为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文学语言是用以唤起某种情感的,是情感语言;科学语言是用以指称某个对象的,是符号语言。瑞恰慈的语言观使中国学者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对语言意识认识的轻慢。中国古代文论早有言意之辩,文学语言是文学的载体还是本体成为言意之辩的核心话题。中国传统载体论语言观认为,语言是文学的载体,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是外在的媒介,本身没有独立价值。古典诗学的儒道佛三家,虽信奉的本体论各异,语言观却惊人地一致,他们都认为语言只是文学的载体。儒家的“诗言志”、孔子的“辞达”说,都认为文学语言是言志、载道的工具,是文学的载体。庄子也提出,载意之言与捉兔之网、捕鱼之笱性质相同,作用一致,语言无非是获取意义的手段和工具,意义才是目的。一旦获取意义,达到目的,作为工具的语言便毫无用处,可以被忘却,这就是所谓的“得意而忘言”。佛家禅宗的布道方式是“拈花微笑”“当头棒喝”,其要旨是避免拘执于语言而迷失本源,因此只有废弃语言才能悟道。这种对言意关系的认知深刻地影响了几千年来中国文学批评的语言意识,在文学批评中,载体论的语言观是反映论和表现论的基础。反映论认为,文学语言是反映社会现实的工具。表现论认为,文学语言是表现作家和人物内心的载体,语言一旦完成了反映社会现实和表现人物内心的任务,就可以被遗忘了。这种批评方式一直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主流,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只关注语言的载体性能,而没有认识到文学语言本身的价值,中国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便是在语言的背后去寻找文学作品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审美特性”了。中国传统文论中语言意识的薄弱,给中西文化交流带来重重阻碍,也使得人们的思想交锋陷入困境。“西学东渐”之前的中国文论多是思想意识的辩论,而较少关注于语言意识的准确表达。“新批评”的引入,促使中国学者重新思考思想与语言的关系,更为重视语言在文学中的重要作用,李安宅便是其中之一。在瑞恰慈的影响下,李安宅开始关注语言与思想的关系,深入探索文学语言的意义,开始实现了语言意识的最初自觉。他在《意义学》一书中指出:“凡事都是先有自觉,然后才有系统的研究,普遍的进步。涌现于现代思潮的有自我意识,社会意识,种族意识,性的意识等,正不妨添上一个‘字的意识’或‘语言意识’。”李安宅意识到了语言意识长久的沉默状态,主张唤起文学研究的语言意识:“研究语言、分析语言、改良语言,使它成为我们的随手工具,没有人为物役的毛病,是我们的历史使命。”[2]11由此可见,对于语言意识的重新认识和呼唤语言的自觉,成了李安宅一代学者的历史使命。这种使命感警示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对语言意识的轻慢与回避,也进一步宣扬了语言意识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建设的必要性。瑞恰慈也热情地回应了李安宅关于语言意识自觉的呼唤。瑞恰慈在华执教期间,体验到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对于“科学”的热情。但他认为,“科学”的实质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更为重要的是采用一种以语言意识为核心的思维方式,“中国人需要科学,并不像现在许多人觉得那样,以为科学是什么把戏,实在因为科学是一种思想的途径”。他认识到,中西语言观念是存在差异的,“在西洋,则对于语言作用的见解,不管是公开地或是秘密地,都有支配我们底思想的力量,支配了两千多年”。中国的情况则相反,“中国的历史里面,对于语言的结构与种类,不同的字眼所有的种类不同的作用,都没有发展成固定的理论”。瑞恰慈指出中西语言观念的差异源于思想观念的不同,西方在语言意识的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科学精神的完善推动了科学的进步,语言意识是科学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中国必须关注语言与思想的关系,关注语言研究,强化语言意识,才能构建现代科学精神,才能真正地引进西方的科学。“新批评”的语言观是西方众多语言理论中的一种,但是对于中国文学批评界来说,“新批评”采取理性的态度考察思想脉络,研究语言内涵,建构科学认知方式,这无疑是唤醒“语言自觉”的第一声春雷,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一种有益补充。当然,“五四”以后中国文学批评的“语言的自觉”还是比较模糊的,由于“新批评”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异质性,使得“新批评”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受到限制。再加上特殊的政治历史条件,内有国内战争,外有俄国十月革命,“五四”时期对西方文论的接受由“先进”的欧洲文论转向了苏俄文论,在之后半个世纪的时间内,苏俄文论一直在中国文论中占据主流地位。可是毋容置疑的是,中国文学批评借鉴“新批评”所唤起的“语言的自觉”,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转向,是文学走向自由的必由之路,语言意识的觉醒也为文学回到文学本身,表现更高的生存意向和更复杂的精神生活提供了可能,这是从语言载体论转向语言本体论的必经之途。对于文学语言本体的重视也就意味着对文学所表达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内容的刻意疏离,这为中国文学批评铺陈了一条不同于社会政治历史传统的诗性超越之路。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界掀起了“文学本体论”大讨论,这一文学批评盛事进一步证实了文学语言本体论建构的重要性和必然性。
二、本体建构:语言转向条件下文学本体的倡扬
如果说“五四”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借鉴“新批评”的语言观,从而引发了对于传统载体论语言观的反思,那么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本体论”大讨论则实现了本体论语言观的建构。20世纪80年代,“新批评”思想卷土重来,文学语言形式的研究仍是文学批评的焦点。“新批评”倡导对文本进行语义分析,主张文本细读,从而使文学批评回到文学语言形式本身。这一理论的重申大大拓宽了中国文学批评家的理论视野,新时期的批评家反思传统的载体论语言观,开始从本体论的高度定位文学语言,不仅表现在批评实践上,还表现在具体的文学创作实践中,从而掀起了“语言本体论”的热潮。从“新批评”与中国文学批评本体论语言观建构的关系来看,“文学本体论”的理论来源于“新批评”。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陆续地翻译、介绍“新批评”的相关理论和批评家。到了20世纪80年代,对于“新批评”的翻译、介绍与研究呈现出系统化、规模化态势,其中杨周翰、赵毅衡等是重要代表。他们撰书立著和发表重要论文,介绍和传播“新批评”理论。赵毅衡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当时国内研究“新批评”的扛鼎之作《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对“新批评”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另外,还陆续出现一批“新批评”的译介,如刘象愚翻译的《文学理论》、赵毅衡编译的《“新批评”文集》等,构建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界“新批评”的知识谱系。后来有评论家称:“英美‘新批评’派的文学本体论是我国文学理论最近几年来出现的文学本体论的来源之一,国内的文学本体论的呼唤者也自觉地向‘新批评’派寻觅理论武器。”[4]从此处可以得知,中国文学批评呼唤语言本体论,与“新批评”的文学本体论有极大的关联。“新批评”的价值,在于为中国文学批评回归本体提供了理论资源,但是,它不是通过自身的理论体系来证明的,而是通过对统治中国已久的反映论的批判来实现的。其次,“新批评”本体论语言观是对“反映论”的纠偏,是对载体论语言观的颠覆。自“五四”以来,一直统治中国文学批评界的是反映论的文艺观。“反映论”与“新批评”的文学本体论最为抵牾,“文艺观是反映论的,这被认为与新批评的本体论主张截然对立”[5]69。在此基础上,“新批评”作为一种“清道夫”式的文论,主要的使命是扰乱学界的既定秩序,以引起人们对传统反映论文艺观的怀疑,对载体论语言观的批判。因此,“新批评”的存在意义是通过对“反映论”一统天下的局面的批判,打破文学批评界的既定秩序,使人们对权威和传统产生怀疑,为中西文论的融合开拓空间。故而,“新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界的重要价值:一方面,凭借“文学本体论”阐释文学语言在文学中的本体地位;另一方面,通过批判“反映论”,建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新秩序。基于以上两个原因,在“新批评”的影响下,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文学批评批判了载体论的语言观,转而关注文学语言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建构本体论的语言观。在进行“文学本体论”大讨论时,对于文学的本体究竟是什么这个核心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大体经过了由“作品本体论”到“语言本体论”的转变。“作品本体论”以作品为核心,其主要理论内涵是文学活动以作品为重,文学批评应面对作品本身,深入作品内部进行研究,才可窥见文学的本质,文学研究与作者、世界、读者等无关。持“作品本体论”的批评家主要有陈晓明、胡经之等。“作品本体论”的观念主要来自“新批评”的韦勒克(RenéWellek)。由于受西方现代语言学派的影响,不难看出“作品本体论”中包含着“语言本体论”的影子。“语言本体论”的一派则以语言为旨归,高扬文学语言的本体价值。1985年底,黄子平撰文《得意莫忘言》,提出了须重视文学语言本身的价值,“文学作品以其独特的语言结构提醒我们:它自身的价值。不要到语言的‘后面’去寻找本来就存在于语言之中的线索。”[6]这既是对文学语言的本体意义的强调,也是对传统的语言载体论、工具论的有力批判。李劼也在他的《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意味》一文中表达了相同的思想:“所谓文学,在其本体意义上,首先是文学语言的创作,然后才可能带来其他别的什么。由于文学语言之于文学的这种本质性,形式结构的构成也就具有了本体性的意义。”[7]“语言本体论”将把语言与形式合二为一,形式是内容化了的形式,内容溶解在形式之中,语言建构了文学的本质,建构了人类世界,批判了语言意识薄弱的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在文学创作界,20世纪80年代的作家们也开始秉持本体论的语言观。语言在文学创作中不再是反映现实的工具、承载内容的载体。语言就是文学本身,是文学的本体,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语言与内容相互依存、融为一体,文学创作的生命就是语言革新。在“文学本体论”大讨论背景下涌现出的一大批作家表现出了对于语言形式创新的关注。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余华的先锋系列小说、于坚的诗歌,都醉心于语言的革新。他们以语言形式的创新为文学创作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空间。作家们不仅在创作实践中关注语言,而且在批评实践上也阐发了他们对语言意识的重视。汪曾祺提出:“中国作家现在很重视语言。不少作家充分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提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它是和内容(思想)同时存在,不可剥离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8]1从汪曾祺的这段话看来,语言于文学处于显要的地位,而当时创作界对语言开始充分地重视,其语言观念也开始发生转变。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批评界和文学创作界共同致力于语言意识的转变,文学语言观由语言载体论转向语言本体论,为文学语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打下了基础。“新批评”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与其说二十世纪是一个批评的时代,不如说二十世纪是一个以本体论批评为主调的时代”[9]。而西方各种文论在中国的“理论旅行”或多或少暗藏着“新批评”的潜流,“尽管在它之后,西方还涌现了诸如结构主义批评、原型批评、后结构主义批评等等批评流派,但这些批评流派在形式本体的意义上基本都是沿着‘新批评’奠定的研究方向向前发展”[9]。因而,“文学本体论”大讨论的意义在于,它确立了文学语言的本体地位,实现了从语言载体论到语言本体论的转向,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既有型态,促进了文学语言观念的全面变化,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新的语言范式的建立。但是,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本体论”大讨论只是一种理论倡导,给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文学研究的新途径,即从文学内部、文学形式来探讨文学,却未建构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无论是“作品本体论”还是“语言本体论”,都是文学研究的一种中介,旨在将已被割裂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连接起来。被“新批评”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在理论重构过程中,遮蔽了“新批评”自身的理论丰富性,“新批评”被后世所诟病的“文本”自足性、“文本细读”法等也渐渐地与“文学本体论”大讨论之后中国的理论氛围格格不入,故而注定了“新批评”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只是暂时的“亲密”。更有讽刺意味的是,“文学本体论”大讨论没有使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走向“本体论”,而是最终走向了“主体论”。
三、价值重建:后现代语境下价值判断的重建
篇2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伦理文化;文学伦理批评
20世纪是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大发展的世纪。受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影响,文学研究过多地局限于语言和文本现象,热衷于对形式、文体、技巧等实证、实用性的研究,而忽视了文学的道德教化功能。环境问题、社会问题乃至人类的精神问题的复杂多样化促使文学研究重新关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类自身的精神诉求。20世纪80年代,西方文学评论界开始逐渐由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的能力(内部研究)转移到注意研究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作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1]。20世纪90年代,作为生态批评支流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迅速成为西方文艺评论界的“新星”。
一、生态危机: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契机
现代工业的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早在19世纪已经引起人类的注意并开展形式多样的环保行动。20世纪50年代中叶,以“公害事件”为代表的环境问题,引起世人的更为广泛关注,人们意识到环境污染严重损害公众健康,并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从而爆发了一场新的社会运动——生态运动。生态主义者反思人类行为,质疑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至上论,揭示人类中心主义才是生存危机的根源。为探求人类的出路,生态主义围绕非人类的道德身份展开争论,形成形式多样的环境伦理。
生态女性主义是环境伦理中的最新发展,是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的结合。一百多年以来,女性主义经历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20年代的以要求平等的政治经济和受教育权利为特征的自由女性主义,和20世纪20—60年代的以争取女性社会文化身份为特征的激进女性主义的洗礼。在生态危机和环保运动的激励下,在妇女参与环保运动的实践基础上,生态女性主义于20世纪80年代在欧美蓬勃发展起来。它借助解构主义,深入挖掘当下生存危机根源——父权制的男性中心主义观并进行颠覆性批判,力图构建一种新的环境伦理文化,为人类的持续谋求出路。
二、新伦理文化的建构:生态女性主义的活力源泉
人类社会经历了从人类初始阶段对自然界的尊崇、恐惧、依附的生存意识(即自然伦理阶段),到对自然的改造而使自然环境从人类生存视野中逐渐隐退后的对社会利益的关注(即社会伦理阶段),再到现今环境问题带来生存危机而反思后的尊重、爱护自然,寻求人与其他万物平等依存(即环境伦理阶段)的伦理认知和革新过程。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伦理道德的修整重构过程。生态女性主义正是生态语境下伦理革新的表现形式之一。它广泛借鉴其他流派思想,特别是生态思想和传统女性主义思想,批判父权文化体制下的二元对立价值等级思维模式和工具理性主义传统,以颠覆西方主流的父权——男性中心主义伦理观,并形成一系列具有自身特点的伦理价值体系。
首先,它追求整体和谐和生命解放,反对压迫。对“各种形式的统治和压迫相互交织”[2]的认同是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基点。在肯定自然界独立的内在价值,赋予所有非人类(如动植物、河流、山川等)同等的道德地位,关注所有与自然——心理、性、人类和非人类——有关的统治同时,生态女性主义反对各种社会统治形式(种族、阶级、年龄歧视及军国主义、殖民主义等),将所有被父权文化贬为他者的边缘弱势群体如女性、黑色人种、同性恋、酷儿(queer)等视为盟友,认为没有自然的解放,没有其他边缘群体的解放,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从而将其伦理关照的对象扩大到最广阔的领域。
其次,它吸收生态批评的整体性观念,尊重差异,赞美多样化,认为差异、多样性是生态系统和谐稳定的保障。其多样性既包括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又包括人类个体的个性和社会生活风格及地方风俗的多样性等。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对物种的侵害控制,致使生物简化。现代商业社会的技术和竞争将人异化为失去生气和个性的生产机器。在技术和利益的驱使下,统一的文化观念和文化方式无孔不入,诱导现代人的拜物心理,泯灭人的个性,使社会生活风格“齐一化”,文化也因简化失去其多样性魅力。
第三,它呼吁建立一种基于互惠和责任原则而非统治原则的生态伦理观,强调感性如关爱、尊重和公正的伦理价值。生态女性主义关注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物的关联性,从女性与自然在生理、心理和体验上的关联出发,提出重新界定人类自我的身份,抛弃以人类——男性为中心的抽象独立自我的主人身份形象,代之以生态的关联自我[3]。生态女性主义认为,人类只有意识到自己与世界万物千丝万缕的联系,才能从根本上关注“他者”,以平等的道德权利持有者身份修正自己的不良行为和思维方式,还“他者”公正,尊重和关爱“他者”。唯如此,人类和自然才能和谐相处。
生态女性主义者不仅多角度解构父权制思想,还多层面建构新伦理文化。一些女性主义者以恢复对月亮、地球等的女神崇拜仪式来赞美女性与自然的联系,并用人类学家对史前期的母系社会的考古发现论证女性文化建构的可能。普鲁姆伍德提出重新阐释大地女神盖亚,认为认可地球的母亲身份有助于人类尊重和关爱地球及其上的所有存在物,有利于形成新的伦理道德观。一些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对基督教神学进行改造,把上帝理解为母亲或女性。温德尔把上帝称为我们的母亲,因为“上帝的父亲形象适用于父权制社会中的人格形成”[4]。沃伦根据IrisYoung对传统分配模式的社会公正性的剖析,探讨基于该分配模式的环境公正性,指出由于传统的分配模式是静态的物质倾向的,不重视社会进程中的社会关系,因而无法对生态群(如物种、数量、自然栖息地等)的状况给予足够关注,无法建构“生态的关联自我”,也不能充分重视并体现关爱和尊重的重要价值,只有非分配模式语境才是适合生态道德生长的土壤[5]。这些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伦理文化设想,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开拓了新空间。
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新视角
文学作品是现实生活的某种反映,是人类理解自己的生产劳动及世界的一种形式,是为满足人类道德情感或观念表达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富有特点和不可替代的道德思考形式”[6]。因而有人认为“真正的艺术和批评服务于一种道德目的”[7]。以反思人类思维方式、规范人类行为并以最终解决人类生存危机为己任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潮,其伦理特性必然从社会层面延伸到精神层面,从对现实社会中的道德现象的评价和规范及对其伦理根源挖掘延伸到文学批评领域,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它遵照生态女性主义伦理道德观念,将性别(女性)和自然结合起来探讨文学。它在关注人伦道德的同时注重弘扬生态伦理道德,成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新视角。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对文学与女性及自然环境关系的研究。大体而言,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透过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棱镜来阅读文学文本,使文学文本中那些以前忽视的要素凸现甚或更为显眼,促使文学批评家对文本的传统要素如风格、结构、修辞和叙述,形式和内容有新的发现,加强探讨文本中不同角色——人类与自然之间,文化与自然之间,不同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的人之间——的联系与差别,探讨影响人类与自然,人们相互之间关系的差异与联系的因素[8]7。在文学批评实践中,批评家必然会提出这样一些基本问题:自然和女性在这部作品中是如何再现的(是次等的、低级的、破坏性的、缺乏理性的还是美丽的、充满慈爱温情的、不可缺少的),自然和女性在作品中扮演着何种角色(是受贬抑的、受支配的、工具性的还是平等的、受尊重的、具有自身独立价值的),自然和女性之间的关联性是如何在作品中体现的,以及作品中表现的伦理价值观与生态智慧是否一致等。而一部具有生态女性主义意识的作品,往往符合如下标准:即是否体现整体的关联性;是否体现对男女、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整体和谐、多样而相互依存关系的追求;是否反映对两性之间、人与人之间以及人对自然的征服、支配、压迫和统治等问题的探讨;是否有助于重新认识人与其他万物的关系;是否有助于人类重返和重建与自然及其他存在物的和谐关系;是否有助于警醒世人,倡导生态智慧,唤起人们的生态意识等。
生态女性主义在从文化哲学领域切入文学批评的过程中,文学批评家和人文学者承担文学批评的责任,以发展一种文学批评体系来反映和促进生态女性主义运动的政治目的,这一责任是以文本阅读为基础的。首先,通过阅读各个时期的文学文本,揭示文学作品中反映的自然与女性的关联,探寻在文学领域中对女性对自然两种统治和压迫的历史文化根源。生态女性主义神学者对《圣经》进行对抗性阅读,批判它借上帝之口确立男性对女性和自然双重统治和奴役的地位而成为父权——男性中心思想的始作俑者。其次,通过重读文本,得出新的结论,以改变传统的文学史,重建文学经典。一方面,将被忽视的被埋没的体现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文本,尤其是女性文本重新评价,纳入经典之列,如一些寄情花草而被贬为闺阁之作的女性文本得到认可,曾被嘲讽为无病的美国女海洋生物学家卡逊的《寂静的春天》更是以其女性的细心观察和细腻描述被誉为文学、女性、自然三者完美结合的典范;另一方面,重新审视以往经典文本,颂扬体现整体关联的、洋溢着关怀同情、慈爱温情的作品;抨击体现父权中心的、工具理性的、扩张性的、弥漫着男性支配和控制欲望的作品,否定其经典地位。如:被奉为个人英雄主义经典的《鲁滨孙漂流记》体现崇尚权力、征服、统治和男性工具理性而被批判;而珍妮·斯梅雷的《千亩农田》、斯坦因贝克的《愤怒的葡萄》等,因其探索了科技在人类贪欲支配下给土地所造成的损失,以及人的身体、特别是女性的身体与土地的紧密联系,揭示了女性和自然受男性控制和征服的悲剧局面,体现了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在文学批评实践上,努力发掘该文类的写作特征,总结和建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从而修正传统文学的价值取向[9]。这一方面可以带领文学创作者认知、关照、表现社会生活、世俗人生,进行文学创作,深化文学的审美价值;另一方面引导读者的文学欣赏,通过发挥典型人物的启示作用和“揭丑”文学的警醒作用,影响人们的文学乃至文化“消费”观,改变人们行为方式,从而实现文学的社会教化功能。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并非否定所有其他形式的批评。它以新的批评尺度为文学伦理批评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它借助文学宣传生态女性主义,倡导生态智慧,强化环境意识;它不仅重新释义文本,还积极推动社会和人生的建构;它弘扬关爱、平等公正、联系依存的生态伦理观,不仅有利于促进建立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自然和谐关系,也有助于推进各“亚”文化群,如有色人种文学、黑人文学、少数族裔文学、流散文学(diasporicliterature)等从边缘走向被关注的中心,使人类听到不同的声音,从而最终建立“一个免除了有害物质和生态灾难威胁的社会……一个免除了压迫和毒害的社会,一个免除了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毒害的”[10])生态社会。
[参考文献]
[1]鲁枢元.生态文艺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371.
[2]Brown,Rachel.RightingEcofeministEthics:TheScopeandUseofMoralEntitlement[J].EnvironmentalEthics,2004(26):247-265.
[3]Gaard,Greta.EcofeminismandWilderness[J].EnvironmentalEthics,1997,(19):5-24.
[4]何怀宏.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M].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194.
[5]Warren,KarenJ.EnvironmentalJustice:SomeEcofeministWorriesaboutaDistributiveModel[J].EnvironmentalEthics,1999,(21):151-161.
[6]聂珍钊.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J].外国文学研究,2005,(1):8-11.
[7]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J].外国文学研究,2004,(5):16-20.
[8]Gaard,GretaMurphy,DPatrick.EcofeministLiteraryCriticism:Theory,Interpretation,Pedagogy[M].UrbanaandChicago: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1998:7.
篇3
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
体育学学术批评对象的界定独立建构体育学学术批评体系,其次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必须弄清什么是“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关于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问题,时下呈现出两种不同主张。第一种主张认为,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是体育学学术成果,即把体育学学术成果当作批评的对象,主要对体育学学术成果进行评判,持这种主张的人为数不少,也具有比较广泛的影响。第二种主张是以整个体育学术活动体系(体育学学术实践主体和体育学学术实践的成果)作为批评的对象,它不但对体育学学术成果展开评判,还对体育学学术观念、品格、环境、思潮、流派以及学术批评自身进行判析。我们比较赞同第二种主张,并倾向对“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作如下的界定: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包括学术主体、成果、理念、风格、思潮、流派、运动以及学术批评本身,即包括一切体育学学术活动系统。比如李力研“科学研究必须老老实实——因杨杰、周游两作者而说的话”以作者(学术主体)为批评对象,卢元镇“中国体育社会学科进展报告”以中国体育社会学学术成果为评判对象,赵山成“试论茅鹏的学术思想”以茅鹏及其学术思想为对象,黄卓“关于体育科研中的责任与道德问题”以学术责任和学术道德理念为对象,陆一帆“体育生物科学研究方法置疑与推敲”以学术方法为对象,张力为“研究报告评价标准的界定与联想”以学术成果报告标准为对象,杨正云、王颖“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学校体育思潮的历史变迁”以学校体育思潮为对象,王新、钟明宝“刍论体育批评的含义及其形态”以体育学学术批评自身为对象等等。可见,体育学学术批评,是对体育学术活动系统中各种具体学术现象,从科学的观点出发,作出思想性、理论性及价值性诸方面的评价。从表面上看,我们对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范围如此界定,似乎与体育理论的研究对象基本同等。事实上,它们有较大的区别,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具有其自身显著的特点。具象性所谓具象性特点,是指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是各种“具体的体育学术现象”,或者是一项成果,或者是一个或几个学术成果主体,或者是一种学术思潮,或者是一种学术研究方法,或者是一种批评方法,或者是批评的主体等等。体育学学术批评正是对这些具体要素有针对性地予以研究。毫无疑问,体育学学术批评这种具体的局部研究当然也要联系其它部分甚至体育学整体,但是,它是由具体而整体,其研究的中心始终是具体的体育学学术现象,也可以说,体育学学术批评是局部微观研究。这是体育学学术批评对象的一个基本特点。集中性所谓集中性,是指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学术成果”这个基本要素上,也就是说,体育学学术批评是以“学术成果”作为体育学学术批评最基本的对象,其它各种体育学学术批评活动,如“体育学学术主体”批评、“体育学学术理念”批评、“体育学学术风格”批评、“体育学学术思潮”批评等,只不过是“学术成果批评”的延伸,或者说是在此基础之上的批评对象的转变。之所以如此立论,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体育学学术成果”是体育学学术批评系统各要素的核心,是体育学学术意识形态最常见、最基本、最直接、最活跃的形体和存在方式。体育学学术领域里的一切学术现象一旦离开了“体育学学术成果”这一具象形体,就无法存在,也就不称其为体育学学术现象了。所以,体育学学术批评对象的第二个特点是极具集中性。现代性所谓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具有现代性特征,是指体育学学术批评主要是以现实的、最新的多种多样的体育学术现象为主要对象。尽管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偶尔会投射聚焦在过去某个历史时期的一个点上,但这种偶尔的投射聚焦往往也是为了评介该对象的现实意义与价值。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体育学学术批评是对当代现实体育学的研究,属于一种共时性研究。体育学学术批评对象的这种现实性特征,一是来自体育学理论发展的宏观驱动,二是来自体育学学术批评价值的内在要求。因为体育学要发展,体育学学术批评要前进,都需要以新理论、新实践、新成果为研究对象,也只有通过对开创新领域和出现新论断的批评与评价,才能实现真义上的进步。所以说,“现实性”特征直接决定着体育学学术批评的意义、价值和生命。由此,可以说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就是体育学术活动中各种具有一定新质的具体的体育学术现象。其中,最新的体育学术成果是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基本对象[3]。学科性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与体育学学科内涵和外延紧密相关,体育学学科内涵和外延的所有成果部分都应该是体育学术批评的对象,如果其内涵与外延超出体育学学科领域,则不应成为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因此,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具有学科性特点。这是体育学学术批评区别于其他批评的最显著特征,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需要指出的是,在研究确立体育学学术批评对象的时候,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第一,我们必须客观、公正地面对各种体育学学术批评实践,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而是主观主义、片面主义当头,偏于一隅,就可能使体育学术批评有失公允。第二,我们的研究必须是对体育学学术批评对象的全面整体的研究。如前所述,尽管我们对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作了简单、静止、孤立的解说。但在体育实践中,这些对象并不是简单的、静止的、孤立的,而是复杂的、运动的、庞大的、有机统一的系统整体,体育学学术批评必须把它作为一个系统整体予以全面的而不是局部的、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系统的而不是孤立的研究。只有尽可能的全面真正地占有体育学学术批评的研究对象,才可能保障独立建构体育学学术批评体系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体育学学术批评的性质
体育学学术批评的性质,是独立建构体育学学术批评体系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重要基本问题。搞清这个问题,有利于体育学学术批评在体育学中的合理定位,有利于体育学学术批评的自身建设,更有利于体育学学术批评的科学化发展。首先,体育学学术批评是体育学中的一门独立的应用性理论。诚如杨黎明所指出:“如果按传统的方法将体育学划分为体育学实践和体育学理论的话,我们认为对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合理定位应该放在‘它是体育学实践与体育学理论之间得以连接的纽带和桥梁’这样一个认识层面上。因为体育学学术批评源自体育学实践,而体育学实践通过体育学学术批评上升为体育学理论,体育学理论又反过来指导体育学学术批评,并通过批评促进体育学实践的进步。如此周而复始,就构成了体育学的运动发展历程。”[2]体育学学术批评,一方面联结着体育学实践,另一方面联结着体育学理论,是体育学发展过程中具有独立性质的中心环节,更是体育学各分支学科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共同发展的重要枢纽。正是由于体育学学术批评的这种特殊地位,决定了体育学学术批评是一门具有独立性和实践性的“应用理论”,而不像体育学理论属于“基础理论”。其次,体育学学术批评是一门科学,是一种创造性的科研活动。体育学学术批评使用逻辑推理方法、历史方法、数理统计方法、比较方法等科学方法,去进行概念、判断、归纳、演绎、推理,从而对体育学学术批评对象进行证伪、辩驳、争论、分析、综合、评价,从根本上讲,这个过程就是“获得或者接近真实真理”的科学过程。体育学学术批评也因此而就具有了科学的一般属性。从思维的方式上看,体育学学术批评在对体育学术现象进行评价时,与科学研究主要运用抽象思维而基本不用形象思维一样。在进行归纳、比较、分析、综合之后,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再深入到体育学术批评对象的本质,揭示错误的理论,总结客观的规律,以更科学的理性认识形成真实的体育理论,这就使体育学学术批评具有了科学的性质。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上来看,体育学学术批评与科学研究一样,都是一种自觉的理性思考和假设验证活动,它们都以一种冷静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研究对象,都以一种客观公正的标准追求真理。从这个意义上讲,体育学学术批评具有科学的属性,又可以称之为“科学批评”。总体上讲,体育学学术批评的性质具有科学的因素,但不是科学的附庸;是体育学中一门独立的应用性理论。
篇4
[论文关键词]文学批评 现代 独立性 科学性
文学批评作为文艺学的一个专门术语,是“五四”时期从西方译介过来的。“批评”含有“裁定”“判断”等意。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说:“批评渊源于一个希腊字,意思是“作出判断”,因而,在广义上说来,批评就是“判断”。17世纪后期英国批评家德莱顿也曾说过:“批评最先由亚里士多德确立的,它的意思是指作出正确判断所使用的标准。”德莱顿使“文学批评这个术语在英语中意义明确并逐渐为较多的人使用。”我国传统的提法多讲“文学评论”,古代也使用过“批评”的概念。如明万历年间刊刻的《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钟伯敬先生批评水浒传》等。此处的“批评”含义已与近代接近。文学批评作为学科是以~定的文学观念、文学理论为指导,以文学欣赏为基础,以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包括文学创作、文学接受和文学理论批评对象,而以具体的文学作品为主)为对象的评价和研究活动。
首先,文学批评具有独立性。批评是一种建构,一种再创造。任何一位文学批评家都不否认他对创造性的追求。正如法国文学批评家蒂博代所说:“所能给予一位大批评家的最高荣誉是使批评在他手中真正成为一种创造。”批评家依据一定的批评观念、方法,首先对批评的对象进行选择,然后着力于发掘、揭示所批评作品的内在价值,这是一个建立在对作家与作品充分理解基础上的重新建构、新的综合过程,即对作品从“理解”进入“发现”,发现作家未意识到的作品的价值水平以及作品的潜在意义,并以独特的审美理想进行再创造,这时,批评家在批评中表现出自己独特的审美理想、审美观念,使自己的批评也成为一种凝聚着审美个性的“创作”。有了这种创造意识,批评家就不仅是作家的知音而且是与作家并列于文学王国中的另一种意义的作家。另外,文学批评必须在联系于哲学、政治、道德、历史、文化等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摆脱成为它们附庸的重负;必须在联系于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的同时也改变成为它们附庸的地位,而应该使批评回到批评自身的本置中来,使批评真正成为批评.,成为“文学”的批评。
其次,文学批评具有科学性。文学批评不是对主体情感体验的简单记录,而是一种转换,“批评其实是从感觉的范围转到思想的范围。”体验的心理学含义是“从内部”加以知觉,使主体的艺术知觉变为对现实生活的情感认识。而批评则是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看待对象,在内部体验与外部观照和思考的结合中对对象作出综合判断。判断意味着文学批评应在对文学作品及现象的感受中探寻和揭示这些现象内所蕴涵的普遍规律和真理。在发掘和研究文学现象与规律之关系的工作中,仅凭批评者个人的喜好与情感偏向还远远不够,理性化的思维方式是必要的。与此相关,在表达方式上,文学批评应尽可能明确、坦率,这样才能符合批评家理性思维的轨迹,完成批评所应担负的态度鲜明地表述观点、评判作品的任务。这一点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言:“批评应当是尽可能避免任何半吞半吐,限语但书,细致而暖昧的暗示以及诸如此类只能妨碍问题的率直、明朗的迂曲说法。”
另外,文学批评注重对方法诊的探索。进入20世纪以来,批评对方法论的探索热情与何比重明显增加,批评家自觉的批评意识与某种或数种科亨法或学术思潮相结合,产生了如精神分析批评、原型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现象学批评、读者反应批评等多种形态和流派。这种状况显示了文学批评寻求秩序和建立系统的一种愿望,以使批评变得更加科学化。加拿大文论家诺思洛普·弗莱说过这样一段话:“不论涉及哪一领域,科学的引入都会使秩序代替混乱,在原只是偶然和直观的地方建立起系统来,同时它还保护了这一领域的完整,使它免遭外部侵入。”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对20世纪文学批评科学化走向的一个说明。建立在新的哲学观念以及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乃至自然科学理论基础上的新的批评方法的引入,为拓展批评家的思维领域,丰富和完善批评手段,从而推动整个文学批评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随着批评方法的确立和批评模式的建构完成,文学批评的科学性因素更加得到增强。
文学批评的理论化。从文学批评来看,当其摆脱传统的理论附庸地位,通过具体文本分析而在文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大显身手时,本身已经担当起新的理论先锋角色。美国当代批评理论家莫瑞·克里格说:“作为一种知识形态,而不是仅仅作为我们与文学的情感遭遇的详细描述,文学批评必须理论化。”正是这种理论化的批评使得“理论的作用业已深化和广泛”。当今的文学批评与传统的文学批评已有了很大的区别,它们所关注的重心不再是一些具体的文本,而是文学批评本身的性质、目的、对象和研究方法等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即使面对具体的批评对象,批评家们也主要不是以情感和审美为基础,而是以思辨的方式,在一定理论框架的规约下,运用一套理论范畴对文学作品加以剖析。20世纪文学批评十分注重理论建构,它们大多是通过某种理论预设,在演绎的框架中推导而成。在对已存批评的反思中,批评家也总是从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人手,以否定其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同时试图在理论上有所开拓,有所建树。而在理论建构中,20世纪的文学批评又表现出一种泛学科的趋势,即通过与其他学科的联姻,在借鉴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特有的理论框架。在20世纪,几乎没有一种文学批评不与其他学科发生关系。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正是从现代语言学中获取了灵感,精神分析批评本身就是精神分析心理学的产物,而文化学批评则借鉴了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这些人文学科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为文学批评提供了坚实的学科背景,成为各种文学批评流派的理论前提。当今的各种文学批评正是通过对这些学科研究成果的引进、消化和吸收,在交叉、边缘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套独具特色的理论主张和观念方法,使文学批评呈现出浓郁的学术氛围。这种联姻不仅加强了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和特色,多方面地揭示了文学的本质,同时也扩大了文学批评的关注范围,将文学批评研究的问题扩展到与文学相关的文化和知识的前沿。
批评家的立场。蒋原伦在《文学批评学》一书中曾把批评的进程分为三个时期:即前自省期、自省期、和创造期。所谓“自省”即批评对本身进行反思。批评心理的成熟往往表现在这个时期。就西方批评界来说,自省期始于18世纪中叶,由德国批评家“狂飙突进运动”的先驱赫尔德等人开启。如果说,早期批评的地位因其依附于创作,批评家的自信是凭借经典作品而来的话,那么,至自省期,情况有了根本的转变。由于批评意识的觉醒,批评家相对于作品取得了独立的地位。大部分批评家已经从经典批评的樊笼中走出来,觅取新的美学原则、确立新的批评信条并依此来评判创作。这时,批评开始走向繁荣。在前自省期,批评家往往充当批评公理的制作者和代言人(如亚里士多德),因此批评家个性中情感的,独具个人色彩的成分很难得到发挥或宣泄。而批评一旦对创作取独立的地位,批评家在其批评过程中同作家在创作中一样,可得到个性的实现。
篇5
关键词:文学批评问题挑战
一、当代文学批评受到的制约
当代文学批评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多个方面的制约,比如现代化的心态、进化论的思维习惯等。加强当代文学批评研究,需要对当前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
(一)“现代化”心态对文学批评发展的制约
在我国的本土语境中,人们对于现代化思想文化的理解还比较片面,认为现代化的思想就是一种新和一种时髦,但是这种现代化的理解是十分狭隘的,如果只是单纯地追求一种新颖和时髦,并没有为思想文化增添一些新的东西,因此这种所谓的新颖以及时髦持续不了太长的时间,尤其是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任何一种时兴的东西都十分短暂。最关键的问题是,所谓的新颖并一定是有价值的,对思想文化的内涵的衡量,并不是以时间上的新颖以及时髦作为标准的,往往是时间越久越有历史沉淀的东西更有价值和意义,这种经时间沉淀的东西往往也不会因为时间而消逝。因此当前社会上存在的一种现代化的理论对于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往往存在一定的限制。
(二)进化论的思维习惯对文学批评发展的制约
思想文化的发展并不是线性的,而是时间的一种非线性的累积,由于人们在思考的过程中往往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对我国本土的思想文化界以及文学批评理论界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我们在发展文学批评理论的过程中不能对这种思维定势进行突破,则根本不可能实现创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常说的一种规律,往往就是人们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目的,这种进化论的思维方式对于当地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有很大的限制。
(三)在文学批评过程中缺乏批判精神
近年来,我国的本土文学批评界在积极倡导一种宽容的精神,即主张不予外界进行争辩,对外界的任何道理都应该要理解和包容,这样才会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促进相关的理论的发展。这种宽容精神也是一种现代化的体现,是当前社会中存在的一种思维定式,如果不宽容就会被看成是不识时务不现代的。但是这种所谓的宽容反而导致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缺乏一种批判的精神,但是如果将宽容精神运用得好,则可以促进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宽容”的精神与文学批评的职能是不冲突的,宽容意味着有不同的观点以及理论,不同的观点以及理论在发展过程中都会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各种不同的理论在相处的过程中也应该要积极保持对外界的一种批判,以一种客观的视角去看待自身与外界之间的关系,做到理解与批判共处。然而我们当前的时代就是一个圆润的时代,更加注重技巧的圆熟,加上各种商业利益以及体制化的生存方式的存在,导致社会发展过程中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
二、当地文学批评面临的挑战
对于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应该要结合中国本土文化的传统以及特征,进行有创造性的转化,倡导在文学批评的过程中立足于本土的多元文化的平等交流与对话。但是在当前我国的文学批评过程中还面临着一定的挑战。
(一)存在极端的民族主义的指责带来的挑战
在我国的文学批评界的发展过程中倡导的是重建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并且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的过程,这种思想已经受到了很多方面的指责,这种理论在外界很多人看来是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甚至有人认为这种理论完全是没有必要存在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随着各个国家和民族被卷入到对外开放潮流中,任何一个国家以及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不可能完全保持一种绝对的独立,都会受到外来思想以及文化的影响。西方思想文化对中国本土思想文化就产生了一定的碰撞,然而正是由于不同的民族之间的差异,才使得我们的文化能够被拓展。我们在对外来文化进行接受的同时也应该要保持一种独立的态度,即吸收其他文化中的好的一面,对不好的影响进行降低甚至是消除。当前文学批评界在发展时有的学者就存在比较极端的民族主义,对外来的很多东西都是排斥的,这种做法并不利于思想文化的建设以及各种理论的创新,对于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而言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二)体制化生存方式带来的挑战
体制化的生存方式是当前我国本土的学者以及文人在对文学进行研究时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在体制的约束下,人们的活动往往都会按照体制的各种需求,进行量化,在这种量化的影响下,很多人就会为了社会上普遍追求的东西放弃了自己生活中原本应该有的一种独立思考的能力,往往更加注重追求“量”的指标,而缺乏对文学发展中的各种理论进行辨证思考,这样导致泡沫式的学术开始泛滥,很多文字垃圾出现。在这种体制化的生存方式中,对文学批评理论就产生了一种新的挑战,这其实是一种学术的异化。并不是在追求知识、构建思想。体制化的生存方式下要想促进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要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以及批判精神,并且以这一种独立的精神来应对这种体制化的社会。
(三)简单经济决定论带来的挑战
用简单经济决定论来对社会中的思想文化以及文学现象进行解释是当前社会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方式。在将近五十年的本土的文学批评理论中一直都是在用这种理论对文学批评进行支撑的,这也使得文学批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与本土的文学创作实际情况产生了偏离,使得理论与现实生活出现了严重的脱节。此外,简单经济决定论的很多观念与我国本土的思想文化以及各种传统也存在一些格格不入的状况,因此,如果不能对这种模式进行突破,则很难促进各种理论的创新。
篇6
本文作者:徐小霞
解决分析通俗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是贝内特提出“阅读形构/互—文性”观点的出发点和逻辑前提。要理解“阅读形构\互—文性”,必须先阐明贝内特对通俗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的认识和分析思路。贝内特首先站在解构主义立场审视通俗文学与“文学”的关系。他批驳传统文学批评依照资产阶级文学标准划分“文学”与“通俗文学”等级序列,如此做法,使文学批评对文学审美价值过于牵挂,一方面把“文学”看作与意识形态有别的自治领域,另一方面无视通俗文学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多变性,将通俗文学简化为主导意识形态(虚假意识),沦为大众工业生产和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容器。其结果不但使批评沦为一种扭曲的唯物主义,而且阻碍了通俗文学介入霸权斗争领域行使政治运筹的可能性。为反对传统文学批评将通俗文学等同于主导意识形态的简化作法,贝内特认为对通俗文学及其意识形态的认识,不能采取以往文本形而上的观点,要从文本间性即从阅读接受的互文性关系联结中透视文本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效果。因为文本在文本间性系统的关系联结中产生一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效果,“关系联结仍然是构成文本得以发挥作用的惟一可能的政治‘场所’”。[1]文本间性就是不断变化的文本-意识形态关系,这种互文关系效果(政治、意识形态)铭刻在文本接受阅读过程中,影响文本的接受状况。这就意味着文本在多元的接受语境下,成为一个漂浮的能指,被编入不同的文化、权力、社会制度等符码。所以,文本的意识形态效果不是从文本的意指内容中直接体现,而是在多元动态的阅读接受过程中呈现意识形态效果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为此,考察通俗文学的意识形态效果,便需从文本的阅读接受入手。其次,在分析文本阅读接受问题上,贝内特借鉴了阿尔都塞意识形态质询机制,将文本意识形态与具体、差异的阅读个体连接起来,认为文本产生效果的依据不是裸的的主体性,而是“受到各种不同甚至有时矛盾的意识形态构成中对某一特定主体立场质询的个体,”[2]主体立场随差异性社会位置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动态的主体立场再插到变化的文本间性关系联结中,阅读个体便在一系列意识形态坐标轴上移动而形成多元身份,文本则成为或斗争、或反抗、或妥协的多元意识形态场域。可以说,文本不但由于阅读接受敞开了文本的历史,且因接受阅读而成为多元矛盾的意识形态效果场域。通俗文学文本与读者究竟如何发生作用,阅读接受中文本间性的动态意识形态效果场域的变化机制如何运作,阅读接受的条件又是怎样的?贝内特用“互-文性/阅读形构”解决这些问题,令人信服地阐明了阅读和文本受到铭刻于其间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一系列互文调停而形成以文本为中心的动态场域,并揭示出阅读个体在建构多元主体身份过程中的积极能动性。这也是贝内特从文学阅读角度试图调停英国文化研究理论存在着的结构主义与文化主义间的矛盾的理论尝试。
“阅读形构/互—文性”(阅读形构只在阅读引起的互—文联接中得以体现,故将两者置于一起。)的内涵极为丰富,它以读者接受和文学互文性等理论为基础,挪用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质询说,福柯的话语形构,拉克劳、墨菲的话语联接,葛兰西霸权概念等,勾勒出铭刻在阅读接受中的多重社会历史力量及其与文本、读者间的复杂关系,体现了贝内特鲜明的政治旨归和文化唯物主义立场。“阅读形构”指“一套话语和互文力量,它们组构和激活阅读实践,将文本和读者联接为特定的关系:读者是具体的阅读主体,文本是以具体方式阅读的文本。”[3]这种界定显得十分抽象模糊,通过贝内特在不同著作多次对“阅读形构”的特点、功用、性质等描述,可发现阅读形构实则是一种熔铸于文本和读者间的阐释框架或阅读框架,类似于海德格尔、伽达默尔阐释学的“前有”“前结构”。阅读形构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而非阐释学的作为通达“在世之在”的“前见”的本体论范畴。相比阐释学和接受理论的前理解对个体心理经验性的强调,贝内特更重视阅读形构这一阅读框架的文化、意识形态等社会历史规定性,他用佩奇尤克斯的话语形构类比自己的阅读形构这方面的特征。佩奇尤克斯指出话语构形根植于特定的意识形态,个人的言语行为不是个人主观运用的语言产品,而是被受制于具有意识形态倾向的话语构形的制约,语言在实践、操作、建构各层面受到不同的话语形构相斗争的对抗,即使相同的词语也趋向不同的意义,意义是能指之间不停运动关系的结果,而非仅仅是所指,词语、语句、命题从它们所属的话语形构中得到它们的意义。这意味着阅读形构和话语构型一样,在一定的意识形态压力下生产意义和效果。阅读形构/互—文性源自文学互文性理论和阅读接受理论,但又比后者意蕴丰富,它更突出文学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将文学疆域拓展到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领域。众所周知,“互文性”最早由克里斯蒂娃提出,指任何文本都是引语的镶嵌品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改编。即每一个文本中都包含了其他文本涉及的因素,每一个文本都不可能是一个与外界绝缘的封闭的语言体系,而是与其他文本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互文性强调各文本之间的复杂联系,文本意义的交互性、流动性和差异性。克里斯特娃的互文性仅限于单个文本内部中其他文本的指涉关系,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狭义的互文观念。随后,罗兰•巴特在克里斯蒂娃文本互文性基础上,提出在阅读角度认识互文性,并给予理论阐发。他继承修正了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从克里斯蒂娃在作者立场划分文本转向读者立场,表现了互文理论研究从文本生产理论向接受阅读的转换。巴特将文本划分为可读文本和可写文本,强调读者参与文本生产的积极性、能动性,读者在可写文本中通过发现文本意义新的组合方式,重写、再生产、再创造文本,使意义在无限差异中被扩散。巴特反复强调阅读个体在(重)写文本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文本的阐释取决于个体汇集各种互文本并将它们同给定文本相联系的能力。巴特从阅读接受的积极能动性角度分析文本互文性生成的机制,无疑具有开创意义,但他并未涉及主体和互文本如何联系的问题,更未考虑阅读互文性的社会历史规定性。贝内特和巴特一样,将读者受众作为文本相互联系的节点,强调阅读主体的积极能动性,认为文本正是通过阅读才得以关联形成互文关系。他将这种因阅读而相互关联的文本现象称之为“互—文性”。通过与克里斯蒂娃互文性的比较,贝内特说明自己的互—文性概念,“使用连字符是为了避免与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相混淆。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概念指:可在一个特定的单独文本内在构成中辨认出来的、其他文本的指涉体系。而我们的互—文性概念指在特定阅读条件中,文本之间的社会组构关系。”“互文性指一系列意指关系,它们共同体现在一个文本中,是文本所展现的变化的产物。而互—文性则是文本被社会性地组构于阅读形构客观性方面中的关系方式。互文性是社会性组构的互—文性的特定产物,后者在为阅读实践上提供了客观力量的同时,也为互文指涉的生产和运作提供了框架。”
贝内特的互—文性更强调互文本间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广义的互文观,它以阅读为联结机制,形成文学文本之间、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文本与主体、文学领域与其他社会活动领域间的动态场域。相比巴特阅读接受角度的互文性概念,贝内特用“阅读形构”弥补巴特忽视的阅读主体与互文文本如何联系的机制,突出铭刻于其间的多元意识形态效果和意义生产的社会历史规定性、主体与文本间性等特征。“阅读形构”具有极丰富的内涵和政治意味。具体有以下几点:(1)阅读形构是熔铸于文本与读者间的阅读理解框架,类似于“前理解”“前见”,它是接受主体与当前文本产生对话的前提。它凝聚着主体积累的互文知识、经验、审美情趣、心理动因等因素,并和内化于主体经验中的时代、社会、文化、意识形态融合一体,也即主体在阅读接受活动中已先行被话语所塑并将之带入接受活动中。这一过程体现了主体阅读接受的积极能动性,主体依据自己具体的、境遇性的阐释框架阅读文本,赋予其意义,用贝内特的话说“文本是为读者的文本。文本总是被组构好的文本。”(2)“阅读形构是一套交叉的话语。”这套话语铭刻着各种物质、社会、意识形态等历史力量,或者说它是多元话语场域。这就意味着在这套互文话语中充满着各种意识形态的缝隙,它们在相互角逐、争斗、协商中被联接(articulation)、增补。这套互文话语是意义斗争的场所和意识形态角逐的领地。比如在文学批评这个特定阅读关系中,阅读形构使文本被生产性地被激活,文本依照意识形态立场呈现相应的意义,在与其他阅读形构话语竞争中,建构出政治干预的空间和权威。(3)在阅读形构中“主体是为文本的主体。”在这套意识形态角逐的互文话语中,暂时决胜而出的主控性话语和意识形态将个体质询于主体的位置上,使其成为“这个人”。鉴于不存在抽象的意识形态,只存在具体的个体在具体境遇被质询为具体的主体,故贝内特说“读者是具体的主体。”主体在阅读中身份不断被瓦解、重构,成为某一具体意识形态质询下的具体社会主体,并修正原有的阅读形构。(4)阅读形构类似于福柯的话语形构,暗中为知识、权力和意识形态所编码,更确切的说,它是个体阅读实践所遵循的一套制度话语。文本的真正意义和效果不是文本所指内容,而是文本作为能指依据不同阅读形构的意识形态和权力符码而体现不同的意义和效果,“阅读效果不是预先存在于阅读形构中,因为它是在阅读形构中产生的.....意义通过文本在不同的阅读形构中被生产性地激活方式”出现。[5]如邦德小说随阅读接受中变化的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压力而不断重组,最终构成一个集电影、广告、杂志、玩具、评论、演员等各种文本为一体的网络场域。作为通俗文学的邦德小说因其变化衍生的各种互文本,成为英国日益突显的大众文化现象。邦德文本之所以流行和经久不衰,就在于它能依据不同阅读形构中意识形态符码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为此,通俗文学(文化)的意识形态复杂性、矛盾性不在文本本身,而在通过阅读形构\互—文性体现出的变化的意识形态上。(5)阅读形构的物质载体是意识形态实践制度化的各种机构,它们形塑阅读形构,建构社会主体身份。阅读形构在其历史过程中,总是内在地、不断地重新书写进多重物质的、权力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符码,并内化在主体阅读过程中,质询和重构相应的社会主体身份,再生产一定的社会关系,维系或颠覆象征秩序。为此“文本总是已经被文化激活的对象,读者总是被文化激活的主体。”所以要想充分理解并评价阅读形构这套交叉的话语所隐含的权力,“不仅要考虑话语的明确意义或目的,还应更多地考虑话语的系统构成,因为它们形成的模式由它们与非话语实践的关系决定,如与制度、习惯、或日常实际生活的关系等”。[6](6)由于阅读形构是一套争斗和协商的话语联接场域,它可被各种权力和意识形态编码和介入并生产相应政治效果和意义。如此,文学批评话语可积极地介入阅读形构,为霸权斗争生产相应的知识话语并建构相应的政治主体。这点表明阅读形构概念具有鲜明的文学政治效果,体现了贝内特本人的政治立场。贝内特以“阅读形构”为中介,将系列文本、阅读主体、意识形态等联系起来,形成一个以文本阅读为核心的文本之间、文本与社会,文本与主体间多元动态的意识形态效果动态场域。同时,阅读形构在各种变化着的权力和意识形态压力下,将个体质询为多重变化的社会主体系列,因为主体认同机制中隐藏着复杂的权力关系[7]。就此而言,阅读形构是意识形态在文学阅读接受活动中的具体体现。更重要的是,阅读形构/互—文性的意识形态压力并非以抽象观念的形式运作,它有一系列物质的、制度的支持,如学校、教育体制、文学批评和理论话语、文学教育等文化实践形塑阅读形构,为意识形态合法化发挥关键作用,维系或再生产一定的社会关系。总之,文本通过微观层面的个体阅读形构,受到宏观互文系列的文化意识形态之调停和介入。
贝内特以通俗文学和意识形态关系这一问题意识为起点,通过阅读意指实践反驳了传统文学批评将通俗文学简化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做法,就此而言,他承袭了英国文化研究重视受众思路。但贝内特又和霍尔、莫利等人经验式受众研究的思路不同,他更强调文学接受过程中的社会文化等历史规定性,突出铭刻于文本和读者中的意识形态、文化指涉和权力关系,在变化的文本效果场域看待通俗文学(文化)与意识形态关系间的复杂关系,形成“阅读形构\互—文性”这一文学批评理论成果。这种思路启发了英国第三代受众研究,他们不再以个体经验接受为主,而位移于微观(文本-语境)和宏观(社会结构)层面的结合,从文本中见出社会文化结构、话语和文本本身的生产过程等。如对机构\学术写作与受众的关系问题研究即为突出一例。[8]就文学批评理论而言,贝内特将媒介社会学的文本效果说引入通俗文学的接受研究上,通过文本接受彰显出文本随社会历史语境变化而变化的多元意识形态效果,突出了文学尤其通俗文学意识形态的复杂性、矛盾性。贝内特在方法论上,强调从互文性角度理解阅读,并为前理解注入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弥补了以往文学阅读接受研究和互文性理论对阅读实践的社会历史规定性重视不够的缺憾。用贝内特自己的话来说“注重效果的传统很少受媒体社会学好评,但它确实对观众问题给予了认真思考,近年来输入的关于'解码'过程的符号学观点已对影视研究产生影响,比文学批评界更重视形式所能产生的效果。简言之,现在还没有真正的读者研究(从效果角度思考文本接受。)”[9]综上所述,贝内特的“阅读形构\互—文性”文学批评理论,是对文化受众研究和文学读者接受研究的双向融合和超越。他的分析思路、理论观点对当代中国文化诗学分析通俗文学、文化现象具有一定的方法论启示和借鉴意义。
篇7
关键词:蒂博代;自发的批评;职业的批评;大师的批评;文学批评共和国
法国文学批评家阿尔贝・蒂博代将其有关文学批评的部分演讲稿编辑成书,并为之命名《批评生理学》。在此书中,蒂博代将文学批评大致分为三种类型:自发的批评、职业的批评和大师的批评,他强调这三种不同类型的批评方式构成了一个和谐的文学批评“共和国”。
一、三种批评形式的内涵特征
(一)自发的批评
自发的批评又叫口头批评、现时的批评,是一种有教养者的批评。它的主体并非是所有的读书人,而特定指那些本身文化素养很高、鉴赏品评力强的人。但是这些人往往具有述而不作的特点,他们对于文学的批评停留在与友人交流的层面不经常性的进行批评写作,即使要鉴赏他人的作品,也只是跟自己志趣相投的友人分享体悟。比如说,随着网络传媒的发展,大家更倾向于在博客、论坛中发表个人对某些作品的看法,与其他网友进行交流互动。
这些人对其他个体的作品进行品鉴,也只是为了赢得精神上的愉悦。而且这种批评不需要引经据典,也不需要面面俱到,更不需要那些刻板严谨的规律,具有自由的、活跃的、灵敏的、坦率的、生机勃勃的特点。这种口头的批评也并非无迹可寻,我们在个人的通信、日记、私人手记、回忆录、报纸等载体中都能寻到它们的踪影。
(二)职业的批评
职业的批评又叫教授的批评,是一个遵循来自讲道的某种形式的法则的人所进行的批评。进行职业批评的主体大多是专家,他们通常对作品进行阅读、研究和整理,采取理性的鉴赏、分类、解释的方法,很少去感悟式的品味。其自然的倾向是条理化、系统化和科学化。从事职业批评的专家总是从理性的角度出发,对数百年的文学史追根溯源,文学因此也被分为具有固定规则的各种体裁,并且一直不断的延续发展。出自职业批评家之手的批评文稿总是给人平淡、枯燥、古板的印象。
(三)大师的批评
这里的“大师”指的是那些已获得人们普遍认可的大作家,这种批评又称艺术家的批评或作家的批评,是一种寻美的批评。大作家在批评上各有各的风格,他们往往在运用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创作经验与感受去细品所要批评的作品。在美学和文学的诸多问题上,他们会阐明自己的看法,他们的批评一般会形成普通美学。大师们认为,批评首先是一种理解和同情的行为,应该以富有创新精神的人为主体,其最完美的表现为浪漫派批评。蒂博代对这种批评充满期望,希望它“就是那种居于艺术最深处的批评”。
二、三种批评形式的局限性
在“文学批评的共和国”里,自发的批评、职业的批评和大师的批评各在其领地内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被它们自身光芒所吸引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它们的暗淡面和局限性。
(一)自发的批评的缺点
自发的批评有三大缺点:首先,在评论过程中经常存在不读而评的现象。在某些交流活动中,经常会存在人们并没有读原作品,只是在道听途说的基础上加以评论的现象。这是口头批评最大的危险使得批评难以避免歪曲的观点。其次,这种批评很容易受团体性的影响,极易演变成派别间的批评。斯丹达尔说:“为了受到某一派别的赞赏,只需重复这一派别所憎恨或喜爱的老生常谈就够了。”[1]第三,自发的批评很容易出现判断失误,它表达的是时髦的趣味,而时髦是一种老的最快的东西,我们难以预料它的变化和发展,很容易为后人诟病。
(二)职业的批评的危险性
职业的批评有两种危险:一是职业批评家并不是每次都会将自己要批评的对象全部读完或者细致体会。有时候因为时间关系等也会偷懒,常常依靠自己在当时阅读的回忆和所做的笔记,而且他们常会隐藏个人对作者的真情实感。有时候他们所表述的可能不是自己真正的想法,而是受外在因素影响而写出一些陈词滥调,导致他们做出毫无意义的事情。二是更为严重的顾虑病,即职业批评家们由于过于搜求证明材料,瞻前顾后地行为使得自己迟迟不能进行高效率的工作,从而导致职业的批评一事无成的后果。蒂博代虽说不想贬低职业的批评,但字里行间对职业批评固有的僵化作风颇有不满。难能可贵的是他对此提出了非常中肯的意见:“一本批评著作的生命就在于它是否引起批评,是否参加了对话,是否把它的震动传达给了超越它的活动,也就是说,它是否有欠完整,是否能引导读者纠正它的错误。”[2]在他看来,我们可以通过良好的教育的途径来避免这两种危险,必须要在注重鉴赏、排列、解释的同时让趣味与品鉴参与进来。
(三)大师的批评的不足
尽管蒂博代对大师的批评寄予厚望,但是他也指出了这种批评的不足之处:在对经典作品进行品评的时候,大师们通常运用自身的创作优势对作品进行精彩的解读,这也是其他的批评做不到的。但是,当它面对当代作家所著作品时,难免会因为一些现实因素而有失偏颇。大师的批评在对作品进行解读的时候,一方面进行理性客观的品评,但是由于受某些原因影响会造成互相吹捧的局面,使之蜕变成“作坊的批评”;然而,当他因感性因素影响对作品表达出不满时,容易造成文学派别间的相互抨击,形成“文学党派的批评”。
三、结语
蒂博代曾多次指出三种文学批评形态在“共和国”里并不是处于和平共处的状态,它们互不相让甚至互相攻击。对此,蒂博代认为我们应该把三种文学批评看作三种活跃的倾向,它们组成了文学批评的“共和国”。而对于他们彼此之间的斗争,我们不应该阻止,也无需遗憾,我们只须记住这三种批评方式是并存的,它们虽然都有自己的不足之处,但都对文学的发展起着巨大的参与作用,我们应该允许和承认多种批评形态的存在。
【参考文献】
篇8
一、原型批评
原型批评是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重要流派之一,代表人物是瑞士心理学家荣格。他认为,“原型”是从远古时代就普遍存在的意象,这一意象在每个时代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文学作品并非作家的凭空创造,而是传统的产物。当读者看到作品中的某个角色、某个主题与心中的原型相似时,就会生发出对这种角色、主题的认同或共鸣。我们在读《雷雨》时会感到,剧本中的主题、情节、人物都似曾相识。《雷雨》呈现了戏剧中常见的三种母题:复仇、、弃妇。
1.复仇的母题
复仇是人类的一种本能,也是文学创作中常见的母题。在《雷雨》中,明显具有复仇性格的人物是蘩漪和鲁大海。蘩漪“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她性格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蛮劲”,使她能够做出不顾一切的决定。当周萍以一句“一时的糊涂”抛弃了她时,蘩漪绝望了。接着,她采取了一系列的复仇行动。雨夜跟踪周萍,关窗堵住他的退路;阻止周萍与四凤出走;当众公开自己和周萍的关系,导致周公馆的崩溃。复仇的结局是惨烈的,四凤触电身亡,周萍开枪自杀,周冲也不幸丧命。从火一样的爱到火一样的恨,让一个女人丧失了基本的理智。正如剧中蘩漪对周萍所说的,“把一个失望的女人逼得太狠了,她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在蘩漪身上,我们看到了复仇女神美狄亚的影子。
鲁大海是《雷雨》中塑造的另一个复仇者形象。鲁大海是个苦大仇深的无产阶级工人代表,他与周朴园的冲突可以看作是无产者和资产者之间的矛盾,他对周朴园的复仇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复仇。鲁大海组织个人罢工,在周公馆当面揭穿周朴园故意淹死工人发昧心财的丑恶罪行。尽管他的这次斗争因矿工的复工而失败了,但我们可以看出,他并没有失去反抗的决心,他的斗争是坚决的、义无反顾的。
2.的母题
在世界文学作品中,“”这一母题被戏剧家们以不同的编码形式表现出来,建构出不同的悲剧故事。《雷雨》情节之所以如此扣人心弦,给人强烈的震撼,与作者对“”这一母题的巧妙运用密切相关。剧中有着令人不寒而栗的“双重”:周萍与蘩漪之间的母子,周萍和四凤之间的兄妹。如果说周萍与蘩漪的是有意为之,是人的天性战胜了理智,那么他与四凤无意中的兄妹就是命运的残酷与捉弄了。母题使戏剧《雷雨》具有了浓烈的悲剧色彩。
3.弃妇的母题
弃妇母题一直是古今中外文学创作的焦点,大多表达对弃妇的同情之意。的《雷雨》是弃妇母题的典范模式。温柔善良的侍萍是以弃妇的形象出现在作品中的。三十年前,周朴园为了娶有钱人家的女儿,把刚生下第二个儿子才三天的侍萍赶出家门,对侍萍“始乱终弃”,侍萍成了封建等级制婚姻的牺牲品。剧中的另外一个女性蘩漪,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弃妇的形象。婚后,蘩漪一直被禁锢在监狱式的周公馆里,呼吸不到一口自由的空气,享受不到半点快乐。周萍的出现给她的生活带来生气、带来希望,使她重新找回了自我。然而,周萍给她的欢愉是短暂的,最终还是将她抛弃。同为弃妇,蘩漪与侍萍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性格特征。侍萍具有传统妇女的“美德”,逆来顺受,周朴园将她赶出家门,她没有做任何抗争,而是抱着刚出生的儿子投河自尽。三十年后,与周朴园再次相逢,她提出的条件也只是见见她的萍儿。与侍萍不同,蘩漪具有美狄亚式的叛逆性格。为了追求周萍的爱情,她不顾一切地反抗、报复,从她那颗受尽蹂躏的心中升腾出不可遏制的力量。
二、伦理道德批评
伦理道德批评是以一定的道德意识以及形成的伦理关系作为规范来评价作品。这种批评着重于对文学作品的道德意识性质的评价,侧重作品的伦理价值及其道德教化作用。
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我们重新审视《雷雨》中周萍对蘩漪的始乱终弃。周萍当初爱上蘩漪,是出于一个青年男子生理和心理的需要。他从小失去母亲,渴望着温暖的母爱和温柔的情爱。当周萍遇到了比自己仅大几岁、聪明美丽的继母蘩漪,他深深地陷入了情爱中,以至失去理智地说出了恨父亲的话:“犯了灭伦的罪也干”。然而恢复理智后,周萍对这种畸恋感到了恐惧,他只能选择退缩,选择抛弃蘩漪。诚然,蘩漪的一往情深值得我们同情,从人道主义角度看,周萍是一个对爱情不专的负心汉。但从伦理的层面去分析,周萍也是情有可原的。蘩漪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值得赞赏,但她爱错了对象,通奸固不可取,更为伦理所不容。周萍最终抛弃蘩漪,主要出于对伦理的恐惧,他不可能也永远找不到一种大于伦理的力量来与之抗衡。为了摆脱与蘩漪的畸恋关系,周萍把爱转向了四凤。但命运却又一次捉弄了她,四凤是自己同母异父的妹妹。周萍在痛苦中挣扎,本想冲出畸恋的漩涡,结果却铸成了一个更大的错,最终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
三、精神分析批评
精神分析批评是探寻人物深层心理的一把钥匙,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是精神分析批评方法的理论基础和依据。弗洛伊德把精神活动分为三个领域:本我、自我和超我。对于文学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如果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去探究,会发现许多我们忽略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更有助于理解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对《雷雨》中的周朴园这一人物形象的分析似乎已成定论:残酷、自私、虚伪的资本家代表。而周朴园对侍萍的感情,也被冠以了“虚伪”的帽子。我们如果从精神分析角度重新审视周朴园这个形象就会发现,周朴园几十年来对侍萍的情感是矛盾而复杂的:伤害与悔恨并存,冷漠与真诚同在。周朴园的“本我”、“自我”、“超我”一直在不断地冲突着、碰撞着。周朴园从未忘记过侍萍,经常看侍萍的照片,记着她的生日,三十年来居室摆设依然按照侍萍当初在时的样子,一直都在打听过去的事……所有这些,怎一个“虚伪”了得?抛开周朴园的冷酷、自私,我们同时看到了他的孤独与脆弱。只有看到了这些,才能更好地理解周朴园作为一个普通人性格的复杂性,也就能更好地去理解周朴园这个人物形象。
四、女性主义批评
笔下最具艺术光彩、最富感染力的是一批女性形象。其中以蘩漪为代表的是深受新思想、新文化影响,具有鲜明女权意识的形象。从这些女性身上响彻着女性解放的呼声,透射出作者对女性的眷顾和关爱,体现了作者鲜明的女权意识。
蘩漪是个聪明、美丽却有“叛逆性”的资产阶级女性,她追求人格独立,渴望有爱的婚姻,不甘心做一个没有追求、没有梦想、百依百顺的花瓶。作者在蘩漪与周朴园的激烈冲突中,展示了蘩漪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对以周朴园为代表的男权社会的抗争。她向男权世界宣告:“人家说一句,我就要听一句,那是违背我的本性的。”“我不后悔,我向来做事没有后悔过。”“我做的事,我自己负责任。”从蘩漪身上,我们看到了女性追求人格独立、个性解放、自由平等的进步思想。以人道主义的情怀,站在女权的立场上,表达了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和同情。
五、语言学批评
中学语文阅读教学应注意从语言学角度引导学生深刻领会作品中的语言,探讨语言在文学作品中的含义、功能、技巧。通过“精读”、“细读”,抓住关键词,深入理解作品。语言是剧本的第一要素,抓住人物的语言就抓住了解读剧本的钥匙。
例如:《雷雨》第二幕鲁侍萍与周萍相见一段的描写:
鲁侍萍:(大哭起来)哦,这真是一群强盗!(走至萍前,抽咽)你是萍,——凭,——凭什么打我的儿子?
周萍:你是谁?
鲁侍萍:我是你的——你打的这个人的妈。
鲁大海:妈,别理这东西,您小心吃了他们的亏。
鲁侍萍:(呆呆地看着萍的脸,忽而又大哭起来)大海,走吧,我们走吧。(抱着大海受伤的头哭。)
侍萍看到自己的亲生儿子周萍,也就是周公馆里的大少爷,此刻正凶狠地殴打同胞兄弟,内心是多么的痛苦!那种欲认不能、欲罢不忍的心情是何等矛盾!作者巧妙地运用标点符号、谐音等手段把人物内心的痛苦、矛盾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总之,语文教学应该尽可能紧密地联系当前的文学研究,以文学批评家的眼光和姿态去拥抱和占有作品。把文学批评方法引进课堂,多方面、多角度地解读文学作品,为中学语文阅读教学增添新的视野。
参考文献
篇9
论文摘要:妇女的文学批评在魏晋南北朝进入了初创时期。首要表征在于从“人物藻鉴”发展为专门的文学批评,并出现了如《与妹刘氏书》等一批论著。特征之二是确立了一种明显具有女性特征的批评范式“以诗论诗,卒章见志”:东晋才女谢道韫以其形象化的批评方式深远地影响了时人及后人;早见于《诗经》的“卒章见志”在这一时期有了质的飞跃,两相结合,成为了一种时代风尚。
经历了从先秦至两汉的漫长滥殇阶段之后,妇女的文学批评在魏晋南北朝进入了初创时期,特征有二:其一,“文学批评”在“人物藻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初期带有较多的“人物藻鉴”的痕迹,后期则转向专门的“文学批评”,出现了如《与妹刘氏书》、《答程骏表上(庆国颂)令》、《答程均表上(得一颂)令》等一批论著;其二,确立了一种明显具有女性特征的批评范式——“以诗论诗,卒章见志。”
一、从“人物藻鉴”到“文学批评”
纵观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的文学批评,其中夹杂着相当多的“人物藻鉴”,更确切地说,“文学批评”就是在“人物藻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就具体发展过程来看,则大约经历了一个从“纯粹的人物藻鉴”到“在人物品评中包含对被品评者文学成就的评价”再到“专以文学批评为宗附带藻鉴人物”直至最终独立为专门的“文学批评”的过程。
汉末以降,女学渐衰,惟晋代稍隆,六朝妇女能文者多出缙绅之家,尤以两晋为最,如:晋左思妹左?薄⑿话仓杜?坏黎埂⑽勒古?李澹黄氡?彰帽?铌停涣毫跣⒋旅昧趿铈档龋唤猿鲧粕鹬?遥?痈感质芤担?⒂胁琶??藻鉴人物的风气既在社会广为流传,受父兄影响,女子也多有浸染,如:韩氏之观狐赵,钟琰之相兵儿,卫铄之赞曦之,道韫之叹王郎……眼观口赞之外,更有一些妇女干脆书之文字:左?庇小睹祥鹉冈蕖返仁?嗥?赜谙透救说脑薮牵?跎苤?小督?⑺獭贰ⅰ镀裟竿可剿獭罚?锴碛小豆?锓蛉诵蛟蕖菲渲械馁??叩笔糇?保??蟾攀堑谝晃蛔ㄊ氯宋锲菲赖呐?裕?醋髁恕冻哺富蒎?蕖贰ⅰ队菟炊??蕖贰ⅰ吨苄?踅?笤蕖返仁?嗥?薮牵?糜诟杷獭⑵兰圩怨牌??赜胁诺碌拿??K淙换?旧鲜谴拥赖碌慕嵌茸叛郏???园噫兼ニ?鳌肮?们?椤钡钠兰廴匆丫?缓笕耸幼髁宋难??馈G迦寺疥圃谄浼?嫉摹独???率?省分衅缆郯噫兼ナ彼档剑骸吧?鼓蕉?宦叮?乖谝盅镏?洹=?蠊箧?左??称其(班婕妤)恭让谦虚,可谓知己。”这虽然说的是人品与文品之间的关系,但显然更多是从文学的角度着眼的。
左?敝?螅???钗?忻?摹案九?寮?钡笔簟凹媚崧哿郊腋尽薄<媚崾?湫彰??渌档靡员4婺嗽谟谒?畚???酱蟛排?盒坏黎购驼判??谩4耸铝郊?凇妒浪敌掠铮?玩隆泛汀督?椋?坏黎勾?罚?杂幸焱?G罢呶?
谢遏绝重其姊,张玄常称其妹,欲以敌之。有济尼者,并游张、谢二家。人间其优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晋书》记载略有出入:
初,同郡张玄妹亦有才质,适于顾氏,玄每称之,以敌道韫。有济尼者游于二家,或问之。济尼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
《世说》的记载中,济尼所论基本上仍属“人物藻鉴”,《晋书》则明确指出济尼所论实为“才质”,这实际上已经是后世所谓的“作者论”了。谢、张皆文学名家,王、顾二妇又俱有才名,遏、玄各称其亲,不知孰胜,在盛行人物品评的时代中,难免有好事者想弄个清楚明白。问及游于两家的济尼,高下立判:张玄妹可以算作“闺房之秀”,谢道韫却不仅为女界之雄,甚至还超出了一般的男子。“林下风气”之赞已经把她和“竹林七贤”并列了起来,可谓评价甚高。
如果说左?敝?薷?嗟厥粲凇叭宋镌寮?保?媚嶂?劭?忌婕岸员黄菲勒呶难С删偷钠兰郏??妓?拐咝煸迤蕹率系摹队朊昧跏鲜椤吩虿徽鄄豢鄣厮闶侵泄?糯?九??钤丶?囊黄?显绲奈难??雷?郏
伏见伟方所作《先君诔》,其述咏勋德,则仁风靡坠;其言情诉哀,则孝心以叙,自非挺生之才,孰能克隆聿修若斯者乎?执咏反复,触言流泪,感赖交集,悲慰并至。元方伟方,并年少而有盛才,文辞富艳,冠于此世。窃不自量,有疑一言,略陈所怀,庶备起予。先君既体弘仁义,又动则圣检;奉亲极孝,事君尽忠;行已也恭,养民也惠,可谓立德立功,示民轨仪者也。但道长祚短,时乏识真,荣位未登,高志不遂,本不标方外迹也。老庄者,绝圣去智、浑齐万物、等贵贱、忘哀乐,非经典所贵,非名教所取,何必辄引以为喻耶?可共详之。文章从评论妹妹陈?(伟方)的《祭父文》人手,先是高度赞扬刘氏诔文的文学成就,“其述咏勋德,则仁风靡坠;其言情诉哀,则孝心以叙”,发出“自非挺生之才,孰能克隆聿修若斯者乎”的感叹;然后详细描述自己“执咏反复,触言流泪,感赖交集,悲慰并至”的读后感,对诔文的情感力量作了生动刻画;最后论及父亲的生平行事“体弘仁义,又动则圣检;奉亲极孝,事君尽忠;行已也恭,养民也惠,可谓立德立功,示民轨仪者也”,指出诔文动辄以老庄为喻的特点,质疑其不合“经典”与“名教”。可谓“专以文学批评为宗附带藻鉴人物”式的“文学批评”。撇开陈氏和刘氏对老庄思想认识上的差异不论,应该说,前述三点都颇为中肯,达到了相当的理论高度。晋代妇女能有这样精彩的批评文字,实属难能可贵。
南朝妇女善辨已然不争,而北朝亦有妇人能论,北魏文成文明冯后即为代表。据《魏书》记载,冯后“性聪达,自人宫掖,粗学书计。及登尊极,省决万机……以高祖富于春秋,乃作《劝戒歌》三百余章,又作《皇诰》十八篇”。这又是一个聪敏博学的多产作家,《魏书》以其文多不载,故而散佚。冯后文论见于答程郡的两篇《令》文:
省诗表,闻之。歌颂宗祖之功德可尔,当世之言,何其过也。所箴下章,戢之不忘。(《答程骏表上(庆国颂)令》)
省表并颂十篇,闻之。鉴戒既备,良用钦?。养老乞言,其斯之谓。(《答程均表上(得一颂)令》)
在前后相趁的两篇《令》文中,冯后表达了一个观点:“颂”之为体,若用于“歌颂宗祖之功德”,则不妨尽量夸张;但如若用于“当世”,则不能太“过”。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何把握“颂”体在“颂祖”与“当世”上的分寸。冯后之前,已有批评者涉及了“颂”体,如:《荀子·儒效》以为‘《颂》之所以为至者,取事而通之也”;《诗大序》给“颂”下定义为“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陆机《文赋》分文体为十类,认为“颂”的特点是“优游以彬蔚”……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到了“颂”这种文体的某个方面,得出了一些有益的看法。冯后的颂论则是在“颂”体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出现了期待解决的新问题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颂”最早是用于祭祖的,有所谓“取事而通之也”、“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颂”在社会生活中的用途也越来越广,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颂”,如:东汉以前有周公“哲人之颂”、左丘“变体野诵”、三间“细物之颂”、秦政“矜德之颂”、惠景“述容之颂”;至东京一代则有班傅之“变为序引”,马融之“雅而似赋”,崔(瑗)蔡(邕)之“致美于序,而简约乎篇”,挚虞之“杂以风雅,而不变旨趣”;以及魏晋有所谓“末代讹体”之“杂颂”。
在这个“杂颂”盛行的时代,冯后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如何把握“颂祖”之别“当世”的分寸问题。通过回答程骏所上表《庆国颂》和《得一颂》,冯后指出,“颂”用于“颂祖”和用于“当世”是有所分别的:“美盛德之形容”的“颂”尽可“敷写似赋”、“敬慎如铭”,怎么样赞颂都不过分。但是,当其用于“当世”用于庆国时,还是应该有所收敛、言称其事,否则只会给人留下“何其过也”的不良印象。当然,如果已经“鉴戒既备”,只是“良用钦?”,那么也是可以容忍的。应该说,这一见解颇为深刻,达到了相当的理论高度。后来刘勰撰《文心雕龙·颂赞》亦称:“容德底颂,勋业垂赞。镂影摘声,文理有烂。年迹愈远,音徽如旦。降及品物,炫辞作甑。”观其论,与冯后之《令》何其相似!我们不能肯定刘勰一定受了冯后的影响,但至少可以确定这一点:对在“杂颂”时代如何把握作“颂”的分寸这一问题,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上都名不见经传的北魏文成文明冯后先于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享有盛誉的刘勰,明确地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伴随着这些专门批评论著的出现,魏晋南北朝妇女的文学批评彻底脱离了“人物藻鉴”,而呈现出自主自觉发展的欣欣向荣景象。至此,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妇女的文学批评作为一个整体已初具规模,此后则伴随着文学史和整个文学批评史而发展,并以其独有的女性视角构成了对男性批评的有力补充。
二、“以诗论诗,卒章见志”的女性批评范式的确立
从体式上看,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文学批评的重要特征在于确立了一种女性批评范式:“以诗论诗,卒章见志”。这既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先秦诗歌中常见的“卒章见志”,也不等同于后世的“论诗诗”,而是一种以“诗”的面目出现于文末的“片言只语”式的批评。其确立大约是经过了“卒章见志”和“以诗论诗”两个独立的阶段,最后合成为一种在文学批评史上颇为独特的批评范式。
先说“以诗论诗”。
东晋“以一句诗名千古”的才女谢道韫不仅对文学有着独到的见解,还以其形象化的批评方式深远地影响了时人及后人,成为“以诗论诗,卒章见志”批评范式的一个源头。身为东晋著名文学世家谢氏集团的一员,谢道韫受家学浸染,对文学颇有领悟,并以其独树一帜的见解为后世所称道。据《世说新语,文学队《晋书·列女传》记载:
谢公因弟子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吁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叔父安尝问:“《毛诗》何句最佳?”道韫称:“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安谓有雅人深致。
《诗经》三百篇,佳句比比皆是,谢安以命世大臣的经学视野选出了《大雅·抑)中的“吁谟定命,远猷辰告”;谢玄则从文学欣赏的角度挑中了《小雅·采薇》中既是景语又是情语的千古名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唯独谢道韫捡选了出自《大雅·燕民》的“作者尹吉甫对自身诗作柔和动听、清美感人风格的自赞和寄寓情怀、抚慰人心写诗目的的申述”,与叔父、兄弟的见解均不相同,足见眼光独到。谢安称赞侄女“有雅人深致”,即是对她能够窥见诗歌的作用和艺术力量的高度赞赏。所谓“雅人深致”,当即《诗序》中的“主文而谲谏”。虽然这一思想并不新鲜,但称道《诗经》中不可多得的诗论却隐隐透露出谢道韫喜好批评的嗜尚。从谢道韫生平行事来看,她是雅擅辩论的:其人伦风鉴则有“王郎之叹”;文学批评则有“《毛诗》佳句”;名理清谈则有“柳、谢之辨”、“步帐解围”等;也因此才荣膺了“聪识有才辨”的断语。
不仅喜好批评,谢道韫还擅用形象化的文字进行批评,著名者即是被后人往往视作了诗歌的“咏雪联句”。此事两见于《世说新语·言语》和《晋书·列女传》,以《世说新语》为较详: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奕女,左将军王凝之妻也。
所谓“咏絮之才”即从此出。一直以来,人们都把它视作诗歌、名之为“咏雪联句”而大加赞赏,更津津乐道于谢道韫诗才胜过谢朗;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这句诗其实也是谢道韫从女性视角出发对堂兄谢朗观察到的落雪形象所作的文学批评。因为首先,谢道韫和谢朗的差别不仅仅在于表面上的才思敏捷与否,实际上更是一个男女两性观察角度不同的问题。宋人陈善《扪虱新话》卷三曾说:“撒盐空中,此米雪也,柳絮因风起,此鹅毛雪也,然当时但以道韫之语为工。予谓《诗》云:‘相彼雨雪,先集为霰’,霰即今所谓米雪耳。乃知谢氏二句,当各有谓,固未可优劣论也。”此论经常被人忽视,其实书载“俄而雪骤”,既说“俄而”,可知曾有一段米雪时间,故谢朗所说不谬。更何况下雪时如果雪很大,雪粒下降的速度就快,从男性的观察视角来看,一般会更加注重雪下落的力度,因而出现“撒盐空中”这样的比喻丝毫不奇怪。但身为一个小女孩,谢道韫从女性注重柔美的视角所观察到的飞雪形象就有所不同:雪花一片一片地从空中落下,又被风吹起,旋转、沉浮,就像同样因为被风吹起而在空中旋转、沉浮的柳絮那样自由自在而又轻灵地飞舞,这是一幅多么美妙的图画啊。由飘扬的雪到飞舞的花,再到同样洁白、轻灵的柳絮,这在女性的联想空间中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一件事情。于是“未若柳絮因风起”脱口而出。《晋书》记载“安大悦”,谢安乃至以后的文学批评家对这一句如此欣赏,除了诗句本身的新奇可爱,除了谢道韫以年幼而才思如此敏捷让人不禁心生爱怜;实在也包含了这些男性对来自另一个性别眼中不同于一般男性落雪思维的飞雪形象的认同。自此以后,把“飞雪”比作“飞絮”就成为了咏雪诗中的一种经典比喻,而这种比喻最初当是来自于女性的观察和体验的。
其次,谢安、谢道韫、谢朗是在“内集”的时候遇到“雪骤下”这一事件的。作为东晋著名的一个文学世家,谢氏集团的“内集”除了具备一般亲朋好友之间互相走访、嘘寒问暖的功能;更重要的还在于互通有无、交流思想,对文学现象和文学观念自发地做出评论并加以传播,所谓“与儿女讲论文义”是也。“咏絮之才”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谢安问:“(大雪纷纷下),像什么?”这是文学大家在考较自家子弟。谢朗率尔回答:“‘在天空中撒盐’差不多可以比喻了”,名门子弟的风范一目了然。而谢道韫从女性视角出发,对这种比喻有所不满,于是不甘示弱,立即指出“(空中撒盐)不如柳絮因风而起”。可见,谢道韫存心用“柳絮因风”的飞雪形象批评谢朗“撒盐空中”的落雪形象,“柳絮因风”不仅是一句诗中“名句”,也是一句以“诗”的面目出现的文学批评,“未若”一词的使用更加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据此,笔者认为在形象优美的诗句之外,把“未若柳絮因风起”视作东晋才女谢道韫从女性视角出发对其堂兄谢朗观察到的落雪形象所作的文学批评似乎也颇为适宜。
再说“卒章见志”。
所谓“卒章见志”,即在文的末尾表明自己的写作动机,这在先秦诗歌中并不少见。但在妇女的文学批评中,尤其是进入了初创期的魏晋南北朝,这种“卒章见志”发生了质的飞跃,在交待写作动机之外还反映对文学本质的认识。譬如,左?本驮谄淞绞资?衬┪脖泶锪恕靶醋髂宋?耸闱椤钡墓鄣悖
乱曰:骨肉至亲,化为他人,永长辞兮!惨怆愁悲,梦想魂归,见所思兮。惊寤号眺,心不自聊,泣涟湎兮。援笔抒情,涕泪增零,诉斯诗兮!(《离思赋》)
自我去膝下,倏忽逾再期。邈邈浸弥远,拜奉将何时?披省所赐告,寻玩悼离词。仿佛想容仪,唏嘘不自持。何时当奉面,娱目于诗书。何以诉辛苦?告情于文辞。(《感离诗》)这两篇文字都写于左?比牍??螅?独胨几场肥鞘苴??鳎?陡欣胧?肥谴鹦炙肌对?谩分?鳌K淙恍醋鞅尘安灰唬??捎诙际鞘惴⒗胨贾?椋??币蚨?诹狡?煌?奈淖帜┪脖泶锪送??囊桓龉鄣悖骸霸?适闱椤薄4酉惹匦砟路蛉俗芙岢龈九?醋鞯男睦砘?啤芭?由苹场笨?迹?九?奈难Ъ拔难??谰椭饕?刈拧爸髑椤钡囊宦龇⒄梗喊噫兼ヌ逦颉凹胰朔蚋尽敝?椋?嗾迅锌?澳焉峁释痢敝?椋?撕笸瞥纭笆ト酥?椤薄5搅艘怨刈⑷氲纳??咎逦?卣鞯摹叭说淖跃酢钡氖贝???痹虿皇?币说刂苯铀担盒醋髂宋?恕笆闱椤薄
左?笔?⒏持小白湔录?尽钡呐?婪椒ǎ?肷鲜鲂坏黎埂耙允?凼?钡男蜗蠡?难??酪坏┙岷希?芸炀统晌?恢址缟校?佣?妨⒘艘恢置飨跃哂信?蕴卣鞯呐?婪妒剑骸耙允?凼??湔录?尽薄4蟾糯酉惹乜?迹?九?拖不对谑?闹杏谩白湔录?尽钡姆绞嚼捶⒈砦难Ъ?猓?┤纾何号??獭陡疱稹罚?粕街?鳌栋彩馈罚?嗾研颂尽熬?印薄??阶?弊鳌独胨肌肥?场⒌黎褂健傲?跻蚍纭保?庖患记杀涞贸墒炱鹄础;蛐碛忠蛭?蟆⑿晃牟琶??皇保?胄忝?抡?刃Х拢??蚜街址绞胶隙??唬?佣?钩闪艘恢中碌呐?婪妒健W蟆⑿煌?焙鸵院螅?庖慌?婪绞铰偶?诹??九?奈穆壑小K?怯械氖阈醋约旱男醋鞫?????姆摺⒓幕车雀星椋?纾航??籼?卦?昶蘩钍稀兜躏?猩⑽摹罚骸傲募姆哂谒拐拢?伎犊??湃弧!苯?跞崞尥踣恐?痘乘几场贰爸卷痦鸲?冻郏??胨级?匮省1寺跷锒?埔疲?巫铀贾?研?聊临翰以寄怀,怅辞鄙而增结。”
有的反思古人作诗的方法,如:晋散骑常侍傅统妻辛萧《芍药花颂》:“惟昔风人,抗兹荣华。聊用兴思,染翰作歌。”晋王劭之《春花赋》:“诗人咏以托讽,良喻美而光德。”
篇10
摘 要:西方文论同语言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并直接体现语言学的内容。语言学的发展也深深影响了西方文论的发展。本文关注结构主义理论从语言学到文学批评的发展,主要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在结构主义文学理论中阐释诗歌文本的理论,和叙事理论这两个方面的发展来研究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在文学批评中的发展.
关键词:结构主义;索绪尔的语言学;文学批评;发展
[中图分类号]:G6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0)-15-0172-01
1.引言
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关联紧密。结构主义是一种具有跨学科性,开创性的理论,它质疑学科研究的现状,改变学科研究的对象与方法,力图建立科学化,独立化的人文研究。“结构主义通常是指一批以法国人为主的思想家的观点,他们在本世纪50、60年代受费尔迪南一索绪尔语言理论的影响,把结构语言学的概念运用到了对社会和文化现象的研究上。” 而结构主义所强调的不是某一时期在语言学和文学批评学科领域出现的理论新变而是这些理论新变之间的关联。这些关联就是借用了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包含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促使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形成一股用语言学研究方法分析文学问题的批评倾向。雅各布逊、热拉尔・热奈特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出了文学批评的理论原则。人们把这些理论主张与索绪尔的语言理论联系起来,强调二者之间的关联。雅各布逊等人的理论的价值不仅在于对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理论的运用,还在于其理论主张对文学理论新原则的创建以及开创了文学批评研究的新学科。这些结构主义文论所阐释的理论方法与原则和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理论之间有复杂的转化和发展。本文致力于从结构主义文论的阐释诗歌文本理论,叙事理论来研究语言学理论在文学批评理论中的发展。
2.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在阐释诗歌文本理论中的发展
受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影响,运用到文学批评领域的结构主义就是要建立一种文学科学。雅各布逊用文学材料来开拓语言学的新领域,创建语言学诗学以弥补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漏洞。索绪尔认为语言中任何一个要素的意义都取决于它与前后上下各要素的差异与对立,用他的话说:“在语言里,每项要素都由于它同其他要素对立才能有它的价值。”“他们的最确切特征是,他们不是别的东西。”这一观点启发了雅各布逊对诗歌语言功能的研究。雅各布逊通过自己的研究,对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做了重要的发展,在他的《语言学与诗学》中提出了对等原则理论。
言语的诗歌功能就是在言语展开的线性过程中,把对等原则从具有聚合关系的选择轴投射到具有组合关系的组合轴。对等原则所生成的诗歌文本具有明显的对称、对偶,诗歌文本正是通过突出表现语音之间、韵脚之间、想象之间的相似点,使语言变得丰富复杂。索绪尔提出的符号的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与雅各布逊所描述的语言运用上的相似性与邻近性是相连的:相似性对应聚合关系,邻近性对应组合关系。雅各布逊还进一步将索绪尔的理论与传统修辞学理论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建立在相似性关系上的语言符号选择是隐喻;邻近性关系上语言符号选择是转喻;诗歌以相似性为主突出的是隐喻,而散文以邻近性为主突出的是转喻。他把隐喻和转喻看作是语言的基本运作模式,并以隐喻和转喻为基础建立诗学分析的普遍模式。
雅科布森通过对组合聚合关系的改变来研究文学的诗性功能。他认为诗歌语言正不具有对外部世界的指向性,而是注重语言自身。通过对语言的分析,可以揭示诗句的组织特点。这一思想在现代对现代结构主义文本分析中具有启发意义。
3.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在叙事理论中的发展
结构主义理论运用到叙事文本,分析叙事,寻求叙事规则,突破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适用范围。但这种运用带来了叙述本身特质与结构主义理论的融合:突破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适用范围而开创了新叙事理论。
结构主义理论运用到叙事文本首先就是分析单元从符号向话语转换。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确定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对共时性的语言结构主义符号系统作了要素的切分与结构的分析。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只适用于语言的封闭系统之内,适用于它的语音层和单词层。而结构主义的叙事分析以划分叙事单元为基础。但与语言学理论以语词符号为基本单元是不同的,叙事分析中所划分单元大于语词符号。
结构主义理论运用到叙事文本是从普罗普1928年《民间故事形态学》对民间故事深层结构的分析中开始的,以功能作为民间故事的基本单位,功能就是根据人物在情节过程中的意义而规定人物的行动。后来热奈特认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是叙述话语。叙事分析都是以语言学模式为基础的,无论功能、神话素,还是陈述、话语都是大于语词符号的要素单元。他研究叙事与故事,叙事与叙述,以及故事与叙述之间的关系,所涉及的结构关系越出索绪尔语言的范围,是个体的话语结构。他所说的结构不仅依赖具体的上下文关系,而且还涉及社会生活背景。他所说的叙事分析离开了索绪尔的语言系统,进入话语世界。
叙事分析从语言结构发展到话语结构,适用了分析对象带来的变化。最初的叙事分析是适用的是个体性和创造性相对较弱的民间故事和神话等文本;而成熟的叙事分析适用的是个体性、创造性相对较强的现代叙事文本。叙事文本的个体性、创造性特点改变了结构主义语言理论。而结构主义语言理论运用到叙事文本研究对象从符号扩展到话语、从语言结构发展到了话语结构。
4.结论
在索绪尔语言学的影响下,结构主义文论重视对文学自身的研究,突出文学的语言意义,关注对作品语言和文学形式的研究,改变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原有的特点,形成了新的文学研究的基础理论。
结构主义理论从语言学到文学批评的转化,它并不是直接借用语言学的模式从而失去文学批评应该有的文学审美特性。相反,它是以关注文学文本的独特性为方向的,通过阐释诗歌文本的独特性和分析叙事文本的非语言学个体性、创造性形成叙事学原理。结构主义理论从语言学到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形成了新的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基础理论,它促成了文学批评的成熟与独立。
参考文献:
[1]卡勒: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P29
[2][3]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明凯译)[M],商务印书馆,1980年:P128,P163
[4]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申丹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巴尔特:叙事学研究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免责声明
公务员之家所有资料均来源于本站老师原创写作和网友上传,仅供会员学习和参考。本站非任何杂志的官方网站,直投稿件和出版请联系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