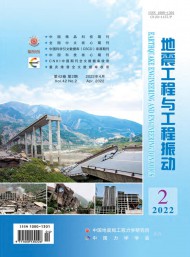铅笔盒里的争吵范文
时间:2023-03-17 11:39:56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铅笔盒里的争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天黑了,小主人回房睡觉了。铅笔盒的“肚子”里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首先,铅笔先生大声嚷到:“我在这些文具当中是最厉害、最有本事的,我能帮助小主人写字,还有画画,样样工作我都能干!”
橡皮大叔忍不住了嚷到:“我才不相信你样样工作都能干,我可比你厉害多了,我能把你写在本子上的字全部擦掉!”
尺子小弟也忍不住了喊到:“我能把所有的线条打的笔直笔直的,你没看见吗?上数学课的时候,小主人用我画图形,每次都画的漂漂亮亮的!”
这时橡皮大叔说:“这样吵也没有用,我们还是去问一问铅笔盒爷爷吧。”别的文具听了觉的很有道理,就听了橡皮大叔的话。
橡皮大叔推醒了正在熟睡的铅笔盒爷爷,他们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都告诉了铅笔盒爷爷,并问:“我们之中谁最有本事?”
篇2
我们学生每个人都会有一个铅笔盒,而每个学生的铅笔盒里都会有很多笔,铅笔、钢笔啦,等等。我也不例外,而且我铅笔盒里的笔还会“说话”哩!一起去看看吧!
早上,我上学的时候,书包里装着铅笔盒,我听见铅笔盒里瘦瘦的自动铅笔说了:“哎呀!挤死我了!可恶的消字笔你就不能往那儿一点啊!”“那里没空呀,所以我只能往这儿来啊。”消字笔解释着。从旁边又传来了高贵的钢笔的声音:“谁呀!打搅我的好梦!不想‘活’了!”一路上我就伴随着这些“小家伙”们的争吵声来到了学校。我放下书包,把铅笔盒从里面拿了出来,接着又把我最喜欢的钢笔拿出来用了起来,在写字的过程中,钢笔瞧不起的对铅笔盒里没有用的笔说:“哈哈!你们看看我,一天主人几乎都是用我写的字,看我多高贵,哼!”说完便用眼睛白了他们一眼。忽然,我有一个字写错了,拿出消字笔修改时,一支笔叹息道:“唉!从被买到现在,我一次也没有被用过呀!就算摸摸我也行啊!唉!”
到了下午,我从学校门口的店里又买了一支新的笔,我把那支新笔放进了铅笔盒里,那支笔便有礼貌地向铅笔盒里的笔打了声招呼:“你们好,我叫中性笔,以后请多多指教。”自从这只新的中性笔来到了我的铅笔盒里之后,原本多事儿的自动铅笔事也不那么多了,原本高傲的钢笔,如今也变谦虚了。
我明白了:原来一个懂礼貌的人,可以改变这么多以前有着许多不好的习惯的人。
六年级:王文鑫
篇3
突然,大家都听到一些声音:“我们的功劳是最大,”大家仔细一听,原来是骄傲的铅笔们不约而同地发言,“因为我们那高大的身体都被主人画得矮小了,还有我们的一些兄弟离开了我们,那么这个奖牌就属于我们铅笔一起戴的。”说完,铅笔们就把奖牌拿到自己那儿。
橡皮听了铅笔们的话,就怒气冲冲,就对铅笔们粗声粗气地说:“我的功劳才是最大,要不是我帮助你们纠正画错的地方,主人能得到这个画画优秀奖牌吗?这个奖牌应该我戴的,还有我那洁白的身子去掉了一大半,变得黑乎乎的。”话音还没有消失,橡皮就已经把奖牌抢过来并戴好了。
铅笔削听了橡皮和铅笔们的话,也怒气冲冲,就对它们两个也粗声粗气地说:“我的功劳不是最大吗?如果不是我帮铅笔们削好笔头,主人怎能画画呢?怎能得到这个画画优秀奖牌呢?这个奖牌应该我戴的。”话音刚下,铅笔削就把奖牌拿走了。
彩笔听了铅笔削、橡皮和铅笔们的话,比铅笔削更加怒气冲冲,就对它们三个更加粗声粗气地说:“我的功劳才是最大,如果不是我帮助主人涂上颜色,让画更加美丽,主人就不能得到这个画画优秀奖牌了,所以这个奖牌应该是我戴的。”说完,彩笔就把奖牌抢过来。
谦虚的尺子和又美丽又香的圆珠笔不约而同地说:“大家都各有各的长处,也各有各的短处,正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大家的功劳都一样,不如大家一起戴,不要再争吵了。”
篇4
铅笔、橡皮、转笔刀 广东省深圳 蚝业小学五(3)班 陈嘉瑶 一天深夜,小主人小花睡觉了,铅笔盒里响起了吵闹声。
铅笔说:“今天真把我累坏了。”矮小的橡皮争辩说:“你累坏了,我才不信,我常常给小花擦去错别字,我的功劳最大。”转笔刀抢着说:“我的功劳可最大了,无时无刻地飞速旋转着,使我的外表都弄脏了,没有以前那样漂亮。”橡皮说:“我也是呀!被小主人擦得脏脏的,这里一块黑,那里一块黑。”铅笔笑着说:“噢!原来你们俩这么可怜呀!,而我这瘦小的身体却安然无事。”橡皮说:“铅笔,你的身体不是矮了吗?还说安然无事。”转笔刀凶恶地说:“铅笔,我以后要把你刨成越不越短,让你消失。”铅笔说:“你真想得美呀,想让我消失,真难了,你想想怎样对付橡皮吧。”橡皮说:“铅笔,如果我不帮你擦去错别字,你们俩可没什么作用了。”它们一直没睡,它们一直争吵着……
有一天,笔盒里来了一位新朋友——尺子。尺子对它们说:“你们为什么要吵呢?你们这多年的友谊就这样毁掉了,这值得吗?你们还是和睦相处吧,如果大家不相互帮助,是克服不了重重的困难。”大家听了尺子的劝告,都再次做回了好朋友。 指导教师:曾冬莲
[推荐给朋友] [显示打印]
篇5
夜幕初垂,我躺在床上睡得正香,突然文具盒里发出了激烈的争吵声。
“我的身体非常漂亮,有许许多多的花纹,小主人每次画画,写字都用我,你们谁也比不过我。”铅笔骄傲的说。
听了这句话,一向憨厚的橡皮就不满意了,它撅了撅嘴不乐意的说:“谁说的?每次你写错字都是我帮助你的,小主人应该更喜欢我!”
“凭什么?每次小主人写那么漂亮的钢笔字,还不都是我的功劳啊?为什么说小主人更喜欢你?”钢笔气汹汹地说。
小尺不服起了:“小主人每次连直线都离不开我!你们这群主人不喜欢的家伙!”
篇6
说起我熟悉的人,有好多,邻居中的,幼儿园的,小学里的。但是,我最熟悉的人,要数我过去的同学——徐倩了。
徐倩和我个子一样高,两只大眼睛嵌在一张红润的脸蛋上,高鼻梁,好看极了。从一年级开始,一条友谊的锁链就把我和徐倩连在一起。我们之间从未发生过争吵,互帮互助,亲密的简直像一个人。
记得有一次期末考试,还有几分钟就要开始了,同学们都在都在做着考前准备,我一翻铅笔盒,忽然发现尺子忘记带了。“没有尺子,那行呀?回家去取一定来不及。”我急的真是要哭了,这时,我的好朋友徐倩看见了,便走过来,问我:“梦婷,怎么了?”我心急火燎的说:“都怪我,偏偏在这个时候忘记带尺子了。”徐倩看我急成这样,便毫不犹豫地跑回自己座位上,只听见“啪”的一声,我回头一看,只见徐倩手里正拿着两段折断了的尺子,她将一段递到我手里,我愣住了“啊!多美漂亮的新塑料尺呀!”我深情地望了望徐倩,手里握着那段尺子。不知说什么好。她呢,冲着我微微一笑,说:“快拿去用吧。”这时,上课铃响了,我赶紧回到座位上,等待着考试。
放学回到家,我从铅笔盒里拿出那半段尺来,想欣赏一件珍品,爱不释手。我决定把它珍藏起来,因为在那短短的半段尺子上凝聚着我们之间的深厚友谊和徐倩那永远值得我学习的助人为乐的好品质
篇7
“动脉硬化、耳鸣、左耳失聪……”医生一边飞快地在病历本上记下一堆蓝色的字一边轻轻地说,母亲频频点着头,照常锁着眉头。这样的表情是我熟悉的,从三十几岁开始,她的眉心就有重重的皱纹。她紧紧盯着医生翕动的嘴唇,目光惶恐、谦恭、小心、虔诚。她未必信赖他,但是她会身不由己地被对方的权威所左右,像个孩子般盲目。
透过百叶窗帘,我看到窗台上有两钵茉莉,白色的花一簇簇地从叶子里钻出来,淡淡的香糅合着正午的阳光,热辣辣地晾在窗台上,白得耀眼,白得心神不宁。
“好了,先吃这几副药,以后有什么问题再来找我。”医生合上母亲的病历,抬头微笑着对我说。他是我的熟人。我向他道谢并告辞,母亲也跟着道谢,她的声音跟在我的声音之后,像一味中药,厚朴,还有些歉疚―――我们没有排队便直接享受了诊疗。
在医院门口,我要母亲打的回去。在这个城市,打的便宜得要命,让我每次都有赚到了的感觉。
母亲不肯,她坚持要走二百米路到车站坐车。我没有坚持,我说服不了她,就像她说服不了我一样。
“那我有事,先走了,你过马路小心。”我向她道别,转身向街对面走去。我从来不触碰她,从来没有挽着她的手逛过街。告别也是这样,无论我到哪里去,去多远,有多久,都是两人站在刚好听得见对方声音的地方,干干脆脆地说完话,然后转身离去,像两根同极的磁铁,一碰就紧张地弹跳开。
我走得很快,我知道母亲一定在看着我,审视地,刻骨地看着我。我的脊背中央有一根线热辣辣地炙痛起来,像搁在放大镜焦点下的火柴,噗地一下燃烧,火焰迅速蔓延到全身。
我经不起她这样看,小腿肚子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二
我穿着一件白底蓝花的棉布短袖娃娃衫,白色的超短裙,黑瘦,头发总有梳不平的绒毛,扎成一把马尾。我不漂亮。那年流行白色超短裙,每个女孩子都有一条。我的这条套上身时夏天已经过去了一半,而且它是母亲用化纤料子自己裁剪缝制的,和棉布上衣很不协调,经不起近距离的审视。
但我只能这样,母亲很少带我到集市买衣服,十四岁前我的衣服都是姨妈们买来送我的。母亲也很少给自己添置衣服,穿来穿去似乎总是那么几件。她有件淡绿色的衬衫,压在箱子底,放了很多年。我记得她穿那件衬衫的样子:扎着两根粗黑的短刷子辫,白嫩丰腴的手腕从淡绿的袖子里伸出来,散发出上海牌雪花膏的香气。
记得我对她说,妈妈,等我长大了把这件衣服给我穿吧。她听了咯咯地笑,用火钳夹着蜂窝煤往炉子里送。那年,我五岁,她二十九岁。
后来,她拿出那件衬衫给我,我看了看,说,现在谁还穿这样的领子,尖尖的,又大又笨。
她不会打扮自己,也不会打扮她的女儿。有时,母亲参加工会组织的旅游,带回来一大包七零八碎的衣裙和布料,热热闹闹地分给我和她的姊妹,但对当时极度需要好看衣服的我来说,还是没有一件合适的。
我和她天生就有距离。这一点也许在她哺乳时就感觉到了,襁褓里的我总是哭,折腾得她整夜不能睡。她恨得把我丢到摇篮里,任我去哭、去嚎。可随便谁抱了我,轻轻地走几步我就不哭了,只是一到她怀里,就又开始哭、嚎。
三
穿白色超短裙去上学的那天我来“好事”了。
我一直知道会有这一天。班上的女生几乎全都来过“好事”了,她们神秘地笑着,小心地,隐秘却又张扬地,从书包里掏出一包东西,飞快地跑出教室,直奔厕所。然后回来聚在一起叽叽喳喳,说着说着,就有几个人小声地笑起来。上体育课时,体育老师问哪些同学需要休息,她们就高高地举起手,在男生复杂的目光中,走到走廊下休息。
比起她们,我似乎是棵晚熟的植物,跌跌撞撞地跟在她们后面,听她们说班上的某某很帅,某某的“好事”来得很早。她们个个比我高大,肤色匀净,像上了釉的桃子,胸脯微微地隆起,从背后的浅色衬衫里,可以清晰地看到白色棉布小背心的痕迹。
而我,一直没有这些迹象。
也许有的,洗澡时我已经感到胸脯隐隐地痛,里面有小小的核。我为之恐惧、羞耻,我想也许我要死了,得了某种难为情的绝症。但我没有告诉母亲,我为我身体的一切守口如瓶。因为就只是一张纸条,一张夹在铅笔盒里的纸条,让我挨了她结结实实的一巴掌。那纸条上写着:“我喜欢你,星期天去看电影好吗?”
那天,几个女生把我拉到墙角凑着耳朵对我说,“你的裙子,你的裙子搞脏了!”说完,她们吱吱嘎嘎地笑起来,脸色潮红。她们真的很想体贴人,但看到意外发生,还是忍不住地兴奋,有一点幸灾乐祸的快乐。我扭头望去,我的短裙上绽开两朵殷红的喇叭花,像雪白底子上打横画了两块水墨重彩,鲜艳夺目。我的头轰地响了一声。那天下午,我走过操场,一大帮高年级同学在打篮球;我走过三四条走廊,不时地碰到一群一群的男女学生。回想起他们的笑声,还有对话,肯定是冲着我的。
我将身子紧紧贴在墙上,无地自容,最糟糕的是我的书包里除了一堆课本,什么也没有。
当时我窘迫得想去死,想从高高的五楼跳下。
四
为这点事去死肯定是矫情的。但我真的无数次想过去死,死给母亲看。
她从不夸我,走亲戚时,总对亲戚说我又懒又笨,什么也不会。我讨厌她看我的目光,黏稠、阴冷、厌烦,像把带锯齿的刀子,一下一下剜着我单薄的身体。她同样厌恶我看她的目光,她无数次说过:我像地坑里的老鼠,看人的样子又狠又毒。
我多年后想起她这句话,发现她一直是了解我的。那种地坑里老鼠似的眼光,斜的,悄悄地瞟一眼过来,又瞟一眼过去,看似没有来由,其实都在心里暗暗地下了套子。这无疑是令人厌恶的,我那瘦小干瘪的身子里藏着这样不光明的神色。
阳台上的茉莉花蓊蓊郁郁地开着,家里总是养这种植物,大概因为它容易活。
它的香在阳光里热烈地喷发着,屋子里卫生间的水哗哗响,母亲边洗衣服边哭。她的声音毫不掩饰地响亮。这次加级她又没有加上,上次是说她参加工作的年限不够,这次是说她学历不够。母亲觉得委屈,她说她是中等师范毕业生,虽然是半工半读的三年,但是以年级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去的,凭什么比不上那些初中毕业跑去夜大进修两年拿到文凭的老师?凭什么不能让她代课?她抽泣的鼻息声和着哗啦啦的流水声、搓衣板一下一下撞击在木盆上的咚咚声,让人感到又刺耳又羞耻。
我趴在阳台上将脸埋在茉莉丛里,深深吸气,吐出来的却是灼热的白气。把这种粉白的小东西捏在指尖,稍稍一用力,就成了一抹蔫黄的汁液。我看到楼下的老妇人走出院子抬起头往我家张望。
母亲好像以为只要走进这两室一厅,门一关,就可以肆意发作了。她大声地咒骂我,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大声地喝斥父亲,摔扫帚,摔她的先进工作者荣誉证书。
我越来越多地与她顶嘴,与她争吵。她操起细竹条子劈头盖脸地打,我不逃,拼命地忍住不哭,直到她打累了,或被父亲拉走。
她的脾气越来越坏,当着亲戚的面,当着同学的面,恶毒地骂我。
我爬上高楼时总会有意地扒住边沿往下看,我想象的死亡总是和跳楼有关,只有这样才能最快、最直接地在母亲一声尖叫还来不及出口的时候从她眼里消失。我积极地准备有一天,在她的暴怒煽起了我足够的勇气,就那么跳上凳子,跳上桌子,然后从窗口一跃而下。
五
偶尔我们会结成同盟―――母亲要我跟她一起去书记家送礼。
我拘谨地坐在书记家黑色人造革的沙发上,瓦数不足的白炽灯光昏昏欲睡地罩在头顶。母亲坐在身边,对着书记絮絮说着那些缘由,她的神情和若干年后,我带着她去看病时一样,惶恐、谦恭、小心、虔诚。她对领导总是本能地害怕,像看待父辈一样敬畏。书记是个秃顶的矮胖老头,他沉着脸埋在沙发里一直耐心地听母亲说,不插话,最后吭吭地咳了几下说:“你的问题组织上会考虑的,是比较遗憾。但是,你还年轻,以后还有机会,这次的几个老同志情况比较特殊,如果这次他们评不上,以后就没希望了。”母亲的眼睛黯淡下来,她不知道该怎样继续,她更说不出“按原则办事”之类的硬话。
回来的路上,我在前面,她在后面。一路上我们没有说话。
她始终是单位职工庞大队伍里的一粒石子,随时可能搬到这里,填到那里。母亲继续兢兢业业做着她厌倦的一切,年年领着先进工作者的荣誉证和十五块钱的先进工作者奖金。
她愈憎恨我,我地坑老鼠式的恶毒愈激烈,我口齿清晰地指责她:没用,没本事,只会在家里横,像头丧失理智的母兽。
开联欢会时,她在单位里给一帮青年工人倒水泡茶,也是我鄙视她的原因。
“那么多人,水瓶就在桌上,谁要喝谁倒,你为什么要去给别人倒茶?”
“这有什么关系?”她肯定会说。
她不知道,在学校,一个出了名的调皮男生往我抽屉里扔鞭炮,我冲上去啪啪给了他两耳光。那个男生愣了一下,醒过神来,狠狠地还我一掌,我飞出两米之外,鼻子重重地撞在课桌腿上,血呼地流下来。我爬起来,向那男生走去,他又给我一掌,我又飞出两米之外,我再爬起来,抹了一把鼻子,血粘了满脸,再走过去。其实我真的不明白我一遍遍向他走过去是为什么,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我只是傻傻地爬起来,向他走过去。那个男生被其他男生抱住了,他们诧异地望着我,望着我皱巴巴的,糊满汗水、灰土的衣服,还有脸上纵横的血。我奇怪地没有哭,站在课桌前,望着那个男生。那个男生奇怪地笑了,回到他的座位安静地坐下。而我,哭了。
我知道我的父母不会冲到学校,揪出这小子,拽到教导处,或者干脆掴他两耳光。他们不是这样的人。而我呢,我是怎样的人?
六
“茉莉花开了。”母亲手里捧着一小撮白花走到我面前,她的手心掌纹深纵,指节粗大肥厚。她已经是个往衰老里去的妇人。她的皮肤依然白皙,但已经是干燥失水的橙子。
家里还是种着茉莉,数量一年比一年少,除了母亲,什么时候开花没有人关心。我就着母亲的手掌看了一眼,淡绿的须状花托,脆弱得稍一用力就与白色小花冠分离了。淡淡的香,它从来没有淡出过我的记忆。
母亲把花撒进茶杯里,茶几上摊着我给父母签的夕阳红旅行团人身保险保单。她看我的目光成了已经磨去锯齿的刀子,只有背没有刃。随着她的衰老、病痛,她似乎越来越默认我的悖离。
她的一切我都要颠覆。我咬着牙对自己说。她在人前说不出话,不会应酬、不会客套,我在人前滔滔不绝,似乎没人能让我害怕;她退让,我攻击;她隐忍,我嚣张;她厚道,我刻薄。总之,我否定她的一切。我竭力地改变自己,改变骨子里她渗透给我的东西。
我从不向她诉苦,尽管我的日子并不比老实巴交的她好过,尖锐和迟钝都是容易受伤的品质。她跟我说起谁谁可怜,我就不耐烦地打断她,“还有比你更可怜的吗?”很多次,她被我激怒了,叫我“滚”,我冷笑着,立即“滚”。然后,她又害怕了,打电话叫我回来。
我穿出大半截肩膀的衣服,脚趾甲上涂着蓝色指甲油。她看了不满,却不说。她看我赤着脚在地板上走来走去地听电话,笑嘻嘻地和对方说三道四。她警惕地问:“是谁?”我总是挑衅地,毫不在乎地回答:“喜欢我的人呗。”
她对我的嚣张无能为力。
一天,她看着我在镜子前梳弄头发,突然说:“你长得像外婆。”我停住手,她在镜子里我的背后望着我。我笑了,我早知道这个秘密。我说:“那我会不会跟外婆一样苦命?疯了,然后死在外面?”母亲“呸”了一声,眉心的皱纹迅速地拢在一起,重复从前那种凶狠的样子,狠狠地说:“哪有苦三代的?苦我们两代就够了。”
她终究是我母亲。我的鼻腔有点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