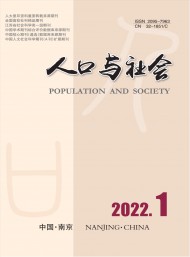人口红利的含义范文
时间:2023-12-25 17:36:48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人口红利的含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引言
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是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设计,人口结构发生了转变,我国目前已处在劳动力供给丰裕时期的末尾。对于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的影响的相关研究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其中人口红利的研究成为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所谓人口红利就是指人口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人口年龄结构的优势导致比较高的劳动参与率,所产生出来的对一国的经济增长比较积极的效应,包括储蓄率上升,人均消费提高等。
本文就是基于这样的研究背景,对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详细的分析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达到对未来经济增长趋势进行预测的目的。
2.文献综述
随着经济的增长,关于人口红利的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都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其中Sarah Cook(2006)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与经济结构和人口转型相伴而生,人口的年龄结构对经济的增长有非常重要意义。而在人口红利是否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这一问题,不同专家学者持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蔡昉(2009)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正是得益于人口红利的持续增长。他甚至经过详细的分析研究得出,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优势的存在贡献了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均GDP。他还认为,我国人口红利的存在还能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近20年的增长空间。而王德文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与人口红利具有某种默契关系。正是因为在人口红利发展的最佳时期,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就人口红利推动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和经济市场化发展而言,中国目前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可能离开人口红利的巨大作用和良好的发展时机。另外,车士义(2011)通过验证劳动参与率的扩大与经济负面影响的关系,进一步证实了人口红利的发展给经济增长带来的推动作用。在他的试验中,已经对第二次人口红利与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某种预测。他认为在第二次人口红利时期,必须将劳动参与率维持在较高水平,才能削弱人口负债的片面影响。而侯东民(2011)认为,正是由于通过人口红利使得经济结构的调整有了充分的准备时间,才使资本递减速度减少。因为,在我国改革开放时期,人口负担也最重。这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国家压力,使国家能够有更多地资金和精力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去。与多数学者认为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不同。
聂鹏(2011)则对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人口红利是促进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原因,并且强调发展外商投资促进经济发展。郭琳(2011)则利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劳动参与率是影响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影响人口红利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之一。强调应该需要积极采取措施,提升我国劳动参与率,充分发挥人口红利的作用。此外,石海峰(2012)利用实证分析的方式论证了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且强调,在充分把握人口红利效应的同时,应加强产业结构转型,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
但是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我国人口红利在一定意义上也不利于经济发展。如Schultz(2005)认为,我国当期储蓄和年龄结构之间存在着重大依赖关系。而Johnson(1999)则对生育率的下降提高了中国储蓄率持怀疑态度。穆光宗(2008)研究认为,人口红利对于发展经济而言,只能说是增加了一个可能性,具体说推动作用还比较牵强。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依照国际通用的Mason(2004)为代表。以实际的抚养比值域的变动研究第一人口红利。该抚养比表示为:即有效生产人口同有效的消费人口之比。其中有效生产人口是通过对历年的分年龄劳动生产率进行加权计算而获取。有效消费人口是则是通过把历年的分年龄消费水平通过加权计算而得到。如果分年龄劳动生产率同分年龄消费水平同时被确定,那么就会得出固定不变的有效劳动人口人均产出。在假定前提下,人口红利就成为经济活动盈余的影响指标。但是在国内的研究中,大部分的研究也采用了抚养比的指标,但是在指标含义反面略有不同,国内的抚养比指标则采用了人口负担系数来表示。其计算方法则是有老年人抚养比和少年抚养比只和构成。其中老年抚养比则是指65岁老人占劳动人口(15-64岁)的比率。少年抚养比则是值14岁以下人口占劳动人口的比比率。
3.与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首先,劳动参与率与人口红利不仅在经济学方面存在一定的联系,同时,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在国内的研究统计中,通常把经济活动人口作为劳动年龄人口的一个近似替代,因此根据劳动参与率的公式可以看出,只有劳动参与率保持较高,其劳动年龄人口优势才能充分发挥,进而才能实现人口红利。因此,在衡量人口红利的时候,可以把劳动参与因素考虑在内。其中劳动参与率的计算公式为:
(公式 1)
其中ER表示劳动参与率,PR表示经济人口(就业人口+失业人口),P15表示15岁以上的人口
其次,通过上文的文献综述可以看出,国内的研究把人口负担系数作为衡量人口红利的指标,并且把人口负担系数也成为抚养比。在本文对于研究中,采用了总抚养比的方式来表示人口红利。
(公式2)
其中F表示人口红利。表示老年抚养比,即: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与15~64岁人口数量的比率。表示少儿抚养比,即:14
岁及以下人口数量与15~64岁人口数量的比率。
最后,在衡量经济增长效果的时候,本文选用了GDP作为衡量指标。其中关于各个指标的含义和选取区间如表1所示:
表1 模型变量选择及数据处理
指标 替代变量 数据 数据来源
变量名 符号 区间 频率
经济增长水平 GDP GDP 1995~
2011 年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11》
劳动参与率 ER ER
人口红利 F F
其中,在实证分析之前,由于数据序列是时间序列,因此需要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排除经济序列伪相关给统计结果带来的影响。
在进行平稳性检验过程总,本文利用了ADF单位根检验法,其中详细的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序列的ADF单位根检验
变量 检验形式 ADF
统计量 临界值 P值
1% 5% 10%
GDP (c,t,1) -2.5225234 -4.107976 -3.481567 -3.168632 0.3131
ER (c,0,4) 0.320534 -3.542056 -2.910034 -2.592611 0.9722
F (c,t,1) -2.650445 -4.107965 -3.481545 -3.168621 0.2645
DGDP (c,0,0) -5.592443﹡ -3.53654 -2.907644 -2.591346 0.0000
DER (c,0,3) -7.428734﹡ -3.542056 -2.91005 -2.592623 0.0001
DF (c,0,0) -4.816367﹡ -3.536585 -2.907635 -2.591342 0.0002
注:检验形式为(c,t,k),其中c表示截距项,利用t对趋势项进行表示,利用k对滞后项进行表示。变量序列的一阶差分利用d来表示。
通过对检验结果的分析可以看出,在1%的显著性水平条件下,其变量GDPP、ER、F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一阶单整关系。即三个变量是一阶差分平稳序列。
通过单位根检验可以看出,四个变量是一阶差分平稳序列。符合进行协整检验的条件。因此,利用VAR模型的最大似然估计法对模型进行协整检验。
利用协整检验可以看出,显著性水平为5%的条件下,非贸易部门的就业情况以及贸易部门的就业情况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三个序列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详细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dGDP、dER、dF协整检验结果
协整向量数目 TRACE检验值 迹统计量 5%显著性水平 P值
0 0.48545 24.5621 23.7850 0.0012*
1 0.42565 16.5656 15.4123 0.0425*
2 0.34256 12.2568 11.2562 0.0045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三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和协整关系,符合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条件,因此对人口红利和增长之间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得到检验数据如表4所示:
表4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Granger结果 Granger原因
dGDP dF
H0 n.a.
dGDP x2 n.a. 12.57428
P n.a. 0.0026
H0 n.a.
dF x2 0.126392 n.a.
P 0.9567 n.a.
注:H0表示列变量不是行变量的Granger原因,P值是根据Wald系数检验X2统计量计算出的相伴概率。
注:显著性水平为1%。
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可以看出,在显著性水平为1%的情况下,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经济增长却不是导致人口红利Grander原因。进而得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的结论。
4.结论和对策
4.1 研究结论
通过上文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经济增长却不是导致人口红利Grander原因。进而得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的结论。说明人口红利的存在切实的促进了GDP的增长。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GDP的增长对人口红利的却不存在显著性影响。
4.2 建议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人口红利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的发展,人口红利也逐渐的在小时,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的经济的增长步伐。但是本文只考虑到了人口红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未对其他要素进行考虑,尤其是在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的环境下,人口红利的消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会被其他变量的变化所抵消。因此还需要客观的看待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
首先,充分利用现有人口红利,发挥经济增长比较优势。虽然本文论证了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且可以预测代未来人口红利的发展趋势,但是人口红利消失的过程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甚至有专家断言,我国人口红利还将继续存在大约5—10年的时间。这就说明,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人口红利仍然能够为下一步我国的经济法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和条件。也必然会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发挥自身不可多得的优势。我国政府必须正视这个因素,并且在提高就业率和确保产业结构调整、挖掘劳动力潜力方面充分利用这个条件。同时,人口红利的存在也要求我国政府在努力提高就业形式和就业率的同时。必须不断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加大对就业培训力度的投入,不断地做好各类人才和各行各业人才的吸引和利用。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人口红利的潜力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潜力。这种转移潜力目前正受到城乡体制与诸多限制城乡劳动力转移等制度的影响。因此,加快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步伐,进一步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不仅仅有利于转变城乡二元结构转变,更有利于人口红利的充分利用。
其次,为了避免人口红利带来的消极影响,我国应该加快产业升级,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抵消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消极影响。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促进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使得劳动力更多的像高附加值的二、三产业流动。进而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
参考文献:
[1]Sarah Cook. Structural Change,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Asia:Pathways to Inclusive Development[J].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2006,24(s1):5l-52.
[2]Sanchez,Eugenio Camus-Fernando,2005. AFP: A Three-letter Revolution,Edited by Juan Ariztia (Santiago:CIEDESS).
[3]蔡昉.劳动力短缺:我们是否应该未雨绸缪[J].中国人口科学,2009(6).
[4]聂鹏.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J].中国市场,2011(13).
[5]郭琳,车士义.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1(09).
[6]石海峰.人口红利、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J].琼州学院学报,2012(19).
[7]穆光宗.中国的人口红利:反思与展望[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
[8]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J].人口研究,2004(02).
[9]蔡昉.“人口红利”消失的隐忧[J].中国企业家,2006(07).
[10]侯东民.国内外思潮对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及老龄化危机的误导[J].人口研究,2011(03).
篇2
[关键词] 制度变迁;生育决策;经济增长;综述
[中图分类号] F0 [文献标识码] B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经济维持了高速稳定的增长态势,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而这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与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众多的劳动人口为我国经济增长做出了极大贡献。根据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人口红利”效应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人口老龄化”作为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一个突出现象,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成为了许多经济学家的研究内容。不论是“人口红利”还是“人口老龄化”都与我国的人口控制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近些年来出现的一系列人口现象都与我国的人口政策,特别是计划生育政策有着密切的关联。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观点,不同的制度安排决定着不同的经济绩效,从而影响着人类的行为方式。可以说,制度是至关重要的。
在我国,计划生育制度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其对于人口变化和家庭生育决策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很多经济学家也探讨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这一影响途径是用人口作为中间变量的。近些年来,新家庭经济学的兴起,特别是用微观经济原理解释家庭生育决策的方法和成果的广泛传播,为研究家庭行为提供了很好的工具。
另外,近一段时间一个被广泛讨论的名词――“失独家庭”,也是本文写作的背景之一,所谓“失独家庭”是指独生子女由于出现了各种意外伤亡,而其父母不再生育或收养子女的家庭。可想而知,这种状况对于家庭是多么沉重而残酷的打击。而且根据有关机构的估计,目前我国至少有100万个“失独家庭”,且每年以7.6万个的数量增加,由此可见我国目前的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的脆弱性和复杂性。不仅如此,计划生育制度实施以来,虽然促进了我国向低生育率的转变,为经济增长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也给社会带来了诸多问题。因此,面对这一问题,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分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应该继续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另一种认为应该逐步放松,甚至取消计划生育政策。
二、生育决策理论相关研究综述
家庭生育决策理论是人口理论中的一个重大主题,而经济学对于人口问题的关注则由来已久。众所周知,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是一个典型的双向关系,人口变动对于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而经济发展又推动着人口结构和数量的转变。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的一门科学,而家庭作为经济的微观主体之一,更是经济学家所重点关注的领域,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家庭活动则推动了一门新的学科,即“新家庭经济学”。新家庭经济学主要研究家庭生育决策;家庭成员的就业决策与劳务分工;以及家庭组织经济问题等。因而,生育决策理论作为新家庭经济学的一个核心主题,得到了经济学家们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并建立了若干种家庭生育决策理论模型,用以解释经济发展中的生育率变化以及不同经济条件下的家庭生育决策。
在家庭生育决策研究中被广泛使用的理论主要包括:莱宾斯坦的“边际孩子合理选择”理论,贝克尔的“数量质量替代”理论,卡德威尔的“财富流”理论,以及伊斯特林提出的“生育供给与需求模型”和“生育率临界假说”。
这些年来,面对国外学者对于生育决策问题不断涌现的学术成果,国内学者依据本国国情,也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解释和学说。李小平(1992)提出的“期望孩子效用”概念,他认为父母的生育意愿取决于孩子带来的期望效用,而非实际效用,政府可以通过降低孩子的期望效用来降低父母的生育意愿,从而达到降低生育率的目的。彭希哲和戴星翼(1993)提出了“风险最小化原则”,他们认为风险最小化原则表明我国农村地区夫妇决定是否再生育子女时,其内在的动机是为了分散风险,即通过选择生育数量来规避风险,使风险得以减弱。应当说明的是,风险最小化原则和效用最大化原则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风险最小化原则可以用效用最大化原则的函数式表示,但其最明显的区别在于政策含义,风险最小化原则要求通过降低风险来降低家庭的生育意愿,国家对少生的家庭进行补偿,然而效用最大化原则要求通过提高孩子的成本或降低孩子的效用来降低生育意愿。对于我国落后的农村地区而言,风险最小化无疑更为适用。
周双超(1996)则认为传统的成本―效用理论忽视了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孩子对于家庭的效用是不同的这一事实,他认为孩子对父母的效用主要包括享受效用和必需效用,而父母对孩子的需求主要分为奢侈需求和基本需求,因而,当孩子是奢侈品时,父母对孩子需求的弹性较大,当孩子是必需品时,父母对孩子需求的弹性较小,因此,对于我国落后的农村地区而言,父母对孩子的需求是基本需求,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父母对孩子的需求趋向于向奢侈需求转变。
经典的西方生育决策理论提供了一整套用于研究家庭决策行为的工具和视角,但是它的运用建立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基础上,一般的基本假设包括:家庭生育决策以追求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家庭中的个体均为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每个家庭中的个体是完全自由的,其对于出生人数和出生间隔完全可以自主决策和控制;孩子既是一种耐用消费品,又是一种生产物品,他具有消费性和生产性;市场环境是完全竞争市场,即商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是完全竞争的。经济形态为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关系高度发达且无处不在。
只有满足以上的假设条件,其通过模型得到的结论才能够成立,显然,对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中国来说,其假设条件并不完全满足。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庞大的13亿人口,市场经济制度远未建立完善,且在广大农村地区,商品经济远未成熟,收入水平还较为低下,存在着自然经济的残留思想和观念。因此,简单的套用西方经典理论是切不可行的。在研究过程中,需要注重本国国情,从实际出发,灵活地运用和吸收西方生育决策理论,注重不同的假设前提,借鉴分析方法,从而得出符合我国实际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我国的家庭决策和家庭活动具有一些特殊且重要的特点,例如:①父母一般会抚养子女到成家立业为止,即当子女完婚后才会真正脱离父母抚养,因此,家庭抚养子女的时间要长于西方国家。②家庭养育子女成本的内容比西方国家要多,除了一般的费用,通常还包括买房,结婚等费用。③具有浓厚的“养儿防老”的传统,子女的保障效用极为重要,这源于深厚的传统思想观念,较为落后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家庭养老”的传统。④我国的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中具有浓厚的“宗族文化传统”,“传宗接代”,“人丁兴旺”等观念深入人心,其宗族的生育压力较为明显。⑤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生育政策,政策控制力度较强,家庭的生育决策空间较小,绝大部分家庭的生育子女数量为0-2个。⑥经济处速发展中,经济变革、社会变革、文化变革都深刻而明显,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因素较之西方国家更为复杂和多变,因此,需要更为多样且细致的分析。
总而言之,对于西方理论的应用应当重视假设前提,借鉴分析框架,绝不能生搬硬套,更何况,西方生育决策理论中的很多结果尚需实证检验,很多理论还存在空白和有待发展之处。与西方经典生育决策理论相对应,我国学者的研究更注重本国的实际和国情,更加关注特殊的文化体制因素对于生育决策行为的影响。但是,我国学者的分析也具有一些局限性,例如,对于理论的重视不够,多倾向于利用西方现有理论进行实证分析,而缺少对于模型的构建与理论的创新。另外,对于西方生育决策模型的运用缺少前提,片面的运用从而导致错误的结论。而且研究多局限于微观范畴,缺乏对宏观变量影响的研究。
三、制度变迁与生育决策的相关性研究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定义,制度有两层基本含义:一是制度是一种行为规则,它决定了社会主体在社会生活中可以选择的行动方式。二是制度是人们结成的各种经济、社会、政治等组织或体制,它决定着一切社会经济活动和社会经济关系的展开。按照制度的层次,制度可以分为: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制度的实施机制。制度包含着激励和约束的双重功能,制度的变迁推动着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变,不同的制度安排决定着不同的经济绩效,也对人产生不同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促使人的行为的改变,同时也改变着人的决策方式和权衡关系。
不同的制度安排导致不同的经济环境,不同的经济环境导致家庭生育孩子的成本和效用发生变化,家庭中的个体面对着成本和效用的变化会做出不同的生育决策,体现着制度变迁对于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下面将简要介绍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对于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
曾毅和舒尔茨(1998)主要研究农村对于生育率的影响。他们运用罗吉斯特多变量回归方法和生命表分析方法进行相关数理统计分析,他们认为在集体所有制的“大锅饭”体制下,实际上会对农村生育多孩的夫妇给予了一种经济补偿,而的推行则打破了“大锅饭”体制,客观上取消了对生育多孩夫妇的补偿,从而导致了生育率的降低。通过数值分析,他们得出结论:在改革前期,削弱了生育控制,而在后期使家庭倾向于少生孩子,同时加强了生育控制。王水雄(2002)则通过将博弈论内容引入生育决策模型中,建立了生育的博弈模型,从而证明了在没有制度控制下,当公共领域中存在大量资源,且实行平均分配制度,人们此时倾向于多生孩子,从而导致了“公地的悲剧”,这表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均分配制度将会导致家庭倾向于多育孩子,而市场经济体制且产权明晰的条件下,家庭倾向于少育孩子。
与此类似,郑龙真,史清华(2006)通过调查样本数据,运用博弈分析方法,比较了无制度控制下的农民生育决策行为和有制度控制下的农民生育决策行为。得出在无制度控制下家庭将会选择多育孩子以争夺公共资源,在存在制度控制的条件下,人们将会减少孩子的生育数量。张华宁、陈纪平(2009)的研究利用产权经济分析的方法,通过在人口增长率的统计分析中加入政府产权制度效率参数和计划生育政策强度参数,通过将实证分析和逻辑推演相结合,得出两个基本结论:一是由于产权制度的变迁,不同的产权制度导致不同的绩效,由于产权界定具有规模经济性质,随着产权制度体系效率的提高,导致家庭生育行为的变化,进而导致过剩人口数量逐步减少,人口增长率下降。二是由于产权界定不完全,导致人们拥有多个孩子以获取更多的公共资源,从而导致“非生产性”过剩人口的增加,进而导致人口生育率的上升。
对于计划生育制度变革是否会引起家庭生育决策的变化,即是否会引起生育率的反弹,学界基本上呈现两种态度。顾宝昌(2010)提出改变计划生育政策,即放开二胎不会引起家庭生育行为的改变,也不会导致人口失控。而朱中仕和陈华(2012)的研究表明调整现行人口制度的时机还不成熟,在短时期内将会引起家庭生育行为的改变,导致人口生育率的反弹。
通过不同学者对正式制度变迁与生育决策的相关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正式制度包括产权制度、农业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计划生育制度等社会经济中的一系列制度都会对家庭生育决策产生影响,进而对人口增长率和生育率的变化产生影响。
四、生育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根据有关部门的估计,我国因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而少生的人口达到3.38亿。同时也大大加速了我国人口转变的进程,人口转变是指从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的状态转变到两者都很低的状态的过程。根据国际经验,人口转变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一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阶段;二是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阶段;三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阶段。[21]在我国,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和对生育的有力控制,经过30年时间,我国便进入了第三阶段,即通常发达国家处于的阶段。与我国相同收入水平和发展程度的国家均处于第二阶段,因此,我国人口的迅速转变无疑是实行严格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
与我国人口转变过程迅速推进相伴随的是人口老龄化加剧和“人口红利”效应,按照联合国的划分标准,在全部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10%,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7%,即被称为老龄化社会。据此推论,由于2000年65岁老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6%,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根据预测,到2050年我国老龄化水平将超过20%,成为名符其实的“银发国家”,这对于我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将会产生复杂的影响。
在人口老龄化的同时,我国的经济增长也长期受到“人口红利”的积极影响。“人口红利”是由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于1998年正式提出的。根据标准的定义,“人口红利”是指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较低,这种总人口结构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特征使社会负担较轻,劳动力供给充足,储蓄率和投资率处于高位,且绝对量不断增长,另外,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也不断增长,从而有利于经济的高速发展。
很多经济学家都对“人口红利”的增长效应进行了研究和检验。其中,蔡P(2004)通过运用经济增长因素分解法得出,东亚奇迹中大约有四分之一应归结于人口结构因素。同时,他认为大约23.71%应归功于人口红利的作用。汪小勤(2007)认为高的劳动参与率会促进储蓄率和投资率的提高,进而加速经济发展。王德文,蔡P(1999)的研究表明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对储蓄率的回归系数为0.109,-0.113,且均显著。一般而言,年轻化的人口年龄结构可以推高储蓄率,主要因为工作人口的比重增加导致收入增加,从而导致储蓄增加,而且,年轻人的储蓄意愿和能力也较高。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家庭生育行为的变化,进一步引发了人口转变,产生了“人口红利”效应,根据预测,在2000-2030年间,劳动负担系数在50%以下,在2030-2050年期间,劳动负担系数将逐步上升,到2050年将上升至64.36%,届时,我国将由“人口红利”转变为“人口负债”。
由此可知,21世纪的前30年,将是我国利用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机遇期。因此,对于人口红利的研究就显得格外重要。在当前学者对于人口红利的研究中,既出现了许多成果,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主要包括:一是对于人口红利和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研究,多侧重于将人口因素、人均收入、人均GDP等指标相联系。而人口红利对于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分配结构以及就业结构的影响的分析较薄弱。二是对于人口红利对于经济增长的传导作用与传导途径的分析较模糊。三是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出现人口老龄化与人口红利并存的阶段,这一特殊的人口现象对于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如何,也值得深入研究。
[参 考 文 献]
[1]加里・斯坦利・贝克尔.家庭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62-214
[2]李小平.期望孩子的交易价格及其在生育控制中的应用[J].中国人口科学,1992(5):49-56
[3]彭希哲,戴星翼.试析风险最小化原则在生育决策中的作用[J].人口研究,1993(6):2-7
[4]周双超.生育需求的经济分析[J].人口与计划生育,1996(2):41-44
[5]卢现祥,朱巧玲.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420-432
[6]曾毅,舒尔茨.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对生育率的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1998(1):129-143
[7]王水雄.生育的博弈模型:中国的例子[J].社会学研究,2002(6):82-94
[8]李建民.生育理性和生育决策与我国低生育水平稳定机制的转变[J].人口研究,2004,28(6):2-18
[9]郑龙真,史清华.农村家庭生育行为的博弈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6(3):29-33
[10]王跃生.制度变革、社会转型与中国家庭变动――以农村经验为基础的分析[J].开放时代,2009(3):97-115
[11]张华宁,陈纪平.理性人口过剩:人口的产权经济分析[J].经济管理,2009(7):166-171
[12]顾宝昌.中国人口:从现在走向未来[J].国际经济评论,2010(6):95-111
[13]朱中仕,陈华.由赴港生子到生育公地悲剧的认识[J].人口研究,2012,36(4):103-112
[14]蔡P.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机制改革的理论思考[J].中国人口科学,2001(6):1-8
[15]黄步云.家庭生育选择行为的经济学分析[J].西北人口,2005(1):61-64
[16]郑真真,李玉柱,廖少宏.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成本收益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9(2):93-102
[17]王金营,顾瑶.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条件、问题即对策[J].人口研究,2011(1):74-81
[18]蔡P,都阳,高文书等.劳动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现实[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0-40
[19]蔡P.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J].人口研究,2004,28(2):2-9
篇3
〔关键词〕 婴儿潮;中国;日本;人口世代;社会负担;宏观经济
〔中图分类号〕C92-05;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5-0065-08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04年左右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后,中国乡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速度逐年降低,未来依靠城镇化提高经济发展速度的动力将逐年变弱。〔1〕而上世纪60年代末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的生育水平自1990年代以后便呈现急剧下降的趋势,最终于2014年左右引致人口红利转折点,成年劳动力数量开始减少。根据中国目前55岁的平均退休年龄〔2〕,60后婴儿潮世代将于2015年左右逐步开始退休①,未来5-10年中国的老龄化浪潮将异常迅急,同时,随着1990年代生育水平的持续下降,未来新增劳动力也将不断下降。我国正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不能及时调整人口发展措施,很有可能出现未富先老,甚至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面对这样的情景,迫切需要了解中国人口增长的性态,特别是人口世代对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的影响。只有了解这些趋势性特征事实,才能根据历史上和国际上的经验,制定适宜的措施。
遗憾的是,目前研究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学者较少关注中国的人口性态,特别是中国的人口世代因素,比如60后和80后的婴儿潮问题;研究人口红利和老龄化问题的学者很少关注中国历史上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依次进入和退出劳动力市场对诸如人口红利和老龄化等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的影响;也少有学者关注婴儿潮世代处在劳动阶段这一人口世代对人口红利期的特殊影响问题;未来中国将要面对的是进入和正在进入的低速常态,却少有经济学家从人口世代这个视角观察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比如90后婴儿低谷世代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60后婴儿潮世代开始退出劳动力市场可能引发的问题;此外,关注经济低迷和近期经济下滑的学者多,却少有人研究日本个案,从日本获取经验和教训。而日本过去20年和将来所面临的问题正是中国正在面临或将要面临的问题,比如政府债务危机、老龄化、劳动力短缺、持续发行货币对经济刺激以及经济潜在通缩的影响等。随着日本婴儿潮世代这一超规模人口世代冲向顶峰和由规模较小的世代取而代之,不仅日本庞大的财政和货币刺激对经济复苏所起的作用有限,也大大加重了日本政府的债务。
日本和中国具有相同的东方文化,同时都对外来移民管制较为严格,故比较中国人口性态和日本人口性态之间的相同和差别,进而从日本历史上获得经验和教训,是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所在。
二、文献综述
有关人口性态,特别是人口世代的研究,多集中于人口结构或者婴儿潮对社会和宏观经济的影响方面,如Mankiw & Weil(1989)在Poterba(1984)的基础上考虑人口结构改变对住房需求的影响,其研究结果发现,美国婴儿潮一代(1946-1964)步入购房年龄,是美国70年代住房价格上涨的关键因素;而婴儿低谷一代进入住房市场则引致1990年代美国房屋需求增长缓慢。〔3〕陈斌开等利用人口普查的微观数据发现,中国“80后婴儿潮”一代步入劳动力市场和进入婚配对住房产生的需求,很有可能是2004年以后房价上涨的重要原因,同时也阐释了老龄化到来会引致住房价格面临下降的压力。〔4〕陆D和蔡P比较了中日人口结构,认为中国如今所面临的人口结构和90年代日本所面临的人口结构类似,人口红利开始消失,社会负担开始加重,潜在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5〕李银珩和李硕论述了美国1946-1964年婴儿潮一代步入退休,将使美国面临劳动力短缺以及社会保障体系负担加重等问题。〔6〕在有关人口结构,特别是人口世代演进对其他方面的影响研究方面,张春生和蒋海论述了美国婴儿潮一代对美国1980-1990年股市的影响。〔7〕Andrew(2001, 2003)以及Brooks(2002)就资本市场和社会保障方面做了相关研究工作〔8〕;Reinhardt(2000)就婴儿潮世代进入老年阶段时对医疗行业的影响进行了针对性研究。〔9〕总之,婴儿潮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和全方位的。
不过我们要强调,Mankiw & Weil(1989)等人的研究忽视了中国的特殊性〔10〕,虽然美国和中、日都存在婴儿潮,但是人口结构问题对美国经济的制约没有中国和日本严重,这是因为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且实行较宽松的移民政策,历史上美国本土居民生育水平下降引致的现在和未来劳动力短缺问题可以通过年轻移民填补,更不同于中日的是,美国自1975年后每年出生人数的整体趋势是增加的。陈斌开等则缺乏对中国人口结构的明细分析,没有窥探到中国历史上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也没有论述婴儿潮和婴儿低谷可能对中国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的影响,特别是随着婴儿潮一代以及相继而来的婴儿低谷一代的成长,即教育、工作、结婚、消费、退休以及去世等一系列生命活动会对相应经济部门产生的影响。陆D和蔡P虽然比较了中日人口结构,阐述了人口红利理论,却没有明确地提出人口世代以及世代更替的概念,忽视了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交替进入劳动力市场和退出劳动力市场对经济增速的趋势性特征的影响,没有看到人口结构问题的实质其实是婴儿潮问题。人口红利期是婴儿潮一代处在劳动年龄阶段,婴儿低谷世代处在青少年和老年阶段;而人口红利消失期则是婴儿潮一代逐步退休,婴儿低谷世代处在青少年和劳动年龄阶段。
现有文献中虽存在考察中日人口结构问题的一些研究,如张宝珍(1990),孟双见和吴海涛(2005)分别论述了日本老龄化下日本社会和经济可能面临的问题〔11〕;柳清瑞等(2012)阐述了少子化和老龄化下的日本社会保障经验〔12〕;蔡P(2004,2009,2010)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的人口红利期以及人口红利结束可能面临的问题以及政策应该如何调整,如何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如何成功迈过中等收入陷阱〔13〕;梁颖和陈佳鹏(2013)论述了中国和日本存在人口转变和经济转型的相似性,以及如何根据这种相似性借鉴日本在人口红利期和人口老龄化时期所获得的经验和教训问题〔14〕,但是,目前学术界对于中日人口世代的界定,比如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的具体界定,以及考察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和退出劳动力市场对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可能产生的影响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甚至连基础的描述性分析工作都比较缺乏。这一切主要源于人口世代对经济的影响是长期的,20年前出生的人口要过20年后才进入劳动力市场。因此,本文的研究特点体现在以下方面:详尽论述中国和日本的婴儿潮世代并进行对比性分析,考察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交替进入劳动力市场和退出劳动力市场可能对中日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产生的动态影响,以及这种趋势性特征的变化对中国未来宏观经济的启示。
三、中日人口世代对比
此部分主要考察中国和日本分别在1961-2010年、1946-2010年出生人口的特征,进而界定在此期间中国和日本的人口世代。明细化这个事实特征,对分析人口世代的交替演进,比如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交替进入和退出劳动力市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具有重要价值。同时也有助于决策部门制定合适的人口和经济政策。需要说明的是,什么是婴儿潮?婴儿潮就是人口出生高峰,出生高峰包括出生人数逐年上升的阶段,也包括出生人数逐年下降的阶段;同样出生低谷包括出生人数逐年下降的阶段,也包括出生人数逐年上升的阶段,且出生高峰和出生低谷在时间上连接,其节点为历年出生人数的增速开始发生转折的时点〔15〕,所以婴儿潮时期既不是出生人数完全上升的时期,也不是出生人数完全下降的时期,而是一个波峰。
在上述时区内,中国和日本都存在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中国的婴儿潮世代分别为“1962-1973世代”和“1982-1993世代”;日本的婴儿潮世代分别为“1947-1953世代”和“1966-1985世代”。中国的婴儿低谷世代为“1973-1982世代”和“1993年之后世代”;日本的婴儿低谷世代为“1953-1966世代”和“1985年之后世代”。在此期间,中国两次出生人口的波峰值分别为1963年的3000万人和1987年的2550万人;日本两次出生人口波峰值分别为1949年的2694万人和1973年的2107万人。在峰值时间点上中国比日本晚了14年;中国的出生人口谷值是1979年的1738万人,日本是1961年的1607万人,在时间点上比日本晚了16年。无论是峰值还是谷值,中国都高于日本;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第二次婴儿潮世代都是第一次婴儿潮世代引致,且第二次婴儿潮的波峰低于第一次婴儿潮的波峰。中国第一次婴儿潮世代大约为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期;第二次婴儿潮世代大约为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期。二战后日本的第一次婴儿潮世代为1940年代后期和1950年代初期;第二次婴儿潮世代为1960年代末期和整个70年代以及80年代初期。中国第一次婴儿低谷大约出现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期,第二次出现在1993年之后,大部分是90后和00后;日本的第一次婴儿低谷大约出现在1950年代中后期和1960年代初期和中期,第二次出现在1985年之后。总之,中国的婴儿潮世代约为60后世代和80后世代,婴儿低谷世代大约为70后世代、90后世代以及00后世代;日本的婴儿潮世代大约出现在1940年代中后期和1950年代初期以及整个1970年代,而婴儿低谷世代大约出现在1950年代中后期和1960年代前期,以及1980年代后期和以后各年代。
在相应的考察时段内,中国和日本历年出生的人口数量都呈现出“先上升(中国1961-1963,日本1946-1949)后下降(中国1963-1979,日本1949-1957),再上升(中国1979-1987,日本1957-1973)再下降(中国1987之后,日本1973年之后)的M型轨迹”。1961-1963年中国出生的人口数量呈上升趋势,其中1963-1979年出生人口数量平均呈现剧烈下降趋势;1979-1987年出生人口数量平均呈现剧烈上升趋势;1987年后出生人口数量呈现下降趋势,且表现出明显的阶段特征,1987-2000年剧烈下降,2000年以后缓慢下降。而日本1946-1949年出生的人口数量呈现剧烈上升趋势;1949-1957年出生的人数呈现剧烈下降趋势;1957-1973年日本出生的人数呈现剧烈上升趋势;1973年之后出生人数呈现下降趋势且具有阶段特征,1973-1990年出生人数剧烈下降,1990年以后出生人数轻微下降。
综上,我们认为,中国的1962-1973世代和1982-1993世代为婴儿潮世代,1973-1982世代和1993之后世代是婴儿低谷世代,大体上60后和80后是婴儿潮世代,70后、90后以及00后是婴儿低谷世代;而日本的1947-1953世代和1966-1985世代是婴儿潮世代,1953-1966世代和1985之后世代是婴儿低谷世代。1961-1963年中国出生人数呈现上升趋势,1963-1979年中国出生人数平均呈现下降趋势,1979-1987年中国出生人数平均呈现上升趋势,1987年之后中国出生人数呈现下降趋势,整体上呈现为一个M型轨迹,同时,整个1970年代的出生人数平均而言逐年下降,整个1990年代的出生人数平均而言也逐年下降。大体上,日本出生人数呈现先上升(1946-1949)后下降(1949-1957),再上升(1957-1973)再下降(1973-)的M型趋势。具体走势见图1和图2。
四、中日人口世代更替对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的影响
在相应时段内,中国和日本的人口世代更替究竟是如何影响了对应的宏观经济呢?特别是当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交替进入或退出劳动力市场时,会对宏观经济产生何种影响呢?在假设资本、技术以及资本贡献份额保持不变的条件下,本文考察人口结构转变对中日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的影响,并重点考察劳动力增速对GDP增速的影响。通过将20年前出生率近似为20年后的劳动力增速,可从20年前的出生率和20年后GDP增速的关系上获得一些唯像认识,进而从这些认识中捕捉中国当前和未来可能面临的问题并获取解决问题的启示。
1.中国人口世代更替对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的影响
首先考察1961-1979年出生率变化特征对1981-1999年中国GDP增速的趋势性特征的影响。由于1961-1963年中国人口出生率逐年上升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历年出生人数和出生率的趋势基本上同步,当然下文日本的情景也是一样的。,20年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数量增速也逐年上升,相应1981-1983年中国经济增速也逐年上升;1963-1979年中国出生率逐年下降,相应20年后的1983-1999年中国经济增速也逐年下降。根据20年前出生率的特征,1981-1999年经济增速应呈现先增后减的倒U型轨迹,波峰点在1983年,波谷点是1981年和1999年。从图3可以看出,1981-1999年中国经济增速存在倒U型轨迹,波谷点是1981年和1999年,但是波峰点不是1983年,而是1994年。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认为,中国60后婴儿潮中出生的大部分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平均时间点应该晚于20岁,从图3可以近似地推断,60后婴儿潮世代的大部分人口大约在31岁左右才进入劳动力市场,比如1963年出生的人口大多在1994年左右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其主要原因是那时期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35%左右,存在大量富余农村劳动力和城镇待业劳动力,而真正放开人口流动和深化农村改革是90年代的事情,此时这些富余的和待就业的劳动力才逐步从失业或者非充分就业状态转移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从而变为相对充分就业。
其次考察1979-1990年出生率特征对1999年以后中国GDP增速的趋势性特征的影响。1979-1987年中国人口出生率逐年上升,引致20年后的1999-2007年经济增速相应地逐年上升;而1987年以后中国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2007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速也相应逐年下降,根据1979年以后中国人口出生率特征,中国经济增速在1999年以后也相应呈现倒U型轨迹,波峰点是2007年。1981-1985年出生人口数存在波动,倒U型轨迹也存在同趋势的波动。由于80后婴儿潮波峰低于60后婴儿潮波峰,引致80后婴儿潮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对经济增速的影响小于60后婴儿潮进入劳动力市场对经济增速的影响,1981-1999年平均经济增速相应大于1999-2010年平均经济增速,且2007年经济增速的峰值小于1994年经济增速的峰值。从图3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增速在1999年以后存在倒U型轨迹,波峰点是2007年,1981-1985年存在波动,倒U型轨迹也存在波动;而在高度上这个倒U型轨迹小于1970-1999年的倒U型轨迹。对此应该认为,上述中国经济增速的轨迹基本符合20年前中国人口出生率的趋势型特征,说明中国1961-1990年人口出生率的趋势性特征的确影响着1981-2010年经济增速的趋势性特征。
综上,1961-1990年出生率的变化特征对20年以后即中国1981-2010年GDP增速的趋势性特征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近似地表述为:由于中国的出生人数呈现先上升(1961-1963),后下降(1963-1979),再上升(1979-1987),再下降(1987-1990)两个峰值的M型轨迹,致使20年后中国经济增速也呈现先上升(1981-1994),后下降(1994-1999),再上升(1999-2007),再下降(2007-2010)两个峰值的M型轨迹,但是后一个波峰小于前一个波峰。各时段人口分布演进,及历年经济增速和相应20年前出生率之间的关系如图3、图4所示。①
2.日本人口世代更替对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的影响
首先考察日本1946-1957年人口出生率变化特征对其1966-1977年GDP增速的影响。日本1946-1949年的人口出生率呈现上升趋势,20年后的1966-1969年经济增速也呈现上升特征;1949-1957年人口出生率呈现一直下降特征,20年后的1969-1977年经济增速也相应呈现下降趋势,即1966-1974年日本经济增速呈现先增后减的倒U型轨迹,波峰点是1969年,波谷点是1966年和1977年。从图5可以看出,1965-1977年日本经济增速的确存在倒U型轨迹,波峰点是1969年,这与20年前日本的人口波峰点为1949年吻合。但是日本实际经济增速波谷点是1974年左右,比通过人口波谷点预测的经济波谷点早来3年,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日本城镇化水平和市场化水平较高,劳动力受农业以及限制人口流动的政策束缚较小,引致日本人口参与劳动的时间相对较早。
其次考察1957-1978年日本人口出生率变化特征对1977-1998年GDP增速的趋势性特征的影响。1957-1973年日本人口出生率逐年上升,引致20年后的1977-1993年经济增速相应逐年上升;1973年以后日本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引致1993年之后经济增速也相应逐年下降。根据1957年之后日本人口出生率的变化特征,我们发现1977年以后的日本经济增速相应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轨迹,波峰点是1993年。又因为1946-1957年的人口波峰大于1957-1978年的人口波峰,故日本在1969-1977年的平均经济增速大于1977-1998年的平均经济增速,同时波峰点1993年的经济增速低于波峰点1969年的经济增速。从图5可以看出,日本经济增速在1974-1998年的确存在一个倒U型轨迹,且整体上低于1966-1977年的轨迹,但1974-1998年日本经济增速的波峰点为1988年,比人口预测的波峰点1993年早来5年,再次表明日本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平均时间比中国要早。
综上,日本1946-1978年出生率的变化特征对20年之后即1966-1998年GDP增速的趋势性特征的影响可以近似地表述为:日本出生人数整体上呈现先上升(1946-1949),后下降(1949-1957),再上升(1957-1973),再下降(1973-1978)的两次波峰的M型轨迹,使得20年之后日本经济增速整体上同样呈现先上升(1966-1969),后下降(1969-1974),再上升(1974-1988),再下降(1988-1998)的两次波峰的M型轨迹。由于日本1967-1985婴儿潮世代因1947-1953婴儿潮世代引致,故第二次婴儿潮引致的日本经济波峰小于第一次婴儿潮引致的经济波峰;相对中国,日本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平均时间更早。具体而言,各时段的人口分布演进以及经济增速和20年前出生率之间的关系见图5和图6。
3.人口世代更替对未来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2015年之后,随着中国1960后婴儿潮世代开始逐步退休,2024年左右老年人口将开始超过青少年人口。由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加快和新型城镇化的推进,现行的养老双轨制会逐渐取消,养老将全面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这会给中国的养老保障体系带来巨大压力。过去发达国家实行的现收现付制的养老模式已不再适合中国国情,日本养老模式曾经引致的问题就是一个现实的教训。由于日本婴儿潮一代耗费了发展经济的大量资源,退休之后又享受着档次高且全面的养老金覆盖,导致婴儿低谷一代背上重重的养老包袱,为此,日本政府的债务水平不断上升,社会负担沉重,最终给经济雪上加霜。国内由于学术界目前对中国婴儿潮世代以及中国人口世代的研究较少,以至于当60后婴儿潮开始退休时才注意到社会保障体系的脆弱性。幸运的是平均退休年龄相对较低,还有改进空间,比如可以逐步将平均退休年龄推迟到65岁,通过延迟退休赢得时间,将现收现付制的养老模式逐步改为积累制的养老模式,从而规避在未来劳动力短缺情况下,劳动人口还要背上重重的养老负担,影响经济活力。
类似日本1990年代的房地产泡沫,2015年之后,80后婴儿潮将逐渐结束婚配,95后将逐渐开始进行婚配,由于1990年代以后出生人数逐年下降,城镇化已达到5477%左右,发展速度降缓,对城镇住房产生的基础居住需求将会呈现下降趋势,如果此时供给、改善性需求以及投资性需求不变,房价将面临下降的压力。为防止人口世代更替可能引致的房地产业的过分衰退,应考虑逐年降低新增基础住房供给,如果按照平均寿命75岁计算根据2014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2010年的女性预期寿命774岁,男性预期寿命724岁,为简化分析,不再区分性别,同时考虑到2010-2015年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在此假定2014年的平均寿命是75岁。,2035年之后,考虑到60后婴儿潮世代逐渐离去后将释放巨大的住房存量,目前针对房地产调控的政策应该前瞻到这一点,从而防止供给过剩对经济运行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基于此,在城市可以完善“以房养老”的政策构思,减轻社会养老负担,同时也可以提前平滑掉婴儿潮世代死亡后对房地产行业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2015年之后,80后婴儿潮一代逐步完成婚配以及置业和购车,工作稳定并开始步入中年,出现收入大于支出、收入剩余增加后将引致其对投资产品需求的增加,资本市场在2015年将出现繁荣,但是未来随着60后婴儿潮临近退休和35-54岁人口总量减少,2016年以后资本市场的繁荣也将逐步消退。〔16〕
大体上,由于中国1990年代出生人数逐年下降且1960年代存在一个出生高峰,因此2015年之后,随着1990年代出生人口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和1960年代出生人口逐步退休,人口世代更替引致的老年人口急剧增加,成年劳动力数量减少,即消费人口增加、生产人口减少可能会导致一系列新的经济社会问题。比如老年人口的储蓄逐年减少,劳动人口的储蓄因为老年人口增多也逐年减少,最终社会储蓄率下降,资本存量增长缓慢此命题在劳动人口和老年人口消费不变,要素使用效率不变,资本贡献份额不变以及采取现收现付制的养老制度下成立。,加上劳动力数量逐年减少,经济增速面临下行压力,经济有可能进入新的低速增长常态。
面对人口基数红利不断消失可能带来的问题,提高人口素质、升级产业以及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将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比如,将劳动力短缺的中低端制造业转移到人口红利丰富的国家,提高国内技术水平,解决中低端服务业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提高资本和劳动要素的使用效率;加快创新红利的开发,重视和培养国内高技术人才,吸纳港台、东南亚甚至全球的科技人才,从而提升劳动力素质。为了给长期内的产业升级、提高人口素质以及技术进步赢得时间,在短期内可以采取削减养老金,改变养老制度以及结构性延迟退休等方案。〔17〕考虑到未来城镇房地产行业的衰退和农村土地流转的开展,为减轻社会和劳动人口负担,农村可以实行“以地养老”,城镇可以开展“以房养老”。
五、规避人口世代更迭引致宏观经济趋势性下滑的政策建议
第一,为缓解当前社会保障带来的财政压力和年轻人压力过大等问题,应该实行结构性延迟退休,尤其是劳动力短缺行业应实行延迟退休并给予相应的补贴,同时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开发机器人等新技术,替代这些行业短缺的劳动力。在提高人口素质的同时,吸纳一些优秀的国际移民,升级国内产业;对部分劳动力发展过剩的行业实行不延迟退休,打破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避免老人挤占年轻人的工作机会,造成年轻人社会负担大和社会生产率水平下降的问题。第二,改变养老制度,将现收现付制的养老制度改为基金制的养老模式或者多元的养老模式,且将养老金分为国家基本养老金和附加养老金。基本养老金所有公民一视同仁,附加养老金以工薪阶层为对象且按收入比例缴纳,同时鼓励富人缴纳商业养老金,提高养老金领取的年龄;避免过度医疗开支,在医疗机构引入竞争机制;减少政府公共债务,强制性增加家庭储蓄养老份额,引导私人资金进入养老领域,为提高养老金收益,优化养老资金种类,并在全球化视角下积极对养老金进行投资,吸纳劳动力过剩和储蓄水平较高国家的人口和资本红利,在全球范围内解决资本短缺和劳动力短缺。第三,提高退休后有工作意愿和工作能力的老年人的就业率,并对老年人进行再培训;提高妇女以及年轻人的就业率;创造公平的就业环境,避免年龄和性别歧视,改变年功序列制的工薪和升迁制度,根据绩效设定工资和职称。第四,长期来看,国家应尽快放开生育政策,释放想生但政策限制不能生的这股生育力量。随着经济水平逐步提升,应进一步制定鼓励生育的政策,而不仅仅是放开生育,即制定生育水平的下限,而非上限;同时基于代际生育权平等和城镇居民生育水平提高后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和家庭储蓄水平影响相对较弱,应特别鼓励城镇居民生育。
〔参考文献〕
〔1〕蔡P.刘易斯转折点与公共政策方向的转变:关于中国社会保护的若干特征性事实〔J〕.中国社会科学,2010(6):125-137.
〔2〕姚远,等.退休年龄调整:为何如此纠结〔J〕.人口研究,2012(6):28-43.
〔3〕〔10〕Mankiw N G.,Weil D N. Baby Boom, Baby Bust and the Housing Market〔J〕.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1989 (19): 235-258;Poterba J M. Tax Subsidies to Owner-Occupied Housing: An Asset-Market Approach〔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4 (4): 729-752.
〔4〕陈斌开,等.人口结构转变与中国住房需求:1999-2025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微观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12(1):129-140.
〔5〕陆D,蔡P.人口结构变化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中国和日本的比较〔J〕.世界经济,2014(1):3-29.
〔6〕李银珩,李硕.婴儿潮与人口高龄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J〕.人口学刊,2006(2):41-45.
〔7〕张春生,蒋海.人口结构与股票市场:文献综述〔J〕.国际金融研究,2014(6):86-96.
〔8〕Andrew B A. Will Bequests Attenuate the Predicted Meltdown in Stock Prices when Baby Boomer Retire〔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1 (4): 589-595;Andrew B A. The Effects of A Baby Boom on Stock Prices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the Presence of Social Security〔J〕.Econometrica, 2003 (2): 551-578;Brooks R. Asset-market Effects of the Baby Boom and Social-security Reform〔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s, 2002 (2): 402-406.
〔9〕Reinhardt, U E. Health Care for the Aging Baby Boom: Lessons from Abroad〔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0 (2):71-83.
〔11〕张宝珍.日本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的发展〔J〕.世界经济,1990(5):45-49;孟双见,吴海涛.日本人口老龄化对日本社会经济的影响〔J〕.日本问题研究,2005(4):26-29.
〔12〕柳清瑞,等.基于少子高龄化的日本社会保障改革:经验与借鉴〔J〕.人口与发展,2012(6):31-39.
〔13〕蔡P.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J〕.人口研究,2004(2):2-9;蔡P.未来的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开拓〔J〕.中国人口科学,2009(1)2-10,111;蔡P.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J〕.经济研究,2010(4):4-13.
〔14〕梁颖,陈佳鹏.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基于中日人口红利比较的视角〔J〕.人口学刊,2013(4):21-31.
〔15〕杨华磊,等.中国婴儿潮下的城镇住房需求〔J〕.中国经济问题,2015(2):49-60.
篇4
摘 要:随着我国人口红利时期的过去,老龄化的迅速来临,人口结构的改变将会对企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企业用人成本大大提高。另一方面,随着企业退休人员增多,养老和财政负担不断增加。与此同时由于老年人口增加,夕阳产业显现出了广阔的发展前景。本文将具体研究我国未来人口结构的改变对企业可能带来的各种影响,提出一系列有效的应对措施,保障企业安全度过人口负债时期,实现高效稳定发展。
关键词:人口负债;中小企业;企业年金;退休过度
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主要经济发达国家逐渐迈入老龄化阶段,关于人口结构转变与经济发展之间的问题开始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由于实行了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享受着一系列的人口红利,包括充足的劳动力供给,经济活跃,投资增长。但近几年的各种数据显示我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老龄化正在以每年3.2%的速度发展。在享受过长期的人口红利之后,我们不得不面对人口负债。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显示,未来几十年内我国人口结构将继续发生巨大变化,未来几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大幅增加,并在本世纪中叶达到巅峰,约占总人口的30%多。
老龄化对企业组织来说也是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尤其是缺乏资金和一定的社会吸引力的中小企业。
首先,人口的老龄化使得社会劳动力供应不足,企业招聘遇到难题。
其次,人口老龄化使得中国劳动力成本加大,增加企业的用人成本。
第三,老龄化时代的来临,使得企业需要支付退休员工的养老金数额急剧增大。企业的养老金压力大增。
最后,人口老龄化的好的一方面是老龄化时代的“银发经济”。根据《经济学家》杂志的调查,在发达国家有3/4 的财富掌握在50岁以上的老年人手中,中国也是一样,很多富豪的年龄都是50 岁以上。同中青年相比,老年人拥有财富、时间,使“银发一族”有条件创造这种新的“银发经济”。所以企业要制定一系列的战略来适应人口机构的变化。
从创业领域来看,老龄人口的增加为老龄产品生产、服务企业创造了无限商机。创业既可以考虑短期的养老服务和护理行业的需求,也可以考虑中长期老年文化娱乐(教育、休闲)、老年健康保健、老年金融保险(理财、保险)行业的发展前景。
对于一般企业有以下几点可以选择
一、实行弹性退休制度,适当将退休年龄推迟至 65岁。
我国现行的职工退休制度为法定的企业职工退休年龄是男年满60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企业应以现有法定退休年龄为基础,以工作年限为退休的依据,配合弹性退休办法,调整我国劳动者的法定退休年龄。尤其争取男女同龄退休,最大程度发挥女性工作者的价值。
二、在企业组织结构中建立企业顾问制度
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看,人们的需求大致可以分为生理、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实现。由于国民健康水平普遍提高,我国退休干部在退休时身体素质较之从前有大幅的提高,还有参与经济发展的愿望,并且这些退休人员蕴藏着大量的人力资源。而且老年人优势突出,包括老年人工作经验丰富,在工作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人脉资源,对此实行相应的老年员工返聘,安排过渡性职位。通过组织结构和岗位设计为即将退休员工设立咨询以及培训监督岗位,会有巨大的前景。为弹性退休制度搭建平台,也能实现对现职人员的监督。
三、完善企业年金的激励补偿机制
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向来都采取现收现付制度为主,实行养老的代际转嫁。随着人口老龄化压力的加剧,单纯依靠基本养老保险难以提供充足、体面的退休保障。企业年金计划作为基本养老保险的补充,可以降低国家基本养老保险的退休金替代率,减轻政府基本养老保险支付压力,提高政府对基本养老保险的承受能力。能够将员工利益与企业经营效益及长远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鼓励员工长期服从企业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大量员工退休带来的的财政压力的转移和养老金的补偿,有效的建立了一种对员工的终生激励机制。
四、安排老员工进行养老计划培训,退休前适应性培训,理财规划培训,旅游等活动。
一方面对于企业来说可以适当丰富文化活动,有利于增强企业凝聚力,创造积极健康的企业文化。对于员工来说,掌握了科学的理财知识,能够更加合理的安排退休生活。自己得到了企业的肯定,一定会尽最大努力为企业服务,实现了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和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的有效统一。
五、对于金融类企业,要大力发展经融投资创新,利用老年人拥有的大量财富。
例如发展住房反向贷款,综合养老计划财产信托等业务。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业务的推出,将是银行贷款体系的一种创新。如果这种新的规模巨大的贷款业务发展起来的话对银行将是非常有利的,同时,由于新的保险品种的开辟,保险公司也能获得不菲的保费收入,房屋评估机构等其他中介机构也能从中受益,在巨大的利益面前银行、保险公司不能不为之心动。
综上所述,通过国家和企业共同联手,政策与措施齐头并进,通过合理有效的改变组织结构,为退休员工设立过渡岗位。制定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发展激励性质的企业年金制度,相信企业能够将人口结构改变带来的负面效应降低到最小化。(作者单位:山东大学)
参考文献
[1] 徐盛发,巴曙松《从资产负债表角度考察人口结构的宏观含义》经济评论2011年第六期
篇5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形势看,虽然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没有变,我国处于有利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没有变,但是与10年前相比,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某些有利条件,特别是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已经明显弱化,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人口红利”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正在发生趋势性转变,其他资源性产品的国际价格也明显升高。我国经济发展成本的上升制约了投资效益的提高,进而使经济高速增长态势面临结构性减速的新挑战。
与周边一些国家相比,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传统比较优势正在逐步消退。从最低工资看,2011年北京、上海、深圳、河南最低工资标准分别为1160元、l280元、1320元和l080元,比2005年分别提高100%、85.5%、91.3%和l25%。根据英国经济学人智库(EIU)的数据,l0多年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增长近4倍,单位小时劳动成本由2000年的0.6美元增加至2011年的2.9美元。从土地价格看,2011年末,全国主要监测城市地价总水平为3049元/平方米,是2005年末的2.4倍,其中,商业服务、住宅、工业地价分别比2005年上涨174%、267%和32.5%。
2011年北京和上海两地的最低工资都比5年前增长了1倍左右,单位小时劳动成本比2010年有很大上升,已经远远高于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国。
在这种背景下,当前世界制造业流向出现了两种新动向:一种动向是,在美国高调鼓吹“再工业化”、“重振制造业”等政策目标的口号下,一些制造业向美国本土回流;另一种动向是,世界制造业的某些行业向一些劳动力成本更低廉的经济体转移。特别是后一种动向已经有不少的案例,原本投向中国的外资开始向东盟国家转移。如耐克运动鞋,2000年,中国生产了全世界40%的耐克鞋,全球第一,越南当时的份额只占13%;2009年,双方各占世界的36%;2010年,越南取代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耐克鞋生产国。另外,中国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一些制造业也有向东盟转移的苗头。广东是电子、IT产业 的“世界工厂”,电脑配件生产占世界60%,电子配套能力占世界90%;但近年来电子企业也有向东盟转移的现象,而没有转向中国的中西部内地地区。
国际资本也更多流向东南亚地区。2012年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调查报告显示,在跨国公司评选的最受欢迎的东道国排名中,印尼和泰国排名大幅上升。在中国工资成本和生产成本持续上升的态势下,东盟各国制造业的竞争力继续增强。2000年以来,越南制造业产值以11%的速度增长。根据《世界投资报告2012年》,2011年流入东南亚的外国直接投资为117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6%,而同期中国的增长率只有8%。
二、我国制造业不可能大规模地转移到国外
美国确实希望世界制造业的某些部分转移回国内,其“再工业化”、“重振制造业”的政策目标也是真实的愿望,但美国的劳动力结构并不支持这个政策目标。从美国国内的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看,适应高低两端产业结构的就业岗位增长较快,而需要一定技能的中间层次的产业环节就业岗位却减少。其原因是,低收入家庭受教育的激励不断下降,进而使低端劳动者的教育水平不适应产业结构变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可贸易部门的岗位大量外流,使得这个群体被新的国际分工排斥在外。
制造业回流美国的现象确实也存在,但这主要发生在高端产业中的高端技术环节。由于美国拥有世界上最高水平的大学教育,在科技创新领域继续占有领先地位,因此吸纳高端产业环节在美国具有独特的人力资本优势。但是,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化,即对人力资本要求高的产业和对人力资本要求低的产业扩张快,而处在中间的产业却处于萎缩状态,许多青少年不读大学,甚至高中入学率也大大降低,整体人力资本水平下降。例如,美国2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00年的13.22年降低到2010年的12.45年,其与世界173个国家同一指标中位数的比率也相应降低。如今,在美国已经找不到既接受中端技术环节中一线岗位的报酬,又胜任普通熟练程度技能的工人,美国大规模接受制造业多数生产环节回流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
虽然从总体上看中国制造业不会大规模回转到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不过,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变化说明,随着中国愈来愈需要向产业高端发展,中国制造业在攀升价值链的过程中,将越来越遭遇与发达国家的直接竞争。因此,中国要保持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实际上就意味着能否在更高的产业价值链上获得竞争力。这种新的国际竞争力不仅取决于劳动力数量或工资成本,更取决于劳动力质量或人力资本。
中国制造业会不会大规模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于2004年出现“用工荒”和工资上涨之后,预计在2013年到达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的人口红利转折点,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趋于消失。与此同时,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结构转变要慢于中国,可以预期要经历劳动年龄人口继续增长的一段时间。从逻辑上分析,如果这些国家潜在的人口红利可以转化为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按照日本学者小岛清提出的雁阵模型,就具备承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条件。
然而,事实的逻辑必然是,中国制造业大规模向其他发展中经济体转移也是不可能的。中国的绝对优势是,劳动力的庞大规模和占绝对优势的比重。整体上说,中国劳动力呈增长趋势。第六次人口普查中满15周岁不到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是9.2亿,比2000年的8.25亿或者8.2亿增加了将近1亿人。另据人口专家预测,中国未来10年每年适龄劳动力资源都能稳定在9亿左右。根据联合国最新预测,中国人口的总规模在2030年前将一直增长,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在2018-2020年达到峰值,约为10亿。
与被认为具有经济增长潜力并且与人口红利相关的“新钻11国”,即韩国、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巴基斯坦、菲律宾、孟加拉国、尼日利亚、伊朗、越南、土耳其、埃及(加上印度是12国)相比,中国劳动力数量要大得多。2010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中,中国占到了38%的绝对多数比重,如果不包含印度这个世界第二人口大国,中国在全部劳动年龄人口中的比重更高达55%,即使到202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仍然高于其他许多国家。这就决定了这些国家替代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可能性并不大。即使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一个较小比例转移到某个或某些国家,都会引起相关国家劳动力需求的大幅度提高,以致劳动力供给不足,进而因工资上涨而降低其竞争力。近年在一些承接少量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家,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的趋势就十分明显。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正在成为经济竞争的新优势。1982年我国劳动者人均受教育年限为4.6年,1990为5.5年,2000年为7.1年。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0年的《中国人力资源状况白皮书》,截止2009年,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5年。这一点,中国相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具有明显的优势。以印度为例。虽然该国人口规模和劳动年龄人口规模都十分庞大,但是,由于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低,2010年2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4.4年,很多人并不能胜任岗位的要求,因此,实际上印度的有效劳动力供给并不充足,由此可以解释印度工资上涨幅度连续10年居于亚洲各国之首。
虽然近年我国劳动工资成本呈快速上涨趋势,但劳动要素禀赋优势不完全取决于工资水平,还取决于劳动生产率以及与此有很大关联的人力资本。中国的人力资本积累明显优于印度和许多发展中经济体,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不会被轻易取代。
三、新的国际竞争优势越来越取决于劳动力素质的提升
理论和实践都证明,考察一国产业优势和竞争力的关键是看劳动者素质与价值链分工是否匹配。劳动力供给不仅要看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还要看劳动者的技能是否符合岗位的要求。就是说,劳动力数量与人力资本共同决定着制造业的竞争力。以中国与11个国家(不含印度)25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来比较,只有墨西哥和菲律宾的受教育年限高于中国,大约高13-14个月,而更多的国家大大低于中国,如孟加拉国比中国低33个月。如果我们计算25岁及以上人口总量和人均受教育年限的乘积,作为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总量的话,2010年中国在这12个国家中所占比重超过50%。
从未来趋势看, 新的国际竞争优势愈来愈取决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根据预测,2020年中国2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8.63年,届时中国人力资本总量仍将占全部12个国家总量的45%。这个预测有两个含义:其一,今后10年中国人力资本总量仍将保持巨大的优势。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一定份额会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作为这类产品制造者的地位不可能完全被替代或不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替代;其二,中国保持制造业大国地位的关键是人力资本积累和教育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人口结构转变是一个不可抑制的过程,第一次人口红利终究要消失,但是劳动力素质可以加快提高,第二次人口红利可以是无限量的。
近两三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协调性不断加强,中西部地区正在成为东部产业转移的承接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率减死亡率)为5.05‰,东部地区平均为4.68‰,中部地区平均为4.73‰,西部地区为6.78‰,剔除人口流动的因素,即主要按照户籍人口进行比较的话,中西部地区的人口抚养比也仍然低于东部地区。可见,所谓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判断主要是指中国东部的沿海地区,而中国中西部地区尚有潜力可以挖掘,特别是劳动力供给潜力。
目前沿海地区的农民工很大部分来自于中西部地区。例如,2010年全部1.53亿离开本乡镇6个月及以上的农民工中,中西部地区占68.2%,农民工中跨省流动的比例,中部地区为69.1%,西部地区为56.9%,其中大量的是流向东部地区。更广义地说,东部地区内部的劳动力流动,也表现为从不发达地区到发达地区的模式。
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在一个时期内将保持相对低于东部地区的水平。年龄偏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如果在家乡就可以找到非农就业机会,一定会乐于接受大大低于东部地区的工资水平,这是因为中西部地区较低的生活费用,以及劳动者无需克服跨地区流动的物质费用和心理成本,这等同于提高了实际工资率。
近年来,虽然出现了农民工工资在地区间的趋同现象,但是从趋势上看,未来沿海地区的工资上涨速度将快于中西部地区。例如,以工资争议为主要内容的劳动争议案件,70%以上都发生在沿海地区,这说明中西部地区劳动者对工资的满意程度,大大高于东部地区。说明传统的中国劳动要素禀赋的优势,还将在中国中西部延续一个时期。延续这种已有优势的努力,就是不失时机、因地制宜地把一部分产业或生产环节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转移到中西部地区。
四、加快培育我国国际竞争力新优势
虽然我们可以得出我国“世界工厂”地位不可能被取代的判断,但这是有条件的,上述只是指出了人口总量、结构特征和教育发展的外部条件,而这种外部条件需要在企业和市场的许多内在因素作用下,才能转化为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新优势。因此,培育和形成我国新的国际竞争力优势将成为未来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重大课题。
我国劳动人口的庞大数量决定了我国不可能不需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随着沿海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我国中西部地区将仍然保留较大比重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那么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是否将不存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呢?从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与国际经验的对比来看,工业化、特别是工业现代化在中国还要延续几十年,先进制造业在中国的发展正方兴未艾,中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也并没有结束工业化,只不过是在转型升级中向高端产业方向发展。从企业结构来看,大企业是少数,中小企业始终都将占据绝大多数比重。只少数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企业,科技型的小企业也不可能成为企业的主体结构。因此,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存在是必然的。那么它们的优势在哪里呢?它们的优势在于形成新型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
竞争力不仅取决于工资水平,还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和单位产品成本。工资水平提高并不绝对意味着竞争力下降,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单位成本下降,有可能抵消工资水平上涨的不利影响。而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也不仅仅只有资本替代这一途径,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也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
因此,要创造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政策环境,政府要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在教育和培训的供给方面,政府应该增加公共投入,降低家庭和个人的教育(培训)支出比重。同时,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政府可以矫正失灵的市场信号,提高人力资本回报率,引导家庭和个人对人力资本投资。还要创造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政策环境。正如单位劳动力成本的计算方式(即劳动力成本与劳动生产率的比率)所显示的那样,在由工资表示的劳动力成本不可避免提高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提高越快,单位劳动力成本提高越慢,劳动力优势得以保持。然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仅仅依靠提高资本劳动比,即用资本替代劳动,根本的办法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与人力资本相关联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另一重大课题是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产品的研发能力,并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在技术创新的基础上培育产品的品牌,加快培育自主品牌,提高出口产品的品牌竞争力。除了上述这两大课题之外,培育和形成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新优势还有以下6个不可忽视的途径和措施:
其一,采取精致化生产,提升产品质量和档次。许多中小企业没有能力采取资本替代措施,也不具备技术创新的各种条件,但它们依旧可以在现有技术和工艺条件下,通过精细化管理,节约成本,通过提高产品质量,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使产品比过去更有竞争力。
其二,培育新的商业模式。通过专业分工,少数有竞争力的企业将不具有优势的生产环节外包,集中资源发展优势的生产和经营环节,并以生产为龙头,跨地区、跨行业,把大量中小企业连接为完整的供应链,形成整体对外竞争的新优势。
其三,发展电子商务,利用电子信息化手段寻找新客户,形成网上交易市场,降低交易成本。
其四,打造新型的国际商务平台。在原有国内市场基础上,引进国际商务的技术手段、运营模式和广告宣传,形成更多的义乌国际商品交易模式。
篇6
摘 要:本文针对我国将要实施的延迟退休政策对就业的影响问题,通过建立延迟退休对就业影响的指标评价模型,来预测实施延迟退休政策对我国就业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政策实施年份相同的情况下,延迟退休年限越长,对就业的影响越大;如果延迟退休年限相同,政策越晚实施,其对就业影响越大。
关键词:延迟退休;就业;计量模型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逐渐发展,医疗卫生水平逐渐提高,居民寿命逐步增加,而计划生育实施三十多年来,新生人口增速逐年下降,伴随而生的人口老龄化现象则日益明显,这将会给社会带来一系列负面经济影响,如长期劳动力供给不足和社会保障压力加大。
因此,关于是否应该延迟退休年龄的争论逐步增多,国内学者对这个问题做了大量相关的研究,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延迟退休年龄的必要性,如盛帅、张义凡(2013)从人口结构老龄化和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趋紧两个角度论证了延迟退休年龄的必要性[1];金刚(2010)则从降低养老保险支付压力,应对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从而增强经济竞争力的角度,说明了延迟退休年龄的必要性[2];同时蔡P(2010)也赞成通过延迟退休年龄方案来解决未来劳动力不足和人口红利消失的困境;邓大松、罗昌平(2001)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社会养老保险对退休年龄的灵敏度,退休年龄每提高1%,基金缺口减少0.374%。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延迟退休政策对就业状况带来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延迟退休会导致劳动供给量增加,然而延迟退休却不一定会导致就业压力增大,经济发展是促进就业增长的最直接动力,经济的增长会明显带动就业率的提升,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劳动力需求也会逐渐增加,因此,我们比较不同年份因延迟退休引起的就业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建立延迟退休对就业的影响指标评价模型,对由于延迟退休所带来的对就业状况的影响进行研究。
二、研究思路
本文的思路是主要理清延迟退休与劳动力供给的关系和经济增长与劳动力需求的关系。虽然延迟退休会导致劳动供给量增加,但是延迟退休却不一定会导致就业压力增大。这是因为促进就业增长的最直接动力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可以扩大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降低就业压力。
三、研究方法
一方面,用GDP增长率表示经济增长的程度,进一步以就业人数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比表示就业弹性系数,从中可以看出,在就业弹性系数一定的情况下,GDP的增长率与从业人数的增长率呈同向变化,用λ表示就业弹性系数,有:
GDP增长率=GDP/基期GDP,θ =λ×ΔGDPGDP
(1)
因为各产业部门的劳动力需求不同,社会各产业和部门的就业弹性系数各不相同。同时需要对不同产业的GDP增长率进行区分。以λj为j行业部门的就业弹性系数,ΔGDPj为j产业的GDP增长量,GDPj为j产业的基期GDP。将就业增长率进一步表示为:
θ=∑nj=1λjΔGDPjGDPj
(2)
另一方面,从已有劳动力和对未来劳动力增长趋势的预期角度表示从业人数增长率,同样考虑不同产业部门劳动增长率和劳动需求存在差异,在此基础上,评估因延迟退休年龄而产生的那部分从业劳动力增量对就业的影响程度,将关系进一步限定于延迟退休年龄条件下的从业劳动力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联系从业人数增长率的两种不同表达式,得到就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其中ΔL′为因延迟退休年龄而产生的从业劳动力增量:
ΔL′L′=∑nj=1λjΔGDPjGDPj
(3)
为具体确定ΔL′的量,我们假设,现存的i岁劳动者总量为Li,其相应的劳动力参与率为λi,λiLi即为i岁劳动者的总从业人数。以此类推,便可得到各个不同年龄的从业劳动力总量为∑λiLi。假设劳动者a岁开始工作,b岁结束工作,则就业人数总量为∑bi=aλiLi,记t为延迟退休年龄,并引入延迟退休年龄对就业影响的定量指标σ,此时可以建立延迟退休年龄对就业影响的计量模型:
σ=∑b+ti=aλiLi-∑bi=aλiLi∑bi=aλiLi/∑nj=1λjΔGDPjGDPj
(4)
σ为大于0的值,σ越大,表示延迟退休年龄对就业的影响程度越大。按照本文提出的计量模型,在既定条件下,只要将相关数值代入模型加以试算,便可找到能使等式两边达到均衡的t值,即延迟的退休年龄的年限,此时b+t值即是处于均衡点上所对应的最佳退休年龄。当该式达到均衡时,b+t就是最佳延迟退休年龄,此时σ=1。
四、结果分析
首先,我们对我国1990-2010各年度的劳动力、就业率、GDP预期等指标数据进行线性拟合处理,通过回归预测相关指标数据从2015年到2040年间每年的值。
可知退休年龄分别延长3、5、7年对于不同年份的影响指数σ如图1:
图1 延迟退休对就业影响定量指标
由图可知,不同的延迟退休实施方式,对就业影响不同。一方面,如延迟退休政策实施的年份相同,那么延迟的年限越长,对就业的影响就会越大;另一方面,如延迟退休的年限相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延迟退休政策实施的年份越靠后,延迟退休年限对就业的影响就会越大。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含义
我国当前的法定退休年龄为男60岁,女55岁(干部)或50岁(工人),而在欧美国家普遍的退休年龄都为65岁。如今,我国正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从1990至2010年以来,我国劳动力供求状况保持稳定,GDP稳定增长,有必要在适当时期实施延迟退休政策。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假如延迟退休政策实施的年份相同,那么延迟退休的年限越长,对就业的影响就会越大;假如延迟退休的年限相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延迟退休政策实施的年份越靠后,由于经济的发展,延迟退休年限对就业的影响就会越大。所以,为了缓冲延迟退休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在政府决定推行延迟退休政策时,可以考虑逐步增加延迟退休年限,使就业压力处于一个可控的范围,特别是在现今经济处于下行压力的情况下。(作者单位: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基金项目:2014年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制造行业从业人员延迟退休年龄政策》(AH201410378305);2015年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大学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关于我国延迟退休年限问题的研究》(ACJJXYYB027)
参考文献:
篇7
【论文摘要】随着劳动力短缺现象的出现和人民群众对收入提高的期待,工资水平上涨是必须的和必然的。因此,我国确保产业结构调整成功并避免出现比较优势真空的关键,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这恰恰是教育水平提高的结果。
教育优先发展的依据在于其对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制定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的目的,就是从国情和教育规律出发,通过以公共产品定义教育、以教育深化扩大规模、以资源整合调整结构、以竞争开放提高质量,以及以需求导向增进效益,实现教育发展的跨越式发展,最大化发挥教育先行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一、教育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靠劳动力数量和教育水平优势,取得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占据了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地位。随着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该地区的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已经开始。保持竞争力的关键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成反比关系的劳动力成本,二是成正比关系的劳动生产率。随着劳动力短缺现象的出现和人民群众对收入提高的期待,工资水平上涨是必须的和必然的。因此,我国确保产业结构调整成功并避免出现比较优势真空的关键,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这恰恰是教育水平提高的结果。
我们的研究表明,在制造业,职工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劳动生产率就会上升17%。如果企业职工全部由初中以下学历的职工构成,改善为全部是高中学历的话,企业劳动生产率可以提高24%,如果再进一步改善为全部是大专学历的话,企业劳动生产率可以再提高66%。此外,教育深化对劳动者个人的收益也是巨大的,这意味着可以调动家庭投资于教育的积极性。研究表明,如果城乡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水平提高至12年,即完成高中教育,城镇劳动力教育收益可提高17.0%,农村劳动力提高21.1%。如果受教育年限进一步提高至14年,带来的教育收益增加幅度对城镇劳动力为41.2%,对农村劳动力为43.3%。
根据预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前后达到高峰,之后将下降,意味着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将消失。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程度和社会养老负担显著提高。保障劳动力供给要求未来考虑提高实际退休年龄。而这种可能性几乎完全取决于教育的发展。也就是说,发展教育也是为迎接老龄化做必要的准备,或者说是创造条件赢得第二次人口红利。
二、教育先行要大幅度提高公共投入比重
目前,我国财政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为3.3%,只相当于法国的59%,德国的79%,英国的66%和美国的69%。我国提高公共教育投入的目标是根据这个差距设定的。但是,基于以下原因,我们认为有必要设定更高的目标。
首先,学龄人口比重大要求更高的公共教育投入。上面的比较尚不足以显示我国公共教育投入的实际差距,因为教育投入规模与一个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相关。当学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比较高的时候,也需要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教育。根据这个原理进行模拟,即以美国学龄人口比重为基准,由于中国目前总人口中仍然有更大比例人口处在受教育阶段,模拟的结果显示,我国在教育上的公共投入仅为GDP的2.8%,与发达国家的水平差距进一步扩大,只是法国的46%,德国的52%,英国的52%和美国的59%。
其次,公共投入不足挤压居民正常消费。公共财政支出占全社会教育支出的比例,在发达国家为86%,发展中国家在75%左右,全世界平均为80%左右,而中国仅为46%。也就是说,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私人支出占教育支出比例异常地高。教育投入过度依赖家庭,严重挤压了私人消费空间,导致社会消费其他方面的需求不足,抑制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削弱了出口和投资需求的情况下,扩大教育的公共投入,具有重要的宏观经济意义。教育公共投资不足的另一个后果,是教育不公平问题越来越突出,教育费支出已经成为很多家庭的沉重负担,社会上对教育的抱怨大多源于此。
第三,公共教育投入的临界最小规模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从理论上讲,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应该遵循一个先高后低的倒U字型变化轨迹。首先,我们观察到的发展中国家这个比重偏低,这固然是人均收入水平低、资源不足的结果,但更是导致不发达的重要原因。发展中国家处于受教育阶段人口比重大,人力资本存量水平低,只有实现教育的跨越性发展,才能更快地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而这要求有一个公共教育投入的临界最小规模。其次,由于公共教育经费主要用于义务教育,发达国家已经超越了普及义务教育的阶段,而更高的教育阶段相应要求较多的私人投入。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人口老化,处于受教育阶段的人口比例也降低,从而在教育总支出保持较高的同时,公共支出比重趋于下降。我们之所以在实际中没有观察到这个规律的作用,恰恰是因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未能实现教育超前发展,从而不能大幅度提升人力资本,实现经济发展的赶超。
三、教育资源需要进行更有效的配置
一项流传较广的研究表明,分教育阶段来看,学前教育的社会收益最高,学校教育其次,而职业教育最低。其含义并不是教育收益下降,而是指社会收益与个人收益的消长。从总体上来讲,我们把教育定义为公共产品。但是,由于教育供给的类型是多样的,其外部效应不尽相同。在合理分配公共教育资源和调动家庭教育投入时,我们可以按照这个规律,第一,在不排除竞争的前提下,坚持义务教育的完全公共品属性。同时创造条件把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阶段,把学前教育纳入公共支持的对象。由于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健康具有很明显的外部效应,特别是具有扶贫含义,因此,农村学生的营养餐和城市学生的体育设施属于公共品领域,政府应该进行干预。第二,由于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更加接近于准公共品领域,即这个教育阶段既具有公平补课的性质,也具有个人和企业收益率高的特点,在公共支持的同时,尽可能动员社会、企业和家庭的投入积极性。
篇8
我国2008年开始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10年人均GDP突破4000美元,由中等偏下收入组进入中等偏上收入组。作为世界第二大但人均“较穷”的经济体---中国,发展到今天,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着一些相似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较大、增长方式急需转变、社会制度改革、腐败等。那么中国是如日本、韩国等成功跨入高等收入国家行列?还是如拉美和东南亚国家一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认为关键在政府!
可能导致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
一、 中国经济继续传统方式增长,可能会“揠苗助长”
从1978年到现在,我国一直保持GDP年均增速9.8%。由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制度改革促进了经济发展。然而,一面是“价格指导”等政府“有形的手”,,另一面是中小企业融资难,民营企业投资受限等,这些表明中国经济制度已需进一步改革。
中国当前经济增长受到诸多限制,人口红利,将因人口减少和工资提高而逐渐消失。资源供给约束、环境质量约束、生态容量约束等,使投资拉动经济模式难以为继。如果依据坚持经济高速增长,可能会“揠苗助长”,使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以巴西为例,20-30年代其经济以10%的速度增长,但自1975年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截至2011年已经在中等收入区域滞留36年。
二、 不患寡而患不均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317,自2000年开始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这里面有城乡收入差距,有行业收入差距,而且这些差距在加快扩大。资料显示,拉美一些国家在1970年前后的收入分配已呈现非常集中的状态,基尼系数最低者为0.44,最高者为0.66。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末,收入分配最不公的是巴西,基尼系数达到0.64,乌拉圭和哥斯达黎加低于0.48,但仍高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最令人不安的是,收入差距扩大化,很可能会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从而导致社会动荡,阻碍经济进一步发展。
三、 产业“固步自封”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第一、第二产业比重偏高,第三产业比重明显偏低,且内部结构不合理、效益低。第二产业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就业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发展至今,我国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急需升级优化,资源、能源、环境的约束,使我们不得不考虑产业升级。产能过剩、增强效率等都使第二产业开始走“经济”路线,大大降低了它对就业的容纳量。日益增多的就业人口,以及人们对高收入的追求,也使我国必须进行产业升级。拉美国家就是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时,依然延续着依靠高投资和高物质消耗促进经济增长,这种粗放式的发展终究不可持续,带来的经济成效也越来越少的。
除了以上三个方面,还有很多诱因可能导致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它们的影响也很重大。比如既得利益集团与希望改革发展集团之间的利益斗争;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惯性的GDP崇拜;监管体系不完善;宏观经济政策非理性等
启示
一、制度建设
制度虽然不能直接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它在投资决策、生产组织、利益分配、制定战略决策等方面都起着重大作用。也就是说制度进步对于经济持续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
首要是法律制度的建设,人治社会往往存在各种诟病。其次,建立政府服务型制度的建设,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效率。另外,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制度。
二、产业升级
产业升级需要把握好方向,发展第三产业有节能环保、附加值高等好处,但在积极引导第三产业发展的同时,还是重视第二产业的优化升级,因为目前推动经济发展、容纳就业主要是第二产业,并且第二产业的优化升级,可以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或者两者相辅相成。产业的发展升级除了国企,民营企业应作为重点关注对象。民营企业创新意识更强。当经济后发优势越来越不明显,我们就需要不断的创新,以获得先发优势。
三、 重视公平
相对公平是我们应该努力前进的目标。当人们不仅关注蛋糕的大小,而更加关注蛋糕分配问题时,说明分配已经出现了问题。户籍改革、推进城市化进程、消除公权腐败等都是我们必须要做的课题。
篇9
投资被高估,消费被低估
从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在过去十年大部分时间里,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均超过最终消费,也即中国经济增长一直靠投资拉动。但笔者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GDP增速之间进行一致性分析,发现自2004年起投资增速与GDP增速之间发生了明显的背离现象,如在2005-2007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的过程中,GDP增速却出现了上升。既然大家普遍认为中国经济是靠投资拉动的,那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GDP的背离现象就足以引起人们对投资规模数据可靠性的怀疑了。
1.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被高估。若从增量资本产出比(ICOR,反映投资效率指标)看,1994年大约为1.955,到了2009年已经达到6.09,甚至在2011年达到了7.05的水平。也就是说,增加1元钱的GDP,原本只要1.955元的投资,现在则需7.05元投资。这当然可以解释为边际投资效率的降低,但是否也可以解释为投资的“水分”越来越大呢?虽然说土地购置成本的上升等价格因素也是造成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虚增的原因,但即便用扣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增速来考察,也同样会发现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有虚增嫌疑。
从投资过程的实物投入看,绝大部分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都需要用到钢材和水泥,即钢材和水泥在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中占一定比例,假如这个比例恒定的话,那么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加10%,钢材和水泥的用量也应该增加10%。然而,从统计数据看,2004-2011年螺纹钢消费量平均增长率为15.96%,但同期固定资产实际投资平均增速为22.78%(扣除价格因素),每年平均竟相差6个多百分点,说明螺纹钢消费量并没有随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而同步增长,其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比越来越小。
如2010年螺纹钢消费量同比只增长13.12%,但同期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速为20.89%,超过螺纹钢消费量增速7个百分点。而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水泥,因为水泥的保质期较短,不宜储存或对外出口。据统计局数据,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中每亿元所含的水泥产量为1.7万吨,而到了2011年,每亿元所含的水泥产量仅为0.67万吨,即便考虑过去10年水泥的价格上涨因素(按普通硅酸盐水泥价格涨幅计),也要比10年前减少了一半左右。
再从新增吨钢产能所花费的固定资产投资金额(剔除价格因素)来看,2004至2010年整体呈上行趋势。2004年至2006年,新增吨钢产能的投资花费为3300元/吨,而2007年至2010年上升至7000元/吨,由于2004年至2010年新建产能所购设备未有显著变化,这种台阶式跳升显然不能用设备换代或涨价来解释,反而是投资金额多报的可能性较大。
以上两个证据说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统计存在高估可能。之所以出现高估的情况,无非有三个主要路径:项目转包、统计报表虚报和偷工减料。项目转包是目前非常常见的现象,每转一次,就可以提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如果转包5次,或许实际发生的工程费要比计划少掉一大半。此外,有些项目中存在虚报价格、从事关联交易的财务欺诈行为的可能性;还有些申报项目为能获批而支出的公关费用、招标过程中发包方得到的回扣等支出,往往也计入工程款项而被统计入固定资产投资中。至于在偷工减料方面,把钢筋拉长拉细以降低成本等,更是屡有所闻。
2011年7月审计署了2010年审计署绩效报告,在报告中提到“截至2010年6月底,全国审计机关共对京沪高速铁路等已投入资金1.9万亿元的5.4万个投资项目实施了审计或审计调查。通过审计,核减工程价款和挽回损失、节省工程投资283亿元,占相关项目投资总额的3.5%”。由此,我们认为固定资产投资至少被高估了3.5%,当然,被审计出来的部分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2.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被低估。投资被高估,不仅在统计上需要重新评估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而且也需要对居民收入进行重估。因为国家统计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是抽样调查数据,存在误差。由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以人口数测算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必然也存在误差。笔者认为长期以来居民可支配收入是被低估的,因为从长期看,收入应该等于支出,假定一年内居民新增支出也大致等于新增收入,那么,就可以估算出该年份的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若减去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抽样调查数据,则就是低估的部分。
这里所指的支出,其含义是经济学上的消费加储蓄,即广义支出,包括年内新增的消费、新增居民储蓄、居民在股票、债券和基金及银行理财产品、保险费用的净支出,还有购房投资及房贷还本付息等方面的净投入,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等。根据这一方法,2008年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被低估约4.7万亿。
如今,笔者又发现了一个更便捷的估算方法。《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有2006-2008这三年的“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显示2006至2008年住户部门可支配总收入分别为12.9万亿、15.66万亿和18.24万亿。这是统计局以联合国1993年版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为模式确定的核算方法所得出的数据,其基本原理类似于会计中的“有借必有贷”的平衡计算法。这里所谓的“住户部门”,也包括一般居民之外的个体工商业者,这与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中的“居民”涵盖范围是一致的。
如果把2006-2008年国家统计局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抽样调查数据,分别乘以城乡常住人口,则可以推算出2006-2008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分别为9.48万亿、11.32万亿和13.20万亿。与上述资金流量表的数据相比,分别相差了3.42万亿、4.34万亿和5.04万亿。也就是说,国家统计局修正后的2008年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要比原先公布的抽样调查结果高5.04万亿,也高于笔者之前的估算。
虽然国家统计局要到2013年才会公布2011年的“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但根据已经公布的2011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抽样调查结果),可以推算出2011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约为19.65万亿。由于2008-2011三年居民可支配收入(抽样调查结果)累计涨幅为51%,可推算出2011年的实际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可能达到27.54万亿,即低估了7.89万亿(图4),相当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从41.8%提升至58.6%,该比重或许可以化解长期被大家诟病的“居民收入占GDP比重过低”的困惑。
3.消费被低估。居民可支配收入被低估,可以从逻辑上推断全社会消费能力被低估。统计年鉴中与消费有关的科目主要包括: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GDP支出法下居民消费支出。GDP支出法下的居民消费支出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更能反映中国居民综合生活消费水平,但有很多被低估的成分。我们采用化整为零的方法,尽量还原真实的居民消费支出。
根据我们的详细测算,居民实物消费被低估4%-10%(高端消费品被低估较多),服务性消费被低估18%-21%(主要存在于文化娱乐、居住和医疗等领域)。这样还能算出总的被低估的居民消费支出。修正后的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与统计局公布的居民消费占GDP比重进行对比,得出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大约被低估2%左右。从修正后消费和投资与GDP占比情况看,2004-2011年消费占比都明显高于投资占比。
我们假设固定资产投资被高估了10%,主要基于审计署绩效报告中固定资产投资被高估3.5%以及没有被审计出来的部分。我们将修正后的消费、投资、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进行重新计算,并与统计局公布的修正前相应的数据进行对比,得到的结果令人信服。经过修正,我们发现消费对GDP的贡献被低估了,投资对GDP的贡献则相对被高估了, 2005、2006、2007、2008、2011年消费对GDP的贡献都超过了投资,09和10年出现投资贡献超过消费主要是因为4万亿计划的作用。
未来中国经济由消费主导
在上一节,我们综合各种消费被低估的因素和投资被高估的因素,则可以确信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前几年就已经超过投资。未来情况将会如何呢?我们认为,考虑到劳动力价值重估、社会保障完善和金融改革等因素,中国经济将由消费主导。
1.劳动力价值重估。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从9.4亿下降到9.37亿,几十年来首次出现下降,意味着我们已经处于人口红利的消退期。另一方面,中国现有的第一产业劳动力人数远低于官方统计数据,今后可向城市转移的剩余劳动力人口大约只有4000万-6000万(详见李迅雷《中国还有多少农村劳动力可向城市转移》)。
过去中国劳动力供应充分,劳动力价值低估,导致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持续下降,而今随着刘易斯拐点远去,人口红利逐步衰退,劳动力价值面临重估,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开始上升。
劳动报酬占比上升的一大证据是民众收入增速快于GDP增速。在劳动力短缺的时代,居民收入增速低于经济增速,而在2010年以后,随着劳动力人口的下降,农村和城镇居民收入增速相继超过GDP增速。过去十年全国各地居民最低工资标准逐年增加,农民工平均月收入在过去5年也出现快速上升,在2012年年均工资已达到3万元。
2.社会保障逐步加强。中国消费的一个重要制约是人民生活缺乏保障,其中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是重要短板。过去几年,城镇养老保险以及农村合作医疗确实在稳步推进。
2012年底,全国企业月均退休金达到1721元,比2006年的818元增加了一倍多,而且温总理在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企业退休金还将上涨10%,达到近1900元。农村合作医疗从2004年开始起步,到2011年参加人数达到8.32亿,当年支出1710亿,2012年前9月支出达到1717亿,每年增幅都在30%以上。
3.金融改革助推居民非工资性收入增长。“十”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一个重要的渠道是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从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速快,占城镇居民总收入比重不断提高,而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速缓慢,但是两者占居民总收入的比重只有2%左右。未来随着金融市场改革的大力推进,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有望出现快速的增长。
4.消费:从数量到质量。劳动力价值重估、社会保障完善和金融改革让我们相信,未来中国经济以消费主导的趋势是确定性的。除此之外,我们还观察到了消费自身正在发生一些质的变化。
中国过去的消费以数量增长为典型特征,过去10年的汽车销量从200万辆增长到2000万辆,年均增速近30%,未来数量增长空间有限,近两年乘用车增速已明显下滑。另一方面,2010年以后国人对SUV等高品质轿车青睐有加,其占比在3年内翻了3倍,同期上海车牌价也是频创新高,体现了消费升级的巨大需求。
篇10
摘要:随着外汇占款这个货币发行的源头的作用逐步降低和货币市场利率到商行信贷利率传导的失灵,央行不得不创立了一些新的政策工具,比如PSL,央行试图通过合格抵押品来进行基础货币投放,以达到引导中期政策利率的作用。PSL的推出,不仅是对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箱的丰富,同时也是对我国利率走廊建立的一个有益尝试;另一方面PSL也具有货币最终流向不可控、招标不透明、对利率锚的形成效果不突出和基础货币投放量小等不足的特征。
关键词:外汇占款 中期政策利率 PSL 利率传导
由于外汇占款的增加主要来自于经常项目顺差,而随着中国自加入WTO以来,制度红利、环境红利、人口红利逐步释放完毕,外汇占款有持续下降的趋势,无形中降低了以外汇占款为主渠道的的货币创造机制的作用。基于此,央行的货币发行机制有必要从被动向主动转变。
基于货币供给机制的变化和利率传导机制失灵两方面的考虑,央行有意建立一个新的货币框架,即打造短期利率走廊与中期利率指引的新框架。短期利率方面是SLF、SLO,中期利率方面是PSL(抵押补充贷款)。央行这一构想,最早可见于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清华五道口金融论坛的讲话,此次金融危机后经验,短期利率可能有时候不够有效,由此可以考虑增加一个中期利率。
金融危机前,全球主要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使得短期利率处于目标区间之内的利率走廊机制,短期利率能够保持比较稳定。金融危机发生后,为刺激本国经济,各央行在短期利率方面采取了零利率甚至负利率,货币政策调整空间非常有限,长期中长期利率却与之存在脱节,并有上行压力,从而对经济复苏形成掣肘。
从中国来看,2014年下半年以来货币市场利率在逐渐走低,但金融机构贷款加权利率却在走高,这显示出中国货币市场与信贷市场价格传递并非高效。央行推出PSL可以看作是对发达国家央行经验的一个借鉴。
据媒体报道,央行在2014年二季度向国开行投放了1万亿的PSL,资金用于棚户区改造等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贷款发放。国开行二季度工作会议显示,截至6月末该行资产总额9.9万亿元,比一季度猛增1.56万亿元。
一、PSL(抵押补充贷款)的由来与作用
对于PSL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1、首先,PSL从英国的FLS(融资换贷款计划)借鉴而来的,英国央行设定抵押品框架更多的是解决流动性危机的工具。例如,英国央行的旨在推动银行借贷的FSL面向几乎英国所有的银行和房屋贷款协会,只要有新增贷款作为抵押,就可以从FLS中获得想要的融资额度,即定规则而从未定机构,且如何操作,申请都公开透明。中国则不同,在信用总量的背景上,中国并未达到流动性危机的程度,中国货币政策更多的问题在于资金配置效率低。在资金的流向方面,英国央行和中国央行都难以监控资金的最终流向。从FLS的经验来看,其中大部分资金借道住房贷款协会流向了房地产。从PSL来看,资金从央行转到国开行,被指定用于棚户区改造,这确实做到了定向,但是棚户区改造的居民、企业可以将获得的资金用于消费、投资或存到普通商业银行,后续的效应就超出了国开行和棚户区改造的范围。
2、若要成为货币市场的中期政策利率,那必须是针对所有的参与者而言的,如果只是针对国开行一家对手,只能形成一对一的利率,这样的利率锚是有价无市的锚,意义不大。国开行在获得PSL的过程中并未经过公开的招投标程序,国开行PSL的利率当时尚未公开。既然要打造中期政策利率,就应该是透明的,不然如何引导市场利率?从招标程序的不公开和利率的对外不公布,很难达到目的。从期限上来看,PSL的期限是三年,但利率对应的是一年期利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是一年调整一次的,又怎能成为中长期的政策利率?更适宜的尝试是,可以率先确定一个额度,让各家银行以新增棚户区贷款作为抵押,招标决定利率。即像FLS那样,只定规则,不定机构,申请和操作都公开透明。
3、PSL作为一个货币工具,具有结构性的特征。从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来看,一般有四个,即充分就业、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但这四者都不是结构性货币政策实施的终极目的。此外,衡量和观测PSL效果的标准是什么,理论界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说法。货币工具解决的是总量问题,结构性的问题解决本不应该由货币政策来完成。实际上,央行早在《2014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也表达了对定向工具使用的担忧,如其中提到货币政策主要还是总量政策,其结构引导作用是辅的,定向降准等结构性措施若长期实施也会存在一些问题。
二、结构性的货币工具只能作为非常态的工具
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作为央行货币工具的创新,主动性并没有带来效果的提升,因此,结构性的货币工具只适宜是非常态的工具,而不适宜作为货币框架的长期内容。
在建立货币新框架之前,中国央行首先应该完善市场基准利率才是。基准利率都不完善,货币传导难免会出现失灵现象。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主要以银行间拆借为市场基准利率比如英国的Libor,欧元区的Euribor,日本的Tibor。就中国而言,上海银行间拆借利率(SHIBOR)虽运行多年,但一直存在报价质量不高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交易价包含了一些超出市场安排的因素,包括与对手方的其他利率安排、利益调整等,所以未能成为基准利率。
从一般国际经验看,只有结构合理、信誉高、流动性强的金融产品的利率,才能作为基准利率。在我国已经市场化的几种利率中,国债利率(具体地讲是国债二级市场的收益率)最适合充当基准利率。由于中国的国债规模过小,未能担当此任。
其次,若想从短端利率来引导中场端利率,得解决中期利率工具的公开性、透明性问题。在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之前,关于PSL的传言很多,报告有一定的滞后性,这会给市场预期带来混乱,不利于发挥中期政策利率的引导作用。
再次,在引导中长期利率方面,美联储、欧洲央行都有比较成熟的经验,比如前瞻性指引、窗口指导,中国央行也可以完全借鉴。中国央行通过加强沟通、表达明确态度,就可以消除一些不确定性,引导市场风险预期下行。
参考文献:
免责声明
公务员之家所有资料均来源于本站老师原创写作和网友上传,仅供会员学习和参考。本站非任何杂志的官方网站,直投稿件和出版请联系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