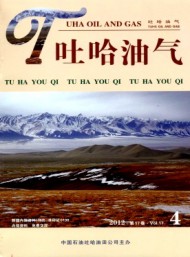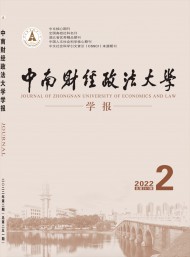简述汉书的文学成就范文
时间:2023-10-26 17:55:30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简述汉书的文学成就,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黄宗羲学术史研究的范式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学术思想史专著,对二百余个明代学者的学术面貌按照年代顺序与学派分属进行了评述与介绍,其材料之广富,内容之翔实,“可谓一代文章之渊薮”(《四库全书在目提要》)。梁启超曾指出:“大抵清代经学之祖推炎武,其史学之祖当推宗羲,所著《明儒学案》,中国之有‘学术史’自此始也”。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4页。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黄宗羲是“中国学术史”的创始人。除《明儒学案》外,黄宗羲还始撰《宋元学案》,未成而卒,由其子黄百家和全祖望两次补续而成。
从研究范式看,黄宗羲的《明儒学案》首创了“学案体”的学术史研究范式, 应该说,这一观点的提出者是原杭州大学的仓修良教授。参见:《国际黄宗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97-399页。即按照学派特征,分析、概括一定时期学术发展历史的写作形式。在中国传统学术史研究的发展进程中,虽然《礼记》中的《学记》、《儒行》、《檀弓》,《史记》中的《儒林传》、《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汉书》的《儒林传》,《宋史》的《道学传》,朱熹的《伊洛渊源录》,周汝登的《圣学宗传》、孙奇逢的《理学宗传》等等,已经具有了中国学术史研究范式的雏形,但是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在收集资料的全面性、分类的系统性、编撰的独特性等各个方面,均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即使比较晚出的唐鉴的《清学案小识》、尹会一的《北学编》,也不能与之相提并论。
具体而言,黄宗羲首创的学案体学术史研究范式的特征,主要体现于以下方面:
第一,资料丰富、全面。在中国学术史上,《明儒学案》以资料丰富、网罗详备而著称,其作为“一代文章之渊薮”的赞誉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于此。《明儒学案》成书于康熙十五年(1676),共分为六十二卷,记载了有明一代近三百年学术发展演变的概况。全书按照时代顺序,将二百多名学者分作十九个学案组织起来,每个学案之前,均有一小序,简述这个学派的源流和宗旨;随后是学者的小传,对各人的生平、学术源流、著作情况等作简明扼要的述评;小传之后,是学者本人的著作节录或语录,偶有作者的按语。全书上起明初方孝孺、曹端,下迄明亡刘宗周、孙奇逢,有明一学中人,大体网罗其中,实为一部明学史。由于阳明学为明代儒学中坚,故《明儒学案》述阳明学及其传衍最详。从卷十《姚江学案》起,至卷三十六《泰州学案》止,篇幅达二十六卷,入案学者计九十八人之多,亦足可谓是王学通史。
第二,分类系统、清晰。黄宗羲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着重梳理各家学术的观点,“为之分源别派,使其宗旨历然”(《明儒学案·自序》),这是《明儒学案》的重要创新。与同时代的周汝登《圣学宗传》、孙奇逢《理学宗传》相比较,黄宗羲《明儒学案》与这两部学术著作的优劣十分明显。周汝登的《圣学宗传》的基调是弘扬禅学,见闻狭陋,“扰金银铜铁为一器,是海门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也”;孙奇逢《理学宗传》的内容“杂收,不复甄别,其批注所及,未必得其要领”(《明儒学案·凡例》)。而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则“言行并载,支派各分,择精语详,钩玄提要,一代学术源流,了如指掌。”(《莫晋序》)
《明儒学案》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对各个学者加以研究,然后分门别类地阐述各家学术观点。黄宗羲在《自序》中表明自己研究学术史的观念:“羲为《明儒学案》,上下诸先生,深浅各得,醇疵互见,要皆功力所至,竭其心之万殊者,而后成家,未尝以懵懂精神冒人糟粕。”正是在深刻理解上下功夫,所以最终在系统性、条理性、明晰性方面,较之前的学术史著作更胜一筹,因而成为中国第一部最完整的学案体范式的学术史著作。
第三,体例独特、新颖。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在体例上以“有所授受者分为各案,其特起者,后之学者,不甚著者,总列诸儒之案。”(《明儒学案·凡例》)这样就形成一个个以学术创始人、继承者为一体的完整、系统的学案。各学案又都冠以叙论,作简括的介绍说明,随后分列本案各学者,并依次叙述他们的传略。在各个学者的叙传中,除了介绍生平,还扼要介绍其主要学术观点,并加以评析。随后再接以案主言论的节录和选辑,提供了解各家学术见解的具体资料。他选取的资料均取自原书,又经过精选,用黄宗羲自己的话说,就是“皆从全集纂要钩玄,未尝袭前人之旧本也。”(《明儒学案·凡例》)
黄宗羲《明儒学案》的体例结构,既汲取宋明以来《伊洛渊源录》、《诸儒学案》、《圣学宗传》、《理学宗传》诸书所长,又自创新制,匠心独运,使中国传统学术史中“学案体”的研究范式臻于完善和定型。乾隆初,全祖望承黄宗羲、百家父子未竟之志,续成《宋元学案》一百卷;道光间,唐鉴著《国朝学案小识》;民国初徐世昌等编撰《清儒学案》二百零八卷,全氏学案以下的诸多“学案体”著作,卷帙虽多寡不一,但就体例格局而言,皆没有逾越《明儒学案》的范围。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倘若没有黄宗羲《明儒学案》的这一里程碑式的创制,在中国传统学术史研究中,也就无从诞生“学案体”这一范式。
二、黄宗羲学术史研究的方法与学术使命
在哲学史的研究方法上,有两种哲学史或学术史的写作。一种是史学家的或偏重于历史的哲学史,如梯利的《西方哲学史》;另外一种则是哲学家的或偏重于哲学的哲学史,如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等。以上两种哲学史研究由于作者的出发点不同,又会产生不同的研究方式、研究方法。史学家的哲学史强调史料的真实、客观,而哲学家的哲学史则往往注重独立的见解和个性化的表达。但以上两种哲学史的写作,在黄宗羲身上得到可贵的统一,既是哲学家又是史学家的黄宗羲的学术史研究,具有在丰富、翔实的资料占有的基础上贯穿自己独立见解和深刻评价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首先,是客观、公允的分析、评价。黄宗羲在编撰《明儒学案》时明确提出学术评价中何为“真”的原则,这就是:“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明儒学案·凡例》)“自用得着者”也即“自得”,自得就是功力深到、独有见解,而不是人云亦云的产物。这就是说,学术评价当以“自用得着者”或“自得”为真,所谓“功力所至,竭其心力之万殊者”,哪怕“一偏之见”、“相反之论”,也要加以重视;相反,若“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则无需认真对待。
纵观《明儒学案》,黄宗羲基本贯彻了这一主张,因而也客观、公允地反映了各家的学术观点。正如莫晋在重刻《明儒学案》序中所论,黄宗羲做到了“是非互见,得失两存。”比如,在评价明初理学家吴与弼时,黄宗羲基本是以客观、公允的态度阐述其学说宗旨,没有因其遵循朱学路径加以非议:“康斋倡道小陂,一禀宋人成说。言心,则以知觉而与理为二,言工夫,则静时存养,动时省察。故必敬义夹持,明诚两进,而后为学问之全功。其相传一派,虽一斋、庄渠稍为转手,终不敢离此矩镬也。……椎轮为大辂之始,增冰为积水所成,微康斋,焉得有后时之盛哉!”(《明儒学案·崇仁学案一》) 黄宗羲首先指出吴与弼对朱学的忠实继承和遵循,在整体上突出了其关心践履功夫及笃实的修心养性方面的学术特征,同时,客观地指出了其对于明学的贡献。这是黄宗羲的可贵之处。
黄宗羲的客观、公允,还表现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学术态度。比如,黄宗羲在分析白沙学与阳明学的关系时,指出:“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又曰:“作圣之功,至先生而始明,至文成而始大。”(《明儒学案·白沙学案上》)从问题的一致性看,明代的心学思潮是由陈白沙开启,由王阳明大成的,似乎非常清楚。但是,有一个问题黄宗羲想不清楚,即:“两先生之学,最为相近,不知阳明后来从不说起,其何故也。”(《明儒学案·白沙学案上》)对于王阳明不提起陈白沙,学者们虽然有一定的解释,但总体上大家并不重视这一表面上看很偶然的现象,似乎认为这一问题并不值得深究,而黄宗羲显然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但由于自己没有想清楚,所以在《明儒学案》中黄宗羲只是提出了问题而没有冒然回答。这既显示出他的敏锐性与洞察力,但同时又显示出他的谨慎和小心,总体上这是一种客观、公允的学术态度。
体现在《明儒学案》中的客观、公允,还表现在对于学派划分上面。比如,从师承和学派关系上讲,陈白沙师从吴与弼,那么,陈白沙应归于《崇仁学案》,但黄宗羲在《明儒学案》的《崇仁学案》中,并没有包括陈白沙,而是另起《白沙学案》,说明吴与弼与陈白沙其实学源不同。黄宗羲如此评价曰:“白沙出其门,然自叙所得,不关聘君,当为别派。”(《明儒学案·崇仁学案一》)依此亦可见其客观、公允的态度。
其次,直指本质,关注理论实质。在关注“真”的同时,黄宗羲还贯穿自己的独立见解,其《明儒学案》属于哲学家的哲学史,因而具有自发的创造意识,而不是依傍某种“正确”、“权威”见解的历史,这一点至今具有借鉴意义。
黄宗羲撰写《明儒学案》,并不仅仅是为了阐述他人的学术观点,而更为关注的是对哲学的基本问题进行的探讨,如传统哲学中关于理、气、心的理论等。在《明儒学案》中,黄宗羲十分欣赏“尽横渠之蕴”的明代哲学家罗钦顺、王廷相等人的气论,认为:“先生(罗钦顺)之论理、气,最为精确,……千条万绪,纷纭胶葛,而率不克乱,莫知其所以然,是即所谓理也。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明儒学案·诸儒学案中一》)又曰:“先生(王廷相)主张横渠之论理气,以为气外无性,此定论也。”(《诸儒学案中四》)在这里,黄宗羲虽然主要是评价罗钦顺、王廷相的气论,但以评价为先导,借以诠释自己的观点,其实质是直指程朱理学“分理气为二”的倾向,而提出“理气为一”的观点:“理即是气之理,……理气是一。”(《明儒学案·诸儒学案中》)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到黄宗羲直指本质,关注理论实质的特点。
当然,黄宗羲所著《明儒学案》是以心学,尤其是以阳明心学为主线来代表明学的。《明儒学案》所收学者及他们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渊源,无论内容和分量,都以王阳明为中心,这显示出黄宗羲的自己的学术立场。比如,对于王阳明与湛若水的“格物”之辩,黄宗羲主要是站在阳明学的立场上,对此做了总结:“先生(甘泉)与阳明分生教事。阳明宗旨致良知,先生宗旨随处体认天理。学者遂以王、湛之学,各立门户。其间为之调人者,谓‘天理即良知也,体认即致也,何异?何同?’然先生论格物,条阳明之说四不可,阳明亦言随处体认天理为求之于外。是终不可强之使合也。……然天地万物之理,实不外于腔子里,故见心之广大。若以天地万物之理即吾心之理,求之天地万物以为广大,则先生仍是旧说所拘也。”(《明儒学案·甘泉学案一》)黄宗羲首先从王阳明、湛若水二人学说的分歧上,强调了“随处体认天理”与“致良知”的不同,因而二者“终不可强之使合”。但是,在理论根基上,黄宗羲主要是以阳明学“天地万物之理,实不外于腔子里”的观点,批评湛若水“仍是旧说所拘”。从学术立场而言,黄宗羲维护阳明学、批评湛若水,主要原因还是与其关注“心学”的理论实质相关,即从“心之广大”而言,并没有门派的偏见。这一点,体现在黄宗羲描述当时王门的学生与湛门的学生相互出入方面:“当时学于湛者,或卒业于王,学于王者,或卒业于湛,亦犹朱、陆之门下,递相出入也。”(《明儒学案·甘泉学案一》)其并没有显示出谈论门派高下的倾向。
应当指出,黄宗羲的学术史研究,除了具有哲学史与哲学研究相统一的研究方法之外,同时还表现出强烈的学术使命感。
一般而言,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术使命有两方面:一方面把以往的哲学成果作为建构自己哲学理论的出发点,即“接着讲”;另一方面则真实地呈现以往哲学演变的历史过程,即“如实讲”。作为哲学家和学术史家的黄宗羲无疑同时具备以上两个方面。从“接着讲”方面看,黄宗羲在强烈的学术使命感的感召下,苦心孤诣地探求学术发展史,其实是从时代的学术发展脉搏中,寻找人类社会进一步完善的一般规律;而从“如实讲”看,作为学术史家的黄宗羲,其学术史研究的目的是:搜集和保存史料,以求历史文化的真实,期待启蒙未来。
比如,黄宗羲编撰《明儒学案》,在资料的收集方面不遗余力。但他的根本目的并非出于“学案体”特征的网罗详备,而是为了所肩负的学术使命。他曾指出《明儒学案》的缺憾:“是书搜罗颇广,然一人之力闻见有限,尚容陆续访求。即羲所见而复失去者,如朱布衣《语录》、韩苑洛、南瑞泉、穆玄菴、范栗斋诸公集,皆不曾采入。海内有斯文之责者,其不吝教我,此非末学一人之事也。”(《明儒学案·发凡》)可见,在黄宗羲看来,学术史的编撰并非自己“一人之事”,而是事关天下,所以他号召“海内有斯文之责者”,要一起搜罗学术资料,共襄盛举,这无疑表现出他强烈的学术使命感。这种学术使命感渗透在他的所有学术研究中,无论是探索理论实质、研究历史事实、还是梳理学术史发展,无不体现出既是哲学家又是史学家的黄宗羲这一特点。
从总体上看,以上三个方面(“学案体”的研究范式、哲学史与哲学研究相统一的研究方法、“接着讲”与“如实讲”的学术使命感)在黄宗羲身上并不是没有关联的,而是形成一个整体,共同体现出黄宗羲学术史研究的特征。
三、黄宗羲学术史研究的意义
明清之际,黄宗羲编撰《明儒学案》的学术史成果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具有历史先导性的意义。其意义集中体现为:
1.突破霸权化的学术模式,形成对学术史本质的重新厘定。从历史发展看,从南宋后期至明代,程朱理学占据了学术界乃至整个思想界的主位,成为霸权化学术的代表,学者们对程朱理学的崇拜几乎到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地步。《明史·儒林传序》指出:“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镬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这就是说,明初学术的基本路向表现为,仅仅是对程朱理学的讲述和解释,几乎达到朱子学后再无学问、朱子学后再无真理的地步。三部《大全》即《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的纂修和颁布, 三部《大全》即《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三部书共260卷,成书于明永乐十三年(1415),由胡广、杨荣等主编。编撰三部《大全》的目的和宗旨乃在于“兴教化、正人心”,实现“家孔孟而户程朱”的“思想大一统”。三部《大全》的编撰和颁布,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原”的目的,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思想和文化的统一,而程朱理学亦由此确立了它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独尊”地位,成为明代官方的正统思想,但《大全》的学术价值颇受非议,如顾炎武评论道:“《大全》出而经说亡”。( 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388页。)朱子学被定于一尊,取得了其他学派无法抗衡的至高地位。
但是,唯权威是从显然是学术的异化。其根本之处是丧失了学术的本质,追求现成说法,这是黄宗羲在《明儒学案》的撰写中主要针对的陋习:“有明学术,从前习熟先儒之成说,未尝反身理会,推见至隐,所谓‘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耳。”(《明儒学案·姚江学案》)黄宗羲认为,学术根源于心之本体,本体并非限于一种模式或途径,所谓:“盈天地皆心也。变化不测,不能不万殊。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故穷理者,穷此心之万殊,非穷万物之万殊也。是以古之君子,宁凿五丁之间道,不假邯郸之野马,故其途亦不得不所殊。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于一途,使美厥灵根,化为焦芽绝巷。夫先儒之语录,人人不同,只是印我之心体变动不居。若执定成局,终是受用不得。”(《明儒学案·自序》)黄宗羲在序文中批评了定程朱理学于一尊的政策,指出,学术“出于一途”,只能使盈天地之心的“美厥灵根”,化为焦芽;使“变化不测”的心之本体,变成绝巷。
正是在学术不能出于一途、定于一尊的指导思想下,黄宗羲《明儒学案》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学术观念,形成“学不出于一途”、“论不主于一家”的学术史编撰,从而成为中国学术史的先导性著作,正如贾润在《明儒学案》序中所言:“盖明儒之学多门,有河东之派,有新会之派,有余姚之派,虽同师孔、孟,同谈性命,而途辙不同,其末流益歧以异,自有是书(《明儒学案》),而支分派别,条理粲然。其于诸儒也,……论不主于一家,要使人人尽见其生平而后已。”学术总是哲学家的学术,从一定的哲学观出发,哲学家们总是展开为个性化的研究(所谓“途辙不同”),那么,作为学术史研究就应该真实地汇集各家的成果,而不是学术“出于一途”。黄宗羲在《明儒学案·河东学案》记载,有人问吕柟:“今之讲学,多有不同者,如何?”吕柟答曰:“不同乃所以讲学,既同矣,又安用讲。”从《明儒学案》不难看到,明儒一家有一家之“宗旨”,不同讲学者用各自所立的“宗旨”为标识,这些纷然各异的宗旨,实际上就是对于突破霸权化的学术模式、重建思想世界的不同取向。黄宗羲的这种对一家有一家之“宗旨”的认识,无疑形成了对学术史本质的重新厘定。
2.把握时代的脉搏,真实地呈现学术演变的历史过程。从整体上看,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无疑主要是以王学为中心,除直接反映王学的《姚江学案》外,还有《浙中王门学案》、《江右王门学案》、《南中王门学案》、《王门学案楚中》、《北方王门学案》、《粤闽王门学案》,以及属于王学稍有变化的《止修学案》、《泰州学案》等,占学案总数的一半以上。莫晋所说的“是非互见,得失两存”,也是围绕着“宗姚江与辟姚江者”而言,所以,莫晋又说:“要其微意,实以大宗属姚江。”从《明儒学案》的布局,固然可以反映出黄宗羲本人的学术倾向,但也在客观上把握了时代的脉搏,真实地呈现出明代学术演变的历史过程。
从历史发展看,明代近三百余年的学术,在王学兴起之前,基本是“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也就是说,是一个朱学独尊的格局。明弘治、正德间,王学崛起,学人翕然相从,而晚明的思想潮流,最为突出的是王阳明的心学大为流行:“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一》)代表官方观点的《明史·儒林传序》中说,王守仁“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
然而入清之后,对阳明学“空谈误国”、“阳儒阴释”的批评铺天盖地,如清初的儒学家王弘撰说:“大抵阳明之学,真所谓弥近理而大乱真者。”(《格物》,《山志》卷五)吕留良则是近于谩骂:“王守仁,……朱子之罪人,孔子之贼也。”(《答吴晴岩书》,《吕晚村文集》卷一)王夫之则云:“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其究也为刑戮之民、为阉贼之党,皆争附焉,而以充其无善无恶、圆融理事之狂妄,流害以相激而相成。”(《序论》,《张子正蒙注》)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黄宗羲所选择进行的明代学术史研究,其内在之义便是深入考察明代学术的发展,真实地呈现明代学术演变的历史过程。当然,在这一过程中,王学渊源流变无疑是一个重点,不能不作为一个突出的内容加以对待。比如,对王学如何定位?其内在精神如何传播、演变?回答以上问题实际上就是对明代学术演变过程的真实呈现。
对于王学的历史功绩,黄宗羲毫不讳言地予以肯定。他认为:“自姚江指点出‘良知人人现在,一反观而自得’,便人人有个作圣之路。故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明儒学案·姚江学案》)应该说,黄宗羲的这一断言并非完全出于其维护学派、光大师门影响的需要,而是在深入考察时代的发展、以及当时学术演变源流的基础上所作出的客观的结论。
那么,对于阳明后学的失误,黄宗羲亦不袒护,所谓“宗姚江与辟姚江者,是非互见,得失两存”,即围绕着对王学宗旨的继承和丧失,黄宗羲总体上否定失去了王学宗旨的学者和学派,如“越中”;而肯定继承王学宗旨的学者和学派,如“江右”:“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东郭、念菴、两峰、双江其选也。再传而为塘南、思默,皆能推原阳明未尽之旨。是时越中流弊错出,挟师说以杜学者之口,而江右独能破之,阳明之道赖以不坠。盖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亦其感应之理宜也。”《明儒学案·江右王门学案一》
可见,判断是否符合王学宗旨即成为关键。黄宗羲所作的主要工作,就是辨析和分诀各家学说的宗旨。当然,以王学为宗旨分析各家学说,并非是要以“王学”去主导、规定各家,如此反而会形成一种新的“出于一途”的霸权学术模式,而这正是黄宗羲所要突破、摈弃的学术方法。因为王学本身的学术宗旨,是要求“人人反观而自得”、“人人有个作圣之路”,所以,以王学为宗旨分析各家学说,反而是要求从各个学者自身出发,从其自得、“得力处”总结出其学说的宗旨,以此得到整体的学术面貌,所谓:“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以一两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也。”(《明儒学案·发凡》)可见,黄宗羲虽然围绕“宗姚江与辟姚江者”,但其实是从各个学者自身出发,“分别宗旨,如灯取影”,充分地展示“其人一生之精神” (《明儒学案·发凡》)。
由此,黄宗羲之《明儒学案》才能够真实地呈现学术演变的历史过程,成为“一代文章之渊薮”,成为与时代变迁密不可分的学术史研究。其把握时展脉搏,客观地呈现学术信史的研究特征,对于现代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发展、建构,无疑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三,《明儒学案》体现出学术史的独立性,是现代意义上中国哲学史的先声。黄宗羲在《明儒学案》的编撰中,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的学术观,即不以君王将相为核心,不以政治题材为关键,而是真实、内在地考察明代学术的来龙去脉,这不仅是一个历史观的进步,而且还是中国传统学术史上的一个突破。梁启超对《明儒学案》的这一特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黄梨洲著《明儒学案》,史家未有之盛业也。中国数千年,惟有政治史,其他一无所闻。梨洲乃创为学史之格,使后人能师其意,中国文学史可作也,中国种族史可作也,中国财富史可作也,中国宗教史可作也,诸类此者,其数何限”。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九·新史学·中国之旧史》,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黄宗羲的学术史编撰,主要体现了学术史的独立性,对中国哲学史的产生和学科的独立性无疑具有积极影响。
从严格意义上看,中国传统学术中并无哲学或哲学史学科,但正是由于黄宗羲《明儒学案》的历史先导作用,不仅使中国哲学史,像中国政治史、中国种族史、中国财富史、中国宗教史一样“可作”,成为独立学科,而且在研究范式、研究方法上,也为中国哲学史能够保持自身的民族性,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免责声明
公务员之家所有资料均来源于本站老师原创写作和网友上传,仅供会员学习和参考。本站非任何杂志的官方网站,直投稿件和出版请联系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