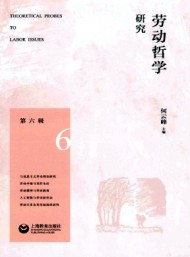哲学的正确说法范文
时间:2023-10-24 17:37:29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哲学的正确说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伊本•图斐利;哈义•本•叶格赞;政治哲学;伊斯兰思想;思想史
《哈义•本•叶格赞》是阿拉伯哲学家伊本•图斐利的著作。根据其生前记载,他的后半生几乎是在宫廷中度过的。他著书数卷,但能够流传下来的只有该著作,“其原因可能要归于他崇尚的思想。过去的年代里,持门户之见,暴虐迫害的群小们总是不遗余力地扼杀阿拉伯思想中追求光明,提倡科学研究和解放桎梏的一切精神产品(在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尤甚)。伊本•图斐利的思想必属被消灭之列。因此我们仅耳闻许多早期阿拉伯优秀进步著作的书目,却无缘目睹。” [1]2图斐利的著作也许就是遭到了这样的厄运。
图斐利生活在宫廷的政治旋涡之中,根据他的政治经验,他已经洞察到政治的有限性,并试图以哲学的沉思活动来超越和克服政治的有限性,《哈义•本•叶格赞》这部著作恰恰表现了这一点。他在《哈义•本•叶格赞》中以隐微的方式向我们表达了这样一个主题: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他的最高成就是什么?——哲学。这不能不让人联想起18世纪另一部著作——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它倒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展现了现代人如何征服自然的图景。《哈义•本•叶格赞》的创作早于《鲁宾逊漂流记》。有专家认为,笛福在创作《鲁宾逊漂流记》时,曾受《哈义•本•叶格赞》的启发。[2]391若如此,那么笛福的著作仅仅是对《哈义•本•叶格赞》著作的摹仿,这种摹仿是以启蒙式的主体性原则颠覆了古典的自然理性原则。这同时也是一次大的哲学反叛行动,即科学对古典哲学、现代对古代的反叛行动。这次行动提出一个尖锐而深刻的问题,即古典哲学在面对现代科学生活世界时如何生存。科学对古典哲学的挑战,使古典哲学面临合法性与正当性危机。于是,当我们再回到《哈义•本•叶格赞》的文本,对其进行解读时会发现,尽管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是对《哈义•本•叶格赞》的形式摹仿,但从前者对后者的思想观念或者精神实质的颠覆来看,恰恰表明了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古今之争。
篇2
现代西方哲学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和消解,确实取得了许多积极的理论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哲学的使命、功能和作用的现解。按照马克思和伽达默尔的看法,西方传统哲学的一个根本缺陷是理论和实践、沉思和行动的分离。这一方面导致哲学脱离生活世界之根,陷入无限反思的追逐中,难以找到生活需要的最终真实;另一方面理论和沉思固有的实践性要求又总是包含着规范生活的强烈冲动。哲学理论一旦获得意识形态或权威话语的力量,哲学就成为消灭差异性,制裁非理性的专制力量,用中性的说法是“以理杀人”,罗蒂说这是“学科帝国主义”或“概念帝国主义”。
哲学的这种文化霸权来自于知识和权力的复杂交织,并不完全是哲学自身的罪孽,而传统哲学的理论形态和思维方式却也难辞其咎。在西方哲学的传统中始终存在着精神物质化、概念实体化的倾向,哲学反思获得的概念认识总要被投射到外部世界之中作为实体化的本体而存在,似乎只有如此哲学真理才有坚实的对象基础,其结果是实体本体成为外在于人的异己的神圣存在。这种实体本体论的形而上学根源于西方哲学知识论的思维方式:哲学知识也是对象性的知识,是对某种实体本体的描述或反映。其实这种本体乃是超验的,是思辨构造的东西,它可能有逻辑存在的理由,却不具有经验存在的实在性。由于错误地把本体物质化、实体化,哲学规范成为自然定律一样的强硬规范,并且是绝对规范,因而隐含着成为某种“帝国主义”的危险。
哲学的基础主义、帝国主义或绝对主义也根源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传统成见,智慧、知识和真理是分成等级的,愈是普遍的、抽象的,愈是智慧的、真实的。实用的技能和影像中的世界不是智慧和真实,而理念的回忆和关于事物普遍原理和原因的知识才是最高的智慧。按照这种看法,哲学对其他文化形式和人类活动方式的统治就是合理的,哲学王或哲学家理应享有至高无上的文化特权。这种贵族式的哲学傲慢必然受到现代哲学家自由、平等意识的反抗,哲学不是一级真理,哲学不能给其他知识和伦理生活提供绝对的基础,哲学只是多种文化形式的一种,更激烈的说法称哲学是无意义的胡说。我认为,现代哲学对哲学功能、作用的限制是正确的,哲学与其他文化形式的关系应当作相对的理解,哲学相对于其他文化形式说并无天然合理的特殊效用和权力。
从哲学的文化功能和社会功能上我们可以接受相对主义的观点,但却不能接受哲学相对主义。哲学上的相对主义、怀疑主义、非理性主义等否定性哲学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相对主义的原则是否也是相对的,怀疑主义是否也怀疑自己的主义,非理性主义只能理性地言说,这并非仅是逻辑上的讽刺和机智,而是关乎哲学理论性质的根本问题。
合理的哲学形态只能是肯定性的、建设性的、绝对主义的形态,相对主义、怀疑主义、拆解和解构等只能视为有益的哲学评论或哲学批评,而不是哲学理论形态。原因是哲学在本性上即是人类思维的绝对性维度,正是因为话语方式、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样式等是相对的、多元的,人类才渴望获得对生活和世界的某种绝对理解。哲学真理不是具有更高概括性、更大普适度的科学真理,它是非对象性认识因而是绝对的真理。
按黑格尔、斯宾诺莎和庄子的看法,绝对是全体,因为不是全体就有与之相对的部分;绝对是无限,无限不是量性规定的“恶无限”,而是没有外在的它物限制;因而绝对是自由,无限的全体才是自决、自由的。绝对就是庄子无限神往的无待无凭的绝对自由。哲学思维的绝对维度就是人类自由的理想。
建立在主客体二元区分和对立基础上的对象性认识只能是相对的认识,因为它已先行设定了在对象之外的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的对立,从而对象性认识是不包括认识主体的有限认识。企图在对象性认识的方式中去获得对整个世界的认识,并构造某种世界观的理论,就是企图把认识主体抛出世界之外去观察世界。这虽然可以解释为通过认识的超越性来实现,而不是真的把人抛出世界之外,但终究无法摆脱萨特指出的对象性认识的疑难,比如以对象为认识对象,再以认识对象的认识为对象,进而以反思对象性认识的认识为对象,这将导致认识的无穷倒退,最终也无法达到对象性认识与自我意识的统一。所以,以自然科学思维方式建立的世界观理论既不是自然科学的真理,因为它超越了自然科学的实证性规范;也不是哲学的绝对真理,因为它是有对待的有限的认识,从而它真的是无意义的胡说。现代西方哲学对冒充科学的形而上学的批判是正确的。
以二元对立的自然科学思维方式不能获得绝对的哲学真理,但还存在着黑格尔所说的较高的思维方式、绝对的方法可以获得哲学真理。黑格尔认为,思辨的方法或辩证的方法就是绝对的方法、无限的认识方式。按照黑格尔,思辨的方法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克服对象性认识的弊病,一是思想以思想为对象,从而哲学认识就是自我意识,哲学意义的反思,是思维逻辑的自我展现和自身澄明,思想以思想为对象,已消融了自然意识的对象性、外在性,在思维和存在同一性的基础上可以获得绝对的哲学真理。二是思辨的方法或辩证法不是主观的方法,是认识沉入思想内容、按照思想内容自己运动的逻辑获得的理论自觉,所以就没有了主观方法与客观内容的对立,甚至可以说辩证法就是无方法,即无可以主观任意使用的方法,从而才能面向事物本身,把握思想内容自己运动的绝对真理。
哲学追求绝对真理必得有不同于自然态度思维的绝对方法的保证,这也是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的根本意义。思维总是对什么的思维,思维必有对象,看来对象性思维是思想的本性,这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日常生活和自然科学的自然态度思维超验地设定了对象的客体性和外在性,因而必须加以还原,同时还归于内在的意识之中。而内在于意识之中的思想对象可被理解为意向性构造的产物,从而现象学牢牢地坚守着意识内在性和自明性的直观视野,力求获得严格科学的哲学真理,亦即绝对的哲学真理。
篇3
什么是稻盛哲学?
稻盛先生曾为我的著作《答案永远在现场》作序,我认为,在近一千字的序言中,他把自己的思想基本说明白了——所有的东西都在现场这个基础上,一个纬度是稻盛哲学、文化、心智,一个纬度是阿米巴经营体系。
可以把稻盛哲学的总体架构比喻成一座房子,地基是“在现场”,两根柱子是稻盛哲学和阿米巴经营。我认为,我在里面做了一个小小的工作,即要让公司的每一个员工,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不断地改善。在这个过程中,按稻盛先生的说法,就是能形成心性的极大的提升。
什么是稻盛哲学?如果把这个问题提给稻盛本人,根据我对他的体悟和了解,他可能会这么回答:稻盛哲学就是当一个人碰到困难和问题时,他的解决办法。比如说,我从27岁创业,我是搞技术的,既不懂金融也不懂管理。在这个过程中,我碰到过很多看起来不可能克服的难题,我当时就一门心思地把问题解决了。在这个过程中,心理的压力是很大的。在解决问题后,我就把这个过程及时地记录下来,例如,在心理上是如何调整的,然后就让员工在第二天晨读,在这个过程中,又对其进行修改。在这个反反复复的过程中,稻盛哲学就形成了。
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的稻盛和夫的书,并不是稻盛和夫今天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回首往事,然后去想这个事是如何处理的,那个事怎么处理错了。他是边干、边记录、边修订,然后把以前写的东西整合起来。正是如此,在阅读他的书时,我们都会感到亲切,有一种在场感。可以说,稻盛哲学的缘起就是从实践的地图上克服问题的一种心理过程。
人人都是稻盛和夫
在稻盛和夫经营企业和创建两家世界500强的过程中,他醒悟了一个很大的道理。我认为,如果中国企业家和高管能对这个道理有些许体会,就可以解决很多难题。稻盛和夫取得了很辉煌的成绩,他后来反思,对于公司而言,什么是最重要的?是高管?是技术设备?是强大的资本?都不是。最重要的是,在一线岗位上,有没有负责的分析问题、判断问题,创造性解决问题的员工。因此,我认为,如果用一句话概括稻盛的理论,有可能是“人人都是稻盛和夫”。哪怕你级别再低,哪怕你刚参加工作,你也可能是经营者,也可能是稻盛和夫,而不是只有那些管理人员才是。中国企业有一个怪象,高管往往以为员工是愚蠢的,而没有认识到员工都是充满智慧的。
我认为,企业管理的重点不是做别的,而是唤醒一线员工的生命感和价值感,然后激发他们去创造。如果中国企业家和高管,在学习稻盛和夫的过程中,能够领悟到这一点,可能就不会“头疼”了,员工也会很开心。
很多人都在探讨稻盛和夫拯救日航的奇迹。在我的著作《垂直攀登:稻盛和夫的生命智慧与经营哲学》中,我总结了14点。但我发现,稻盛和夫在拯救日航时,就是在打造一个 “活力场”——只要你进入其中,就会极大的专注,追求工作中的极致。
那么,如何去打造这个 “活力场”?我在书中有一些总结,有哲学的统一,体系制度的建设,有一整套唤醒员工生命感和价值感的方法,还要有稻盛和夫这种摸底灌顶的方式——他要激发每个人的能力。在三个月内,和三万多名员工握手,并询问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他的“信”,稻盛和夫建立的气场是一个充满信任(自信、被信、互信)的一个场。如果你的企业也有这么一个场,还有什么做不好的?在这一点上,中国很多企业家往往会比较纠结,感觉那是日本文化,在中国价值紊乱的社会背景下,很难做到。但我不这么看,关键还是你自己,作为当家人,你信不信你自己的这颗心。自信不疑人,疑人不自信,你自己整天都在猜疑,想让你的高管,你的员工不猜疑,可能吗?因此,用简单一句话概括,稻盛和夫拯救日航,就是构建一个活泼泼的“活力场”,让每个员工去极大的专注,不断地创造新的业绩。
以稻盛哲学的缘起之法,形成中国企业自己的哲学
在今年的3月16日,稻盛和夫了一条微博。他说很多人老是问我为什么成功。我给他们反复说,他们也不信。你要再我问,我还是要这么说,就那么一个点——作为人,何谓正确。他说,不是作为京瓷公司,何谓正确;不是作为企业主,何谓正确;也不是作为我是经营之圣,何谓正确;而是作为人,何谓正确。因为是“作为人,何谓正确”,就有了普遍的价值,就可以跟员工哲学共有。
如果把稻盛哲学说成是这个样子,如果说稻盛哲学的缘起之法无非是及时地记下来,是在和员工长时间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那么,中国企业有没有哲学?中国企业在“冰封时代”开始搞企业,一系列的难题是稻盛和夫还没有碰到过的。这些难题一个一个都解决了,中国企业发展到现在,是一大堆人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如果把解决这些问题的心法、过程、事件记录下来,再提炼出来给八零后、九零后,甚至将来的两千后来传承,同样是“稻盛哲学”。
但很多中国企业人和中国企业家没有意识到,哲学就在他的身边,反过来去外求,外求的结果就是会形成很多智障。比如,有些人在传播稻盛哲学时,往往把稻盛和夫说成神,我们要有虔诚的心理,要一句顶一万句。但是,只是学稻盛哲学的文句是没有用的,必须要结合企业的问题和实践来学。
之前,一个企业家告诉我,他买了五万块钱的稻盛和夫的《活法》,要发给员工看,改变他们的工作态度。我说大错特错,你以为员工工作态度的转变,是看了一本书就可以了?不是,他会拿着稻盛和夫的书,360度地照你,看你是不是洗脑的,光说不练。反了,稻盛哲学不是用这种方式让人去学的。首先,要看企业家自己有没有这种生命状态,要以身作则地来传承。
篇4
莱布尼兹(G・W・von Leibniz 1646~1716)是西欧17~18世纪初著名的学者。他虽是德国人,但他的活动和影响都绝不只限于德国,甚至也不限于西欧。他是对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有广泛影响的一位学术界的巨子。众所周知,他首先是一位数学家和哲学家:他和牛顿各自独立地发明了微积分,并首先创立了二进位制算术;他创立了一个以“单子论”闻名的很有自己独特性的哲学体系。但他的成绩也绝不限于数学和哲学,而是涉及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以至如当时的普鲁士国王腓力烈大帝惊叹说莱布尼兹“本人就是一所科学院”!有人认为莱布尼兹几乎掌握了他所处时代的所有学问,并在其中许多部门都居于前列或领先地位。
莱布尼兹很少写过专门讨论中国问题的作品,但他的《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哲学》则可说是唯一的例外,如标题所示,它是专门论中国哲学的,而且篇幅较长,译成中文约4万字,这就不是一封寻常的信,而完全可以说是一项学术论著了。
首先我们要了解这封信的背景。我们知道,1581年,即明万历8年前后,耶酥会士,意大利人利马窦来华,开创了天主教来中国传教的事业,也可说是“西学东渐”之始,因为这些大都属于耶酥会的传教士、来华除了传教之外,也带来了西方的一些科学文化知识,特别是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的知识,继利马窦之后陆续来华的这些传教士,包括先后担任来华传教团首领的汤若望、南怀仁、白晋等人,都有一定的科学知识,许多人都曾在明末清初的朝廷里做官,担任过钦天监监正、监副,太常寺少卿等官职,如以上已提到的有些还成为中国皇帝的钦差大臣,命他们回西方招请更多传教士来华,或从事外交活动。当时中国一些有进步思想、奋发有为的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也从他们学习,或和他们合作翻译出一些西方的哲学和科学书籍。
最初来华的耶酥会士,为了传教,也要研究中国传统的和当时的文化思想,以便了解中国人的传统习俗和当时的思想心理状态等,才能够针对性地诱导中国人皈依天主教。他们看到中国是这样的一个泱泱大国,又有几千年历史,有自己成体系的思想文化传统,绝不能像对待其他的一些落后的乃至野蛮的民族那样,可以完全不顾或抹煞其传统习俗等,而直接对他们“灌输基督教文明”。因此他们认为只能是他们所倡导的这条道路: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及礼仪习俗等之中,找出那些和天主教的教义及礼法不相矛盾的成分,并把它们解释成和天主教一致,以便使中国人相信天主教是符合他们的祖宗成法的,因此就可较顺利地接受天主教而成为其信徒。这就是从利马窦以来多数耶酥会传教士的主张。这样,在他们看来,例如儒家经典中的“天”、“上帝”等观念,和天主教的“天主”观念就是一致的;而中国人的相信“鬼神”、祭拜祖先,也正说明了中国人也和天主教徒一样信仰灵魂不死,人死后还有来世生活,如此等。因此,他们认为中国的一些礼仪和习俗,是并不违背天主教的教义教规的,天主教及其传教士对这些应该加以容忍或接受,并藉此来诱导中国人皈依天主教。
但是耶酥会传教士中也有些人不同意这些主张的,虽然在耶酥会中这样的人是少数,但确实存在,如龙华民就是其著名代表。在他们看来,中国儒家所讲的“天”,如历代中国皇帝所祭祀的“天”,就是头上那物质性的蓝天,儒家学说的实质是唯物主义、无神论的,他们所实践的乃是一种“偶像崇拜”,和天主教的教义教规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天主教会及其传教士也绝不能容忍和接受中国基于儒家传统的种种礼仪习俗,而应加排斥。
这常所谓“礼仪之争”,是历史上一桩著名的公案。它先是在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之间进行,后来传回西方,不仅整个天主教从教廷到国外布道团等宗教界人士,而且还有一些非教会神职人员的社会名流,也都参与了这场争论。
了解以上历史背景,对了解莱布尼兹的这封信的内容,自然是很必要的。但如果把莱布尼兹的这封信,仅仅看作当时的“礼仪之争”中一方的某一成员对这场争论的一些问题的看法的阐述,这就大大贬低了这封信的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了。我认为,这封信首先较集中明确地表述了莱布尼兹对中国及其文化的尊重和推崇的总态度,和以后一些“西方中心论”者,特别是西方帝国主义分子对中国及其历史文化的轻视、诬蔑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是值得人们去作一番深入反省的。其次,从这封信中我们也应看到,莱布尼兹不仅在阐述他所理解的中国,而毋宁说他更多地还是藉此更进一步来阐述他自己的哲学思想。他实际上是从自己的哲学思想出发,凡是他认为中国哲学中与他自己的哲学主张相符或可以解释为一致的,就加以肯定,否则就加以摒弃。特别可注意到他的这封信写于1715年11月之后,这意味着最迟也是他逝世前一年的作品,是他晚年完全成熟的思想表现。与其说这封信阐述了中国哲学,不如说莱布尼兹是在逝世前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对自己的哲学思想的又一次表述。这对研究莱布尼兹本人的哲学思想,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至于谁如果想从这封信来理解中国哲学,则就难免上当。
因为限于历史条件,莱布尼兹所能掌握的中国哲学的资料非常有限,他其实主要就是根据龙华民和利安当等在其论著中所述的材料来理解中国哲学的,而龙华民和利安当既反对中国哲学,他们所引述的材料就难保不受歪曲或肢解,莱布尼兹以此为据,自然也难保正确。再加上他――也许出于善意――常常以自己的观点为依据来解释他所理解的中国哲学,就更可能陷入双重的误解或曲解,因此莱布尼兹在此信中所表现的他对中国哲学的理解,有许多是并不符合中国哲学的原意或本来面貌的。这本不能渴求于莱布尼兹。他的这篇作品虽不能作为理解中国哲学的依据,但作为理解当时西方一位大哲人、大学者的莱布尼兹对中国哲学的看法仍有其十足的历史价值。实际上,当时争论的双方又何尝有哪一个是真正准确地理解了中国哲学的呢?又怎能独独责怪莱布尼兹?但不管怎样,指出莱布尼兹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并不准确,对于理解和评价莱布尼兹对中国的看法自然是必要的。
莱布尼兹在这信的开始不远处的一段话,可看作他对中国及其文化的总态度的表述,他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它在版图上不次于文明的欧洲,并且在人数上和国家的治理上远胜于文明的欧洲。在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有一个极其令人赞佩的道德,再加上有一个哲学学说,或者有一个自然神论,因其古老而受到尊敬。这种哲学学说或自然神论是自从约3000年以来建立的,并且富有权威,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而希腊人的哲学却是第一个,地球上的其余地方还没有什么著作,当然我们的《圣经》除外。因此,我们哲学后来者,刚刚脱离野蛮状态就想谴责一种古老的学说,理由只是因为这种学说似乎首先和我们普通的经院哲学概念不相符合,这真是狂妄之极!再说,除非用一场巨大的革命,人们似乎也摧毁不了这种学说。因此,如果能够给它以一种正确的意义,那将是非常合理的。”
“不管怎样,我觉得鉴于我们目前面对的空前的道德没落状况,似乎有必要请中国的传教士到欧洲给我们传授如何应用与实践自然神学,就像我们的传教士向他们教授启示神学一样。因此我相信,若不是我们借一个超人的伟大圣德,亦即基督宗教给我们的神圣馈赠而胜过他们,如果推举一位智者来评判哪个民族最杰出,而不是评判哪个女神最美貌的话,那么他将会把金苹果判给中国人。”莱布尼兹对中国文化非常推崇。
那么,莱布尼兹在中国人的学说中,究竟看到了些什么呢?
篇5
这两位哲学家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都出生在1889年。即使不相信生辰八字,这个事实仍可能满重要的。例如,共同的时代背景可以部分说明怎么一来他们两个都对语言问题特为关注。维特根斯坦当然从头至尾是一个“语言哲学家”。海德格尔早期哲学就把语言放在一个极重要的地位,后期则把语言视作“存在的家园”。在《语言的本质》一文里,这位存在哲学家甚至会断言“语言给出存在”。无论海维两人的思路相去多么远,我以为他们的哲学仍然具有共同的时代关怀,这一点我们最后将稍加概括。海氏和维氏都是德语作家,一个是德国人,一个是奥地利人。考虑到民族语言对思想的影响,这个事实也不是无足轻重的。维特根斯坦虽然是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的泰斗而且他的影响在英语世界里比在德语世界法语世界里要更为广泛,但我们还是看得出他的运思方式和流行的分析哲学往往大相径庭。当然,和海氏不同,维氏从来没说过只有德语适合表达哲学。事实上,人们甚至可以设想,如果认为日常语言有一种共同的逻辑结构(早期)或日常语言挺合适的(晚期),维特根斯坦可能会以为各种语言的效力都是等同的。维特根斯坦没有这样说,我也不相信这是他的意见。这两位思想家还有一个特别的共同之处:他们各自的晚期哲学都和早期哲学有很大的差别。维氏在后期鲜明批判了自己早期所持的很多观点,早期和晚期的表述风格更是南辕北辙。海氏有所谓的kehre,转折,其前后期的文风也截然不同。wwW.133229.COm不过在他那里,前后期的差异不如在维氏那里突出。本文涉及的,主要是两位哲人后期的思想。
就语言哲学而论,海氏和维氏也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从他们所批判的学说来看,最为明显。两个人都反对意义的指称论、观念论、图象论和行为反应论,都反对把真理理解为语句和现实的符合,都反对把语言理解为内在之物的表达,都反对从传统逻辑来理解语言的本质,都不承认逻辑斯蒂语言在任何意义上可以取代自然语言。
从建设方面看,两人的共同之处亦复不少。不过,照这样来比较海维二人,就仿佛他们是两位感想家,对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表达了这样那样的意见。可实际上我们面对的是两位罕见的哲人,沉浸在思想的事质深处,应答着“存在的无声之音”。所以,找出一些语录来,像这样对照海氏和维氏之同之异,远远够不着这两位哲人的对话。他们可曾对话呢?没有资料表明海氏曾读过维氏,维氏对海氏的评论我也只读到过一处。然而,思想像道路一样,其要旨无非“通达”二字;就事质本身所作的思考,必相互通达,形成对话。只不过,袖手旁听,是听不到这场对话的。要听到海氏维氏的对话,我们自己也必须沉入事质的深处,我们自己必须参与对话。限于功力,更由于对话的本性,下面的讨论无疑会使每一个对话者的思路变形。本来,本文的重点不是介绍这两位思想家,而是希望通过道路的分合,导向我们共同关心的课题。
语言哲学[1]的中心问题是意义问题和语言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这两个问题又交缠在一起。以指称论为例:语词的意义即是语词所指称的事物;一句话有没有意义,就看这话和所指的事物吻合不吻合。这样,指称论不仅对意义问题有了个交待,而且建立了语言和现实的关系。
指称论虽然简单明了,却远不足以解释形形的语言现象。更要命的是,它似乎自身就包含着逻辑上的矛盾。要拿所说的和实际情况比较,我们必须已经知道所说的是什么意思了;于是意义或意思似乎就必须独立于实际情况就能确定,于是意义就变成了一个和现实脱离的自洽的系统。意义的观念论,或粗糙或精致,大致也在这样的思路上打转。观念论即使对意义问题提供了一个说法,谈到语言和现实的关系,却往往大费踌躇,而且同样难逃符合论的陷阱。
人们从多种角度列举出这两大类理论的缺陷。例如,我可以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糖,但掏不出一块糖的意义来。这类批评诚然正当,甚至犀利,但限于否定——就是说,没有提示出新思路。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对这些理论的批判,与此类不同,他们的批判开启新的思路,因而是建设性的。初接触维氏的读者,往往觉得他总在瓦解各种成说而不从事建设。这是误解。诚如海氏维氏同样见识到的,哲学的首要建树,不在于构筑理论,而在于引导思考上路。
海氏和维氏对以往语言学说的批评,不在于发现这些成说中的各种逻辑矛盾。他们从根本上对语言的存在论地位作了重新审视。一上来,语言就不被认作某种在自然之外生活之外反映自然反映生活并和自然生活符合或不符合的符号体系,而是被认作一种活动,和人的其它活动编织在一起的活动。海氏在其早期著作《存在与时间》里就明确提出“语言这一现象在此在的开展这一生存论状态中有其根源”(sz,161页)。[2]这始终是海氏看待语言的一条主思路。相同的思路也为维氏所具有,集中体现在“语言游戏”这一提法里。
“语言游戏”这个用语有多重意思,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在于强调语言是人类生活的一个有机部分。就此而论,“语言游戏”这个译法不很好,因为德文词spiel里“活动”的意思相当突出,只从“遵循规则”来理解是不够的。至于望文生义,以为“语言游戏”是说“话只是说着玩玩的”,当然就更不得要领了。“语言游戏”是“由语言以及那些和语言编织成了一片的活动所组成的整体”(pu,7节)。[3]
语言和其它人类活动交织在一起,这本来是语言研究的常识。普通语言学家bolinger观察说,我们坐下、起身、开灯、做工,让我们在作这一切的时候都转动大拇指,将是一件极为荒唐的事情;但所有这些活动都伴随着语言,却是十分正常的。“其它行为都自成一统。而语言却贯穿在所有这些活动之中,几乎从不停止。我们单独学习走路,但我们无法那样来学习语言;语言必须作为其它活动的一部分得到发展。”[4]
从人的生存情境出发,突出的一点就是承认人类活动包括理解活动在内的有限性和与此相连的历史性。海氏早期不断强调此在的有限性,后期则不断强调存在的历史性。维氏不大喜欢反复使用“有限性”这样的概念,但在他对逻辑主义的批评里突出阐发了人类认识的有限性--不是作为一种缺陷,而是作为认识的必要条件。
我说“逻辑主义”而不说“传统逻辑”,因为维氏并不是在逻辑框架内发现了传统逻辑里有一些错误。他关注的不是逻辑体系在构造上是否完备,而是逻辑主义者从认识论上赋予逻辑像上帝的认识那样一种绝对必然性和绝对正确性。“思想被一个光轮环绕。——逻辑,思想的本质,表现着一种秩序,世界的先验秩序;即世界和思想必定共同具有的种种可能性的秩序。但这种秩序似乎必定是最最简单的。它先于一切经验,必定贯穿一切经验;它自己却不可沾染任何经验的浑浊或不确--它倒必定是最纯粹的晶体。”(pu,97节)
维氏当然不否认有合乎逻辑不合乎逻辑之别。张三今年二十李四今年十八,这话可能对可能错。是对是错,要到派出所查了户口本才知道。如果说错,那是事实弄错了。但张三今年二十李四今年十八,所以李四比张三岁数大,这就不合逻辑。或者,不管他们到底多大,只要听到说张三比李四岁数大同时李四又比张三岁数大,我们就知道说话的人犯了逻辑错误。我们不须查户口本就知道错了,再怎么查也查不出它对来。
logik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词logein,说;不合逻辑就是不合我们的说法,就是违背了语法,从而语言就在空转。据海氏考证,在希腊早期,logos及其动词形式logein既意指“说”,又意指“让某种东西现出”。这两个含义又完全混而为一。就原初情形考虑,任何言说都是让某种东西现出,而任何让某种东西现出的活动也都包含了言说。维氏大概没下过这份考证功夫,但就事论事,他恰恰也提出“说就是让人看”。不合事实,相当于:给我看了一样假东西;不合逻辑,相当于:什么都没给我看,说了等于没说。这样的语句,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错误”:它合乎教科书上的语法而不合乎真实的语法,它貌似句子而其实不然,就像乔姆斯基编造的那个例子“绿色的想法疯狂沉睡”,我们弄不明白它说的是什么,我们无法设想它所“描述”的事态。
但这种词源考据有什么意思呢?拿“语法”代替“逻辑”,用“让人看”代替“说”,不就是换个说法吗?“换了个说法”这个说法,有时有贬义:不管你叫它什么名字,玫瑰依旧是玫瑰。事情还是那么回事情,只是说法不同而已。如果天下的事情都是孤立的,那么怎么改换说法都没有意思。然而说之为让人看,就在于说让事情在不同的联系里显现。从一个角度看不见的,从另外一个角度就可能看见,从一个角度看不清的,从另外一个角度就可能看清。“语法”和“逻辑”涵盖的,并不相等。但即使两者重叠之处,说是语法还是逻辑,仍可能十分不同。
例如,a+b=b+a,以往被视作逻辑命题,维氏则视之为转换表达式的语法句子。a=a以往也视作逻辑句子,但它显然不是用来转换表达式的语法句子。那它是个什么句子呢?是个毫无意思的句子,如此而已(pu,216节)。
至于像“每个色块都与它的周界正好吻合”,“我无法偷走你的牙疼”或“青春意味着生长”这样的句子,时常引起逻辑学家的疑惑。它们不大像是逻辑命题,但若说它们是经验命题,它们却似乎必然为真永恒为真。在维氏看来,“每个色块都与它的周界正好吻合”无非是多多少少经过特殊化了的同一律。“我无法偷走你的牙疼”是“必然真理”,是因为“不是一件可以搬动的东西”属于“牙疼”的语法,限制着“牙疼”这一用语的使用方式,而“偷走牙疼”这类说法则违背了我们的语法。如果“牙疼”不仅指称一种感觉,同时也指称扎在牙龈上的细刺,那么我们就可以设法偷走一个人的牙疼了。
维氏通常不像海氏那样用某个词囊括一整套思考,为此甚至不惜改变这个词的通常意义;但他的“语法”却不是语法教科书里的“语法”,而是概括维氏建设性思想的主导词。批判逻辑主义,海维二人一样强烈。这种批判所提示的道路呢?不谋而合,海氏恰也是用“语法”这个词来提示的:要真正了解语言,就要“把语法从逻辑里解放出来”(sz,165页)。不过,“语法”不是海德格尔哲学里的主导词,探讨哲学语法,探讨逻辑和语法的关系,维氏远比海氏具体而微。
难道“我无法偷走你的牙疼”不是对现实的某种必然关系的描述,而只是一些语法规定吗?难道生长和青春不是现实地联系在一起而只是在语法上联系在一起吗?为什么我偷不走你的牙痛却可以分担你的痛苦?我们要问的却是:我们把什么叫做“牙痛”而把什么叫做“痛苦”,我们为什么把这些叫做“生长”把这些叫做“青春”?这些诚然不是逻辑意义上的语法问题;它们是哲学语法问题,就是说,是语词和存在的基本关系问题。生长的确属于青春;也就是说,“青春”就语法而论和“生长”联系在一起。我们把这些而不是那些叫做“青春”,这不是随随便便叫的。我们就不把金属的硬度叫做“青春”。我们的语言应和着存在的无声之音。“本质[5]表达在语法里。”(pu,371节)
这一论旨和海氏的基本思想镜映生辉。而且我认为,这一思想海氏比维氏阐发得更为透彻。
海氏通常以“命名”为题来讨论语词和存在的关系。不过他说的“命名”,不是一端有一个现成的对象,另一端有一个词,我们用诸如贴标签之类的方式把语词和事物联系起来。命名拢集物,使物在与它物的关联中显现,从而具有意义。因此,命名不是建立一个对象和一个语词之间的联系。命名建立的是一个语词在语言整体中的位置,这又是说,建立一物在世界中的位置。而一物只有在世界中有一个位置,才能显现。海氏从来就是在这种现象的意义上理解事物之所是或事物之存在的。事物唯通过言词才是其所是而不是其所不是,才就其存在显现出来。“哪里没有语言,哪里就没有存在者的敞开……语言第一次为存在者命名,于是名称把存在者首次携入语词,携入现象。名称根据其存在并指向存在为存在者命名…宣告出存在者以什么身份进入公开场…取缔存在者藏掩退逃于其中的一切混沌迷乱。”[6]在这个意义上,海氏可以说:语言给出事物的本质(存在)。在相同的意义上,维氏可以说:本质(存在)表达在语法中。海氏说:本质和存在都在语言中说话。维氏说:“语言伸展多远,现实就伸展多远。”这远非“唯语言主义”可以一语了得。海维二人的意思恰恰不是:我们怎么说,现实就成个什么样子。而是:语言里所凝聚的存在是什么样子的,语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就只能那样来述说现实。海氏把这一思想结晶在“语言自己说话”这一警句里。我们首须倾听存在之言始能说话。
就本质言,语言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语言支配人而不是人支配语言。这一思想在欧洲大陆思想传统中本有其渊源。欧洲语言哲学的开山祖洪堡德明言“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就是他的语言”。对法国语言哲学深有影响的索绪尔把语言放在言语的前面。海德格尔沿着这一传统,直思到语言极至处的简朴。
海氏一向不从工具性来理解语言的本质。工具改变对象,而语言恰恰一任存在者如其所是。这样想来,他谈的竟不是语言,而是事物。实际上,海氏反复强调,我们无法把语言作为对象来议论。语言有所说,而不被说。那么,我们怎么思考语言的本质呢?逗留在语言之中。逗留在语言之中,就是让语言有所说。言而有物:人在说话,显现的是事物。我说“凤姐也不接茶,也不抬头,只管拨手炉里的灰”,我说的不是言词,我说的是凤姐,说的是拨手炉里的灰,说的是这么个粉面含春威不露的女人。人用种种方式说着,包括通过沉默发言。用言词来说,只是道说的一种突出形式。本真的道说本来是显示,让万物各归其本是,因而,“语言的本质存在恰恰在对自己掉头不顾之际,才愈发使它所显示者得到解放,回归于现象的本己之中。”[7]在适当的(译维氏语)本真的(译海氏语)言说中,言而有物的时候,言词消隐,出场的是事物。我们听到的不是言词而是事情。言而无物,我们才觉得词藻堆砌,压迫我们,我们才说:“words, words, words!”
语词和对象相应,语词表达对象,这是人的根深蒂固的成见,就像欧基里德空间一样。即使语言哲学家在原则上并不赞同这种成见,在思考具体问题的时候仍然可能经常套用这个模式。从这里看,语言哲学中的很多基本观念,和传统认识论中的很多基本观念一脉相承,无论在指称论里还是在观念论中,意义的符合论差不多就是经过语言哲学改装的认识的反映论。维氏说:“一种原始的哲学把名称的全部用法浓缩进了某种关系观念,同时这种关系也就变成了一种神秘的关系。”[8]海氏遥相呼应:首要的关系不是语词和事物的关系,而是:语词就是事物的关系;“言词把每一物拥入存在并保持在存在里,就此而言,言词本身即是关联。”[9]
可见,海维所讲的“本真之言”,与符合论里所讲的“真命题”大异其趣。本真或不本真全在于是不是言之有物。凤姐云云,也许本无其事,但满可以言之有物。你到人家作客,进门就说“桌子上摆着一只茶壶四只茶杯”,说得可能完全正确,却又完全不适当。符合论自有逻辑上的矛盾,但那还在其次。更值得提出的,是符合论只注意到现成语句和现成事态是不是吻合,而全然不曾留意语言的源始意义:语言提供了使现实在其可能性中显现的“逻辑空间”。海氏在《存在与时间》里就把此在对存在的理解和可能性联系在一起并提出“可能性优先于现实性”的思想。维氏也从一开始就已经洞见,语言把世界转变成了一个可能的世界。“在命题里,我们仿佛用试验方法把世界装到一起。”[10]这一思想维氏始终保持如仪:“我们的眼光似乎必须透过现象:然而,我们的探究面对的不是现象,而是人们所说的现象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我们思索我们关于现象所作的陈述的方式。”(pu,90节)之所以如此,用维氏的话说,是因为一个命题必须由部分组成,其部分必须能够在其它命题中出现。用海氏的话说,是因为言说和理解是同等源始的,而言就是理解的分成环节互相勾连的结构。这两种说法异曲同工,探入了语言之为语言的机关。正因为在这种源头的意义上来理解语言,海德格尔甚至犹豫还该不该用sprache(说,语言)这个词来称谓他所讲的事质,因为sprache毕竟可以意指而且通常也的确意指用现成的语词来述说现成的事物。
言词之可能指称独立的物,本由于事物通过言词才成其为独立之物,并作为独立的存在者拢集它物,与它物关联。这当然不是说,人必须先发明出语言,才能依之把事物分门别类加以勾连加以表述。语言就是事物的区别和勾连。逻辑形式不是在语词和事物之间,仿佛一边是语词一边是事物,共同的逻辑形式作为两者的关系,把两者联系起来。而是:语言就是事物的逻辑形式--语言(命题、思想)之所以和现实有同样的逻辑形式,因为思想就是现实的逻辑形式。“命题显示现实的逻辑形式。”[11]特别当我们考虑到逻辑、logik、logos、logein本来就是“说”“道”--语言就是事物能够被说出来的形式。西方思想中的“am anfang war logos[泰初有道]”和中国思想中的“道生万物”一脉相通。
有人以为维氏对意义理论的批判和对生活形式的强调所表达的只是语用学语境学的关注。维氏对用语和语境联系的细致入微的注意迷惑了这些读者。在我看,实情完全相反,维氏对语用学语境学没有任何兴趣。他通过几乎貌似琐碎的细节所考察的恰恰是高度形式化的规范问题。维氏有时也这样提醒读者。一处,他对灵感现象和遵行规则的现象作出区分之后说,我们在这里关心的不是灵感的经验和遵行规则的经验,而是“灵感”和“遵行规则”的语法(pu,232节)。的确,如果我们不首先知道应该把哪些行为叫做“遵行规则”,我们从哪里开始反省“遵行规则的经验”以及其它一切伴随遵行规则的现象呢?诚如维氏自断:“我们的考察(始终)是语法性的考察。”(pu,90节)其中很大一部分人们从前笼统地称为“逻辑问题”。维氏的方法不单单体现了某种个人风格。这是一种新的哲学思考实践——不再在概念之间滑行,而是在粗糙的地面上寻找路标。
但发现规范,不就是在形形的表达后面在语言的历史演变后面发现某种深层的不变的东西吗?我们不是最终还是要乞灵于逻辑的必然性吗?规则是给定的,因此是某种先验的东西,我们只能遵循。
这里我们看到了语法和逻辑的本质区别。语言是给定的,但不是超验的给定而是历史的给定。transzendent,transzendental,a priori这些术语,在西方哲学史上盘根错节,中文译作“先验的”“超验的”“超越的”“先天的”等等。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当代中国学术语汇的困境:我们既要了解这些语词背后的西文概念史,又要了解中文译名的由来;如果这些中文语词有日常用法(但愿如此!),我们就还得考虑术语和日常用法的关系。语法也许可以说是先天的甚至是先验的,但怎么说都不是超验的。“先天”这个中文词所说的,虽然是给定的,但绝不是超验的。先天近视的人,不得不把近视作为事实接受下来,但他的近视并不因此比后天的近视多出什么神秘的超验的来源,而且,通过一定的治疗或其它技术手段,先天的近视一样可以纠正,或者,可以改变它带来的后果。我不想把维氏所说的语法和海氏所说的存在之言简化为这样的先天性,我只想说明,要理解这两位哲人,我们必须放弃先验/经验的传统模式。
那么,为什么我们的语法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为什么我们把“绿”单单用作颜色词而不同时把它用作长度词?把“疼”限制为一种感觉而不同时包括引起这种感觉的东西?这里不是逻辑在起作用吗?是的,如果“疼”一会儿指一种感觉,一会儿指一种颜色,我们的语言的确会变得非常不合逻辑。而这首先是说,我们的语言将是一团混乱,不再是一种适合我们使用的语言。语法的逻辑来自生活的逻辑。语言给予我们的不是一堆事实,而是连同事实把道理一起给了我们。我们的语言如其所是,是有道理的。给定了这些道理,我们必须这么说而不那么说。但并没有什么逻辑必然性迫使我们的语言是这个样子而不能是另一个样子。我们的语言是一种相当合用的有道理的语言,倒要通过自然的源始涌动(海氏),自然史,人类的生活形式,语言和其它人类活动相交织的“语言游戏”(维氏)加以说明。
我们要讲逻辑,但我们更要讲道理。道理不像逻辑那么权威,非此即彼。一段话要么合逻辑要么不合逻辑,却可以很有道理,有些道理,多少有点道理,毫无道理。道理也不如逻辑强悍,你死我活,要是咱俩得出的结果不一样,那至少有一个错了。然而,可能你有道理,我也有道理。中国话像这个样子,自有它的道理;德国话和我们很不一样,却自有德国话的道理。逻辑从天而降,道理却是前人传下来的。当然,海维二人都不承认有一种和其它一切道理都性质不同的逻辑。逻辑也是一种道理,一种极端的道理,一种我们优先承认最后修正的道理。
维氏把语言的本质从逻辑转化为语法,海氏把语言的本质理解为具有历史性的存在之言,两者息息相通。语法和存在是“给定”的,然而,是在历史意义上的给定,而不是在超验的意义上给定。我们不能从先验/经验、分析/综合的模式来理解两人的基本思路。他们和以往提法的区别虽然相当细微,却事关宏旨。
维氏从生活形式和语言游戏来理解语言的规范作用,从有限性来论述“理解”,于是人们很快发现维氏是个“相对主义者”。历史的就是有限的,有限的就是相对的。取消了绝对标准,就只剩下一些相对的标准。然而,若没有绝对牢靠的基地,倘若我们真的追问下去,相对的标准就等于没有标准。好坏对错都是相对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归根到底”,也就无所谓好坏对错了。语言果然游戏乎?逻辑果然必然乎?
你说 “他强迫我戒酒”成话,我说“他力量我戒酒”就不成话。你告诉我说:我们是用两个词来表示“力量”和“强迫”的,而且一个是名词,一个是动词。你有绝对的根据吗?英语里不是用force这同一个词来表示这两个意思吗?而且它既可以用作名词又可以用作动词。可见用两个词来表示力量和强迫没有必然的逻辑根据。于是,“他力量我戒酒”就没说错;即使错了,不过是相对地错了?
人的认识没有绝对的根据。这话在说什么呢?是说人的认识无所谓对错或“归根到底”无所谓对错?维氏当然不承认,而且把反驳这种相对主义作为其哲学的一项基本任务。是说相对于上帝的全知,人的认识会犯错误?维氏不但承认人会出错,而且把这一点当作其哲学的基石之一。但不是相对于上帝的绝对正确而言。上帝怎么认识的,我们不知道。人出错,简简单单相对于正确的正当的人类认识。我们根据实际使用的语言所提供的规范来判断正误;否则还能根据什么呢?日常语言不是维氏的偏好,而是维氏哲学的奠基处。
历史通过什么把言说的理路传给我们?通过一代一代的言说。在维氏,语法是通过日常交往语言传给我们的。在海氏,存在之言是由思者和诗人承传下来的。在这里,海氏似乎与维氏分道扬镳。海氏从来不喜寻常。常人,常态,常识,都是海氏挖苦的材料。日常的种种话语,集合为gerede,列为此在沉沦三种基本样式之首。后来他又明确断称“日常语言是精华尽损的诗”。
说到这一区别,我们先须指出,“日常语言”这个用语往往是和不同概念相对待的。和日常语言相对的,可以是术语、科学用语、诗词、神喻、理想语言。维氏谈及日常语言,通常针对的是理想语言,逻辑斯蒂语言。在这一点上,海氏和维氏初无二致,只不过他只采用“自然语言”这个用语,不像维氏那样混用“日常语言”和“自然语言”。维氏认为自然语言要由自然史和人类的生活形式来说明,海氏认为自然语言是自然的涌现;维氏认为自然语言是其它符号系统的核心,海氏认为自然语言是语言的本质存在;海维二人都认为自然语言从原则上说是不可能形式化的,逻辑斯蒂语言是堕落而不是进步。另一方面,海氏有所贬抑的“日常语言”通常是和诗对称的。既然维氏不曾把两者对待论述,我们也说不上海维二人在这里有多少分歧。
此外,我还愿意说明,海氏之强调诗,并非出于浪漫主义的遐想,而是海氏从学理上特别强调基本言词的力量和语言的开启作用。
让我们从维氏的一个例子生发出一个新例子来。一种语言里没有“把石板搬过来”这样的结构,我们喊“把石板搬过来”,他们只能喊“石板”,那么他们的“石板”是否和我们的“把石板搬过来”相当呢?他们到我们这里找了份工作,听到“把石板搬过来”的时候,就会像在自己的国度里听到“石板”那样行动。在这个意义上,这两句话的意思是相当的。然而,这时师傅说:“是让你搬过来,不是让你推过来”;本地的学徒会改变搬运的方式,外来的学徒却不知所措了。在这个意义上,“石板”和“把石板搬过来”的意思又不相当。这其实是一个寻常问题。force和“力量”相当不相当?man desires to know by nature这句英文和“求知是人的天性”是不是相当?设想这句英文后面跟着but not woman。简单说,句子一方面和情境相联系,和句子的“用途”相联系,一方面和借以构成的词汇相联系。单就用途来说,词汇只是句子的材料,只要句子具有同样的用途,使用什么词汇都无所谓;材料消失在用途里。然而在诗里,诗句的意思和选用的词汇却密不可分。套用一句已经变得陈腐的话:艺术是形式和质料的完美结合。我们说,诗就是在翻译中失去的那一部分。什么失去了?用这些特定的语词表达这一特定的整体意义。每种语言都有独特的语词系统。表达“同样的意思”用的是不同的语汇,恰恰是不同语言的不同之处。那么,诗就在把语词结合起来表达意思的同时保持着语词本身的力量。在极端处,诗句的意义完全由其所包含的语词(及其特定联系)规定,而与怎样使用这句诗无关。在这个意义上,诗是“无用”的,不用来传达信息,不用来下命令或恳求。但这不是说诗不起作用。诗的作用在于造就规范,在于揭示语词的意义。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与制造器物不同,艺术作品不耗用材料,而是使材料本身的色彩和力量突显出来。艺术关心的不是有用,而是让存在者如其所是地显现自身。事物的本然面貌在诗中现象,也就是说,诗从存在的无声之音那里承接下本质的言词,从而才有语言的日常“使用”。那么,我们唯通过诗才学会适当地“使用”语言,用语言来表达思想,传达信息,下达命令。
尽管有这些差异,海维二人的基本趋向仍然是很接近的。日常语言突出了语言的承传,存在之言也是一样的,因为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始终是历史性的。存在者以何种方式显现,存在者怎么才是存在者怎么才不是存在者,不是一个先验问题,更不是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加以决定的。人被抛入其历史性的存在。
的确,尽管海维两人的教育背景思想渊源差别很大,两人的方法风格迥异,但深入他们的根本立论,我们可以感觉到一种共同的关切。我有时称之为对人类生存和认识的有限性的关切:如果逻各斯是历史的承传,我们还有没有绝对可靠的理解?如果意义要从情境加以说明,人生还有没有终极意义?上帝死了,怎么都行了?没有对错善恶之别了?若有,又该由谁由什么来作出最终裁判?一句话,祓除了绝对怎样不陷入“相对主义”呢?往大里说,这是我们时代最具普遍性的问题。宗教、道德、艺术、政治甚至科学,都面临相应的挑战。
然而,正如海德格尔最初就指出来的,不管喜欢不喜欢,有限性是现代人必须承担起来的天命。海氏强调存在的有限性、历史性,维氏强调生活形式、语言游戏的自然史。其实,只因为我们是有限的,才会出现意义问题,也只有从有限出发,才能解答意义问题。我们不再从绝对的出发点,用上帝的全知的眼睛来看待世界,而是用人的眼睛来看待世界。
--------------------------------------------------------------------------------
[1]这里是广义,相应于“艺术哲学”“道德哲学”之类。
[2] sz是指heidegger, 《sein und zeit》,tuebingen:niemeyer,1979,下同。
[3] pu是指wittgenstein, 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引自该书的只注明节数。下同。
[4] d.bolinger, 《aspects of language》, 1968,harcourt, p.2.
[5].wesen,或译“存在”。
[6].heidegger,der ursprung des kunstwerks,载于《holzwege》,全集版;frankfurt:klostermann,1950,ss.59-60.
[7].heidegger,《unterwegs zur sprache》, pfullingen:neske,1959,s.262.
[8].wittgenstein, blue and brown books, harper & row, new york,1965,p.172.
[9].heidegger,das wesen der sprache, 载于《unterwegs zur sprache》,s.176.
篇6
关 键 词:伊本图斐利;哈义本叶格赞;政治哲学;伊斯兰思想;思想史
《哈义本叶格赞》是阿拉伯哲学家伊本图斐利的著作。根据其生前记载,他的后半生几乎是在宫廷中度过的。他著书数卷,但能够流传下来的只有该著作,“其原因可能要归于他崇尚的思想。过去的年代里,持门户之见,暴虐迫害的群小们总是不遗余力地扼杀阿拉伯思想中追求光明,提倡科学研究和解放桎梏的一切精神产品(在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尤甚)。伊本图斐利的思想必属被消灭之列。因此我们仅耳闻许多早期阿拉伯优秀进步著作的书目,却无缘目睹。” [1]2图斐利的著作也许就是遭到了这样的厄运。
图斐利生活在宫廷的政治旋涡之中,根据他的政治经验,他已经洞察到政治的有限性,并试图以哲学的沉思活动来超越和克服政治的有限性,《哈义本叶格赞》这部著作恰恰表现了这一点。他在《哈义本叶格赞》中以隐微的方式向我们表达了这样一个主题: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他的最高成就是什么?——哲学。这不能不让人联想起18世纪另一部著作——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它倒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展现了现代人如何征服自然的图景。《哈义本叶格赞》的创作早于《鲁宾逊漂流记》。有专家认为,笛福在创作《鲁宾逊漂流记》时,曾受《哈义本叶格赞》的启发。[2]391若如此,那么笛福的著作仅仅是对《哈义本叶格赞》著作的摹仿,这种摹仿是以启蒙式的主体性原则颠覆了古典的自然理性原则。这同时也是一次大的哲学反叛行动,即科学对古典哲学、现代对古代的反叛行动。这次行动提出一个尖锐而深刻的问题,即古典哲学在面对现代科学生活世界时如何生存。科学对古典哲学的挑战,使古典哲学面临合法性与正当性危机。于是,当我们再回到《哈义本叶格赞》的文本,对其进行解读时会发现,尽管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是对《哈义本叶格赞》的形式摹仿,但从前者对后者的思想观念或者精神实质的颠覆来看,恰恰表明了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古今之争。
一
图斐利在《哈义本叶格赞》开篇为叶格赞的出身设立了谜局,没有直接说叶格赞是由谁所生,“赤道线有一个印度岛屿,那里的人是自生的,既不要父亲,也不要母亲。”[1]29这为“先知穆罕默德提到过真主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亚当”[1]36的话题做了铺垫。于是,就有人以此为依据,认定叶格赞就是那样出生的,这就形成对叶格赞出生的第一种说法。接下来图斐利笔锋一转,使用古典政治哲学家柏拉图惯用的讲故事的修辞手法,开始叙述叶格赞出生的第二种说法。一个大岛国的国王的妹妹与国王的亲戚两人相爱,却遭到国王的干涉而不能结婚,于是,两人按照当时惯例偷偷成亲,不久产下男婴,后来怕被别人发觉此事,他们就把孩子放在钉好的木箱,放进大海,海浪把木箱推向一个荒岛,箱子开裂,一只母羚羊发现了箱子内的婴儿,把他抚养长大。这形成了叶格赞出生的第二种说法。这两种说法构成了叶格赞的诞生论:第一种即叶格赞无父无母,诞生于自然,这种说法是依据自然法则的,这恰恰说明“自然是万祖之祖,万母之母”[3]92,图斐利阐明自然,是想阐明哲学的出现。沿着古典政治哲学的思想路径,“哲学由对祖传之物的诉求转向了对于某种比之祖传的更加古老的事物的诉求。……自然比之任何传统都更古久,因而它比任何传统都令人心生敬意。” [3]92因而哲学在根除权威之后,自然就是标准,自然意味着正确和正当的。第二种为约定说,认为依据约定法则,约定、祖传、权威是正当的,与此相反的是不合法的。因此,对万物最初事物(自然)追求的哲学,在政教合一的生活世界里的处境十分艰难。如果我们把叶格赞看成是哲学的意象,他的诞生就是对现有权威的挑战,同时政治与宗教却又成就了他,使他的哲学生活成为可能。如果没有政治与宗教的冲突,就不可能有叶格赞被放进钉好的木箱,放入大海,让海浪把木箱推向岛屿的情况,也不可能让叶格赞“从一种时代进入新的境况,最后达到‘完人’的境界”[1]34。图斐利之所以提到“完人的境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接受了阿拉伯政治哲学家法拉比的政治哲学观点。法拉比“取消了在德性城邦实施公开统治的哲学王,取而代之的是哲学家的一种隐秘的王者身份。这个哲学家,正是因其是一个‘探究者’,才成为一个‘完满之人’。他的私人身份乃是一个不完满社会的成员,对这个社会,他尝试着在可能的范围内加以人性化”[4]207。法拉比通过变通的修辞方式,为他同时代与以后的阿拉伯哲学家从事哲学活动赢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间。图斐利的完人恰恰是对法拉比“完满之人”的另一种政治哲学理念的表达。
政治哲学之所以在伊斯兰世界能够扎根,除了法拉比对古希腊柏拉图政治哲学的修正之外,也有其生存的肥沃的土壤资源。如果我们考量伊斯兰教的启示就会发现,首先伊斯兰教所关注的不是一个信条,也不是一条教义,而是一种社会秩序,使《古兰经》构成终极政治社会秩序的解释依据。然而,终极秩序的建立者则是先知立法者,它不仅是最高秩序的政治家,而是最高秩序的哲学家,这样,先知立法者被构想成为哲学王。哲学王不仅是亚里士多德统绪中的主题,而且是柏拉图政治学的主题。而“先知学因此是一种地道的政治哲学,且是柏拉图政治哲学。与此同时,正是得益于其先知学的视野,这些伊斯兰哲学家才能回头并看穿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其实就是先知学(Prophetology)”[5]248。当然,我们深知,伊斯兰语境中的先知哲学王是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哲学王的。正因为如此,我们不难理解图斐利为何对叶格赞的出生要做两种处理。
如果说哲学活动在古希腊雅典是一种公开的活动,这就意味着哲学就是政治哲学,那么,哲学在中世纪伊斯兰世界就是一种隐秘的私人活动,这使图斐利在处理哲学与宗教政治生活的关系时并未采取古希腊方式,而是以一种温和而保守的方式来解决。在古希腊的自然说和约定说之争中,哲人苏格拉底站在自然说立场上反驳普罗泰戈那等智者学派的约定说,从而为哲学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进行辩护。这个棘手的问题在图斐利这里就转化为哲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他既不能用哲学驳斥宗教,也不能用宗教驳斥哲学,因为在政治哲人施特劳斯看来,哲学与宗教谁也无法驳倒对方。图斐利深知这一点,为了能够继续维持伊斯兰教带给阿拉伯人的社会秩序,又能在不危害社会秩序的情况下,使人们通过智性活动获得更大幸福。他于是就提出双重真理观,“这是西部阿拉伯世界调合宗教和哲学倾向之端倪。” [6]373当图斐利在描写叶格赞一出生就被装入木箱,让海浪送到一个岛屿时,就已经暗示哲学应该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自由活动,而不应该变成“实践哲学”,哲学家也不该是革命的实践者和急先锋。因为哲学就其本性而言,它具有“癫狂性”,它是一种用真理取代意见的知性活动。同时,任何政治社会的存在都离不开道德与宗教信念,以及在这个基础上所制定的法律的维系,如果这些意见和信念被哲学所颠覆,就会导致社会秩序的紊乱,甚至社会的崩溃。身处政治活动中心的图斐利对此颇为熟知,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位哲学家,他能够比任何人更深刻地体验到哲学与宗教之间的激烈冲突。在伊斯兰世界,“哲学的合法性没有得到承认”,必须采用显白的教诲,它就像一层铠甲,哲学穿着铠甲出场既不伤害别人,也保存了自己,这是一种政治的考虑。图斐利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给《哈义本叶格赞》穿上铠甲,使这部著作广泛流传,并被译成德、法、英、俄等多国语言。可以说,这部著作不是简单的文学作品,而是可以与柏拉图的《理想国》相媲美的政治哲学作品。
二
《哈义本叶格赞》作为政治哲学文本,主要由九部分构成,其中有六节阐释自然生存的观点,这足以表明图斐利是倾向于自然论的,他将新柏拉图主义的流溢说揉进了他的自然生存论,认为特殊的发酵大泥团在领有了精气或元气,就会生出新生儿,而这元气“源源不断地、大量地从至高的真主那里溢流而出”[1]35。图斐利用伊斯兰教的真主取代了新柏拉图主义的“太一”,即万物从能动的真主那里溢出来。从表层上看,他的这种对万物和人的生成的解释是符合伊斯兰教义的,“真主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亚当。”当然,他的这种解释也是基于如下忧虑:“如今随着人的这个形象的强化,余者将日趋消失。人独树一帜,以它荣誉的光华烧尽前进道路上的企及者。”[1]36图斐利以显白的教诲教导人们,要坚信和遵奉伊斯兰教,否则这种政治社会秩序将会土崩瓦解,哲学将会随之而消失。他的忧虑潜在地隐含着对当时因教派之争所引起政治混乱的一种批判,正是由于那些所谓的教义学家(即政治家)才使政治社会处于一片混乱中,而政治哲学家则是“清明与温良”的,因为他知道如何教导人们,知道运用什么样的教诲,知道自己生存的根基是生活世界。政治社会是生活世界的主要构成部分,哲学的任务不是要颠覆政治社会,而是通过隐微的教诲来教导潜在的哲学家和立法者,依靠“机遇”成为真正的立法者和统治者,从而建立良好的政体,使人们过上美好的生活。图斐利以隐微的方式给少数哲学家提供了一种古希腊目的论宇宙观,这是一种智性思维的结果。在图斐利看来,哲学家通过智性思维活动同样可以获得真正的幸福。上帝(安拉)在图斐利的哲学语境之中类似柏拉图的上帝,是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上帝,这显然不能与《古兰经》中的真主相提并论。
在《哈义本叶格赞》中,图斐利以精妙的语言阐释叶格赞这个新的生命如何在新环境中生存。他写道:哈义本叶格赞依靠对外在世界的感觉、观察、学习,不仅使自己生存下来,而且学会了思考和保存自己的方式,如在羚羊生病时,他就开始思索与寻找羚羊生病的原因,是器官?是血块?都不是。于是,他模糊意识到是一种在身体中又不是在身体中的那个东西。又如对火的认识与思考,使他的模糊意识明晰化,火意象性地表明人的理性觉醒。在图斐利看来,当人的理性觉醒时,人会对宇宙、生命等现象及世界统一性做深入地思考。如叶格赞对感性世界的思考,当他与自然相处时,就对自然界的事物进行了经验性的分类。他既看到了事物的变化运动与静止,又看到事物的统一与多样,并根据这些现象,追寻发生者的缘由,当他认为“找不到一种不育新,不依赖的行为发生者的物体”[1]74 时,叶格赞就转向天体,最后他洞察到“整个天体中的星星轨道包括其中的一切物体都是个整体,彼此相联浑然一体”。[1]78那么整个世界是如何产生的呢?“如果世界在时间中产生,是从无到有,那结论必然是:若没有一个动力因的作用,世界决不可能自发的产生。”[1]80那么这个动力因是什么?是原动力,是独立于物体之外并脱离他们的力量,它是整个宇宙的创造者,它是没有时间性的。《古兰经》 指出:“当他造化任何事物的时候,他只是说声:‘有’,它就有了。”哈义本叶格赞认为这一切都是来自无限完美、超完美的被选择的原动力,这就是“……天地间微尘的事物不能远离他,比那更小和更大。”他是慷慨的、最仁慈的、是美好、光辉、能力、知识。“除他的本体外,万物都要毁灭”。叶格赞“热切地向往着这个创造者,他的心完全放弃了对被感知世界的思考,统统被上层的精神世界所吸引。”[1]87叶格赞正是这样“诉诸逻辑的方法,找到了事物本质和产生的原因。”[6]169
叶格赞通过摒弃天然障碍,达到全身归一、彻底湮灭和真正的结合,看到了最后的无形天体有一个脱离物质的精髓,“看到了那超越物质世界的天体的精髓和最高天体所有的一切超绝的完整、光明和美妙,这简直无法以言语文字和声音来表达,他看到了至尊的第一存在的精髓,感到无限幸福,极为欢乐和喜悦。” [1]119 “他也在自身的精髓以及与他同处一级的那些精髓中看到无限的美妙、光明和幸福。那是眼未曾见过、耳未曾听过、从未进入人类中心,只有达到大乘,进入自我意识的人才能描述,才能理解。”[1]121而“每一个精髓都具有眼不曾见过、耳不曾听到、人类的心不曾想过的、沐浴着整个形成和衰退世界的美妙、光明、幸福和欢乐。”[1]120图斐利假借哈义之口来表达自己的苏菲主义思想,他说“苏菲派元老及其教长吉尼德临死时对他的门徒说:‘这是感觉到真主存在的时间,不要放过!真主至尊!’——受戒祈祷吧!”[1]93图斐利试图采用这种方式,将希腊的科学和东方的智慧融会贯通,以便创立一种关于世界的新学说。他意识到现代哲人欲借内外感觉来认识世界,其结果使人沉迷于对物质的追求,导致罪恶的产生。他认为,能够拯救人类堕落之路应该是一条永远纯洁的、精神的道路。
图斐利构造了哲人下降到洞穴的图景,他让自己的哲人叶格赞结识了来岛上修行的艾萨里,当叶格赞了解到艾萨里原来所住岛上的情况时,犹如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走下高山一样,决心到世俗生活世界中去,“到世间去,为他们阐明真知” [1]137,但当两人来到艾萨里原来居住的岛上,并给人们讲解哈义本叶格赞所领悟的真理时,人们并不愿意接受它。事实表明,民众无法认识抽象的真理,只能以可感的比喻给他们以启发和揭示。看到此种情形,俩人重返小岛,“在岛上崇拜真主,直到死神降临。” 图斐利以此暗示哲学下降到洞穴,哲学是无法被人们所接受的。在伊斯兰世界里,难道哲学只在于成就哲学家成为“完人”吗?
三
图斐利最后写道:“我们没有将菲薄的书页中的秘密全部点破,只留下了一层薄薄的轻纱。在可以了解其真谛的人面前,这层薄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被撕开,但对那些无能者,它确实如此粗厚沉重,无法穿透。”[1]145这恰恰说明了《哈义本叶格赞》不仅是写给民众看的,也是写给少数哲学家看的,它需要人们精心研究,悉心体察图斐利的写作意图。图斐利以隐晦的表达方式,让少数哲学家明白,他是使用了显白教诲与隐微教诲的写作手法,暗示学者在研习他的著作时不要被文本浅层表面的东西所蒙蔽,而要力图体悟他的最终意图,以作者理解自己的方式来理解作者的思想。文本中有这样一段话,它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他之所以用这种写作手法的初衷,“各派囿于眼前所得而沾沾自喜,各派都喜欢所奉的学派。他们把各自的神作为自己的爱好,把所崇拜的是为自己的意欲。他们不顾生命为捡拾俗卉的浮华尊贵,贪恋富庶,直至走游坟地。一切训诫对他们都无能为力,任何山岩也无法打动他们的心,争辩只能增加他们的固执任性,聪慧睿智对他们是无缘的,因为它们已经淹没在愚昧的大海中。他们企求并得到的已像锈斑一样蒙蔽了他们的心 。(真主已封闭他们的心和耳,他们的眼上有翳膜,他们将受重大的刑罚)。”[1]140图斐利指出:“我们违背了优秀的先辈们所使用的,尽量保存不多披露的方法。当代佯称时代哲学的荒谬的见解,促使我们揭示奥秘,扯去面纱的工作易于进行,其原因则是当代散布的那些佯称时代哲学的荒谬的陈腐的见解。这些错误观点传至世界各地,犹如瘟疫危害甚烈。因此,我们十分担心那些意志薄弱者,他们拒绝先知们的权力,一心效仿愚者的言行,把那些无知妄说看成是真知灼见。结果愈发喜爱、贪恋。我们深感必将这秘密的一个侧面展现在他们面前,把他们引向探求真知的坦途,以免重蹈覆辙。”[1]144可见,图斐利对民众有深刻的洞察,从他的话语中隐微地表达出,民众勿需启蒙,因为政治社会需要政治神学,需要统治,从而保证社会秩序有效运行。如果说哲学在希腊雅典是一种公开的活动,即哲学就是政治哲学,那么哲学在中世纪伊斯兰世界就是一种隐秘的私人活动,而这种私人的哲学活动恰恰不仅使哲学家得到保护,而且使他的哲学活动空间的自由度扩大。在哲学与律法(教义)的关系上,哲学家的隐退缓和了二者之间的冲突,但是哲学并未丧失。
如果柏拉图的《理想国》谈到人在走出洞穴之后就能获得真理,那么图斐利认为并非如此,因为当人走出洞穴,在适应了外界之后,要靠自己的理性直观和体验。其实,当人走出洞穴时,他就已走向前科学和前现代,他面对的是一个真实的、真正的生活世界。当他这时回忆洞穴里所接受的认识或知识时,觉得它们是那么的荒谬。为了获得真正的知识,认识就得必须重新开始,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真正的真理。如果《理想国》的洞穴说是教导哲人走出洞穴,那么《哈义本叶格赞》是解决哲人走出洞穴之后该怎么办的问题。《哈义本叶格赞》讲述了哲人在走出洞穴之后,在他真正认识了世界与宇宙之后,才能认识真正的真理,才不会走向独断与怀疑,才能克服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所导致的片面性。如果哲人从洞穴之外回到洞穴里,这对于生活在洞穴的人们来说是致命的,苏格拉底的悲剧就是哲人的结局。《哈义本叶格赞》的哲人深知在何时才能运用哲学,深知哲学具有“颠覆性”的特点,所以哲人要把握好哲学实践的机运和情势。在哲人下到洞穴后,发现哲学与律法(教义)冲突时,不是用哲学去触动律法(显然这不同于现代启蒙哲学,不会将哲学变为意识形态,比如今天的“主义”之类的)。因为“哲学,尤其政治哲学一旦屈从于权威,就失去了它的本色;它就会蜕变为意识形态,亦即为某一特定的或将要出现的社会秩序所做的辩护词;或者,它就会变为神学或法学” [3]93。而哲学家主动隐退,恰恰构成城邦运行良好的必要条件,从而使哲学与律法取得了和解。哲学家的主动是基于政治的思考,图斐利对哲学进行这种政治思考就成为此文本的主题。
在文本中,图斐利所展现的问题,在后人们那里被逐一地证实:第一,人所观察到的,心里所想的无法用语言说清楚,“用文字判断绝不像用心来表达。”[1]114于是,德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对可以说的说清楚,对不可说的保持沉默”[8]105;第二,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不能认识任何事情。德国哲学家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充分论证了理性的限度,提出知识要为信仰保留地盘;第三,人勿需启蒙,意味着人必须遵从自然,否则就会破坏自然秩序,建立在自然基础上的社会秩序也会随之崩塌。18世纪启蒙运动与现代哲学证实了这一点。启蒙运动兴起之后,法国进行了实施启蒙思想的伟大革命,革命的失败给人们以沉重的打击,并加速了西方理性主义的现代性危机,使许多哲人为之震惊。为克服危机,许多哲人都相应地回到古希腊提取资源,而美国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独辟蹊径,从伊斯兰哲学家入手 ,对伊斯兰哲学家的著作进行了重新诠释,使中世纪阿拉伯哲学家的思想重见光明。就这样,伊斯兰哲学开始在西方引起人们的重新重视与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 伊本图斐利.哈义本叶格赞的故事[M].王复, 陆孝修,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2] 蔡德贵.阿拉伯哲学史[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
[3] 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M].彭刚, 译. 北京:三联书店,2003.
[4] 列奥施特劳斯.写作与迫害的技艺//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5] 林国华.在不幸中骗人//启示与理性[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6] 西德基.伊本图斐利//蔡德贵. 东方著名哲学家评传[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
篇7
关键词:教父学;柏拉图;希腊的摩西;一神教
中图分类号:B13; B9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5)01000106
教父智识非凡,护教不懈,全力抹煞基督教受惠于希腊哲学之事实。反基督教者迫使教父应诉:为何基督教从希腊哲人(尤其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借取大量信条?然而,尽管教父答辩异教,但就文献而言,其答辩内容却大不相同。其中,既有人视希腊哲学为基督教的死敌,也有人视希腊哲人为基督教的先驱。
教父作品中的希腊哲学
在公元二、三世纪,作为基督教护教家,塔提安(Tatian)和德尔图良(Tertullian)强烈呼吁人们远离哲学。《塔提安致希腊人》(Address of Tatian to the Greeks)恶意攻击希腊思想制度,如下控诉在书中比比皆是:希腊哲学家毫无原创,只会窃取异族的思想,应为所有邪恶错误负责,其荒谬无能,更举世闻名。塔提安反对希腊哲学,几近宗教狂热,但这不是《致希腊人》(Address)的主要目的。他主要想证明基督教哲学比希腊体系更为久远。塔提安认为摩西是最古老的诗人兼史学家,并褫夺荷马所有异族智慧创立者的头衔。
德尔图良之护教,同样从全然拒斥异教哲学开始。然而,与塔提安不同,德尔图良谙熟希腊哲学信条,也通晓希腊基本制度。如此,他的体系便更为可信。他拒绝理性主义,怀疑一切形而上学证据,这让他自己在感知之非理性阶段接受基督福音。因此,他声称:“Credo quia absurdum〔信仰恰因荒谬〕”。
尽管承认某些柏拉图主义公式正确,德尔图良依旧认为一切异端均源于异教哲学 On Prescription Against Heretics〔《论反异端的策略》〕, VII, ANF, III, 246.。
既然如此,那么在基督徒和哲学家之间,在希腊门徒和天堂门徒之间,在求名逐利者和追求生命者之间,在清谈家和行动者之间,在建造者和拆毁者之间,在谬误之友和谬误之敌之间……,其中又有哪点相似呢?Apology〔《护教辞》〕, XLVI, ANF, III, 51.
德尔图良强调:在福音研究之外,任何探究都徒劳无益。似乎,他绝不接受任何犹太―基督教哲学作为教会神学基础:要理解基督教信仰,不能通过希腊智慧,而只能依靠非希腊化的旧约背景。在这雄辩、激情四溢、但却难以服人的名段中,他吁求福音免被异教智慧所玷污。
雅典和耶路撒冷到底有什么相干?学园和教堂间能有什么协同?异教徒和基督徒又有什么关系?……别再制造混杂着斯多亚、柏拉图和辩证法的基督教了!在拥有耶稣基督之后,我们无需好奇争辩;在安享福音之后,我们再无需任何探究!On Prescription Against Heretics〔《论反异端的策略》〕, VII, ANF, III, 246.
很早就有人想调和基督教和柏拉图主义,如殉教者查士丁(Justin Martyr)。但凡柏拉图著作,只要他能找得到,他皆精通无碍。况且,在其改宗前,他自己就是个柏拉图主义者。他能审慎地估量:在柏拉图的信条中,哪些能增进基督教体系,又有哪些却与之对立。
查士丁通过“逻各斯”(Logos)定义原则,以统一希腊人和异邦人(基督徒)。
那是因为,不仅在希腊人中,“理(Reason)”(“逻各斯”)成功通过苏格拉底去谴责他们;而且在野蛮人中,“理”(或“言”,“逻各斯”)k自己――取了人形,变成了人,被称为耶稣基督――同样对他们施以天谴First Apology〔《第一护教辞》〕, V, ANF, I, 164.。
查士丁言论出格,甚至将苏格拉底与耶稣相提并论,并认为苏格拉底通过“逻各斯”而多少认识耶稣Second Apology〔《第二护教辞》〕, X, ANF, I, 191.。然而,基督降临划定了界限:在界限内,我们可将柏拉图及苏格拉底视为预示者,他们大略预示“逻各斯”将于人间“复临”(parousia)。
……因为,事实上,哲学就是最多地占有天主,以及在主前无上的荣耀。哲学把我们引向天主,并独自将我们托付给天主……对无形之物的感受征服了我,对“相(ideas)”的沉思让我的思想展翅高翔。我曾愚不可言,刹那间,我便耳聪目明。我期望立刻仰望天主,因为那就是柏拉图哲学的尽头Dialogue With Trypho〔《与特黎丰的对话》〕, II, ANF, 195.。
俄利根(Origen)、亚历山大的克莱门(Clement of Alexandria)、潘代诺(Pantaenus)和亚历山大教义问答学校(Alexandrian catechetical school)在智识灵修两方面给予柏拉图主义与新约作者相等的地位。他们崇敬希腊大师,并借此获得灵感。克莱门大量引用柏拉图著作,尤其是《理想国》、《法律篇》和《斐多篇》,所占篇幅往往超过对新约的引用。与新约著作信徒一样,柏拉图的门徒热情传播柏拉图的“相”William Temple: Plato and Christianity, Three Lectures (London: Macmillan, 1916), p. 93. 〔《柏拉图和基督教――三次讲座》,伦敦:麦克米兰,1916,第93页。〕作者指出:“亚历山大的柏拉图主义位于圣亚他那修全部神学的背后,并提供了在尼西亚信条及伟大正统教义中被逐步提出的语言。”。俄利根是其中典型,就教会接受柏拉图的程度,他要么被认为是基督教英雄,要么被认为是持异端者。
就正义及宗教而言,克莱门建议将哲学视为希腊人的神圣启示,哲学使希腊人活在正义中并保持高度虔诚。因此,哲学是赠与希腊人的圣礼,其作用如教师将启蒙的希腊人带向基督,正像犹太律法的作用是指示将要来临的弥赛亚Stromata〔《杂缀集》〕, I, V, ANF, II, 305; I, VII, ANF, II, 308; VI, XVII, ANF, II, 517 f.. 。无论如何,人们必须明辨哲学,或者是天堂的礼物,或者是误导腐化的力量。克莱门的选择其实很简单:真实可信的哲学就是通过柏拉图讲出的苏格拉底 同上, I, XIX, ANF, II, 321.。
克莱门及其有趣,他让保禄称希腊著作明智地预言、精确地描述了神子同上, IV, V, ANF, II, 490.。此外,他将福音视为希腊犹太两大古代文明的交汇点,而不是两者间根本的转折点Charles Bigg: The Christian Platonists of Alexandria (Oxford: Oxford Univ. Pres, 1886) p. 47.〔《亚历山大城的基督教柏拉图主义者》,牛津: 牛津大学出版社,1886,第47页。〕作者支持此观点,但将古代文明视为偶像崇拜之路。。
因为俄利根哲学,尤其是其中关于柏拉图的部分,成了基督教最强大的盟友;况且,俄利根以一己之力,为教会提供武器装备,以反击教会外(尤其是瑟尔苏 Against Celsus〔《驳瑟尔苏》〕, ANF, IV, 395-669.)的无情攻击,所以俄利根无愧于基督教第一神学家。在他的帮助下,基督教信仰本可以安居于坚实的神学地基。然而,这种柏拉图主义的地基难免使教会陷入哲学的迷惑。俄利根本人认为基督教绝不是被曲解的柏拉图主义同上, V, LXV; VI, I-XX, ANF, IV, 571-582. 。所有真正的柏拉图主义者都能接受三位一体中的两个位格(圣父和圣子),但他们却不能接受圣灵,而后者才能鲜明地体现基督教的特点 De Principiis〔《论原理》〕, I, III, ANF, IV, 251-256.。
教会对俄利根的柏拉图主义抱有敌意,这导致他在第二次君士坦丁堡会议上被谴责。随后,人们便遗忘了他。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伊拉斯谟坚持为其恢复名誉。他写下这句名言:“俄利根开启了神学的泉源。”
在迦帕多加教父(Cappadocians)的影响下,教会获得了基督教文明的视野。圣巴西流(Saint Basil)历史性的文集《就如何阅读希腊文学致年轻人》(Address to Young Men on Reading Greek Literature)业已成为西方文学经典Werner Jaeger称之为所有基督教教育的。。
奥古斯丁对持柏拉图主义的教父圈子并不陌生,尽管在他的时代,柏拉图主义已不自觉地与新柏拉图主义相混同。人们指责奥古斯丁,因他将新柏拉图主义并入基督教的信条。
关于柏拉图在基督教的影响,集中见于《天主之城》(The City of God)第八章及第十章。在那里,柏拉图被当成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比许多神还要优越。奥古斯丁的任务是:既要证明柏拉图之伟大,又要声明他卑于先知及使徒The City of God〔《天主之城》〕, II, 15, NPNF, II, 30 f..。
尽管有些不情愿,奥古斯丁依然认为柏拉图体系受惠于基督教。不过,他礼赞柏拉图,因为柏拉图结合沉思与行动,而使哲学臻于完美同上, VIII, 6, NPNF, II, 148 f..。当谈到柏拉图主义者时,他总结道:“我们偏爱他们而不是其他人,并承认他们与我们最接近。” 同上, VIII, 9, NPNF, II, 150.。
尽管如此,奥古斯丁仍然要承担艰巨的任务:去调和柏拉图哲学技艺与保禄反哲学的警告歌2: 8。 对他而言,这警告不适用于柏拉图主义哲学家――对他们来说,不能仅从字面上去理解保禄的话,因为他们协助以形成背景,正是在此背景下,保禄才能够进行哲学沉思――这点体现在罗马书1:19-23和宗徒大事录17:28奥古斯丁并没有象克莱门一样出格,后者声称保禄鼓励使用哲学。Stromata〔《杂缀集》〕, VI, VIII, ANF, II, 494-496.中。当然,问题在于:让柏拉图赞同保禄,反之亦然。
这便是我们偏爱他们的原因。因为当其他哲学家绞尽脑汁、竭尽全力,以寻求事物原因、正确的学习生活模式时,他们凭借知晓天主,业已发现构建宇宙之原因,业已发现揭示真理之光芒,业已发现涌现幸福之泉源。所有的哲学家,只要他们拥有这些天主的思想,无论他们是不是柏拉图主义者,他们都将认同我们The City of God〔《天主之城》〕, VII, 10, NPNF, II, 151.。
奥古斯丁在处理柏拉图体系、普罗提诺(Plotinus)体系及波菲利(Porphyry)体系时遇到了困难。这些困难尤其体现在《天主之城》第十章中,这辜负了他对柏拉图主义及新柏拉图主义心照不宣的认可:因为这些思想拥有对天主的宗教洞见,所以不能弃之如敝履。奥古斯丁努力证明:当作为基督教神学潜在对手的时候,柏拉图主义哲学将不能像基督所揭示的那样导向对天主的崇拜。
一神教的普世化
保禄绝不承认:基督教能从任何其他的历史或精神进步中,获取比基督死亡复活还大的恩惠。保禄让人相信能够建立一种神学体系,一种与浩如烟海的知识储备无关的神学体系。而这些浩如烟海的、被公开或私下认可的知识储备,却构成了公元一世纪地中海世界的智识基础及社交基础。这观点却无法在某些教父面前得到令人满意的论证,而这些教父的任务便是在旧约的预言和希腊哲学的见识之间寻找交汇点。许多护教家都不得不承认:基督教根植于基督的巴勒斯坦门徒所传达的悠久犹太传统,但如果这些传统没被翻译成希腊哲学中更为普世化的公式,基督教将不能被传到世界各地。如果我们不想用强力把智识和精神全部摧毁,我们就不能全然拒绝柏拉图体系,以及某种程度上的斯多亚体系。看来,我们最好接受这样的真理――如同奥古斯丁曾被迫接受的那样――天主的恩典普降人间,并通过柏拉图的著作得以表现。虽然柏拉图尚无天主的客观知识Lectures or tractates 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John〔《根据圣若望的福音讲座或论文》〕, II, 4, NPNF, VII, 14.,但是将柏拉图视为天主恩典的工具,却能使他成为基督教的先驱。柏拉图主义在基督教中发现自身之完满,这想法曾被基督教护教作品激烈地抵制,尽管这些作品通常也承认:哲学家最根本的教义通过四海同一的逻各斯――之后在耶稣基督身上道成肉身――的内在工作(inworking)而得以展现。
正是在非犹太教的世界中,基督教神学才得以成形。尽管天主的启示是唯一的,但柏拉图主义及斯多亚主义的信条又渗入了基督徒的生命,这给早期教会带来了双重处境。尽管人们承认基督事件是唯一的,形成基督教神学却需要某些比单纯的犹太教信仰更复杂且更有力的元素。基督教需要哲学之形式,基督教神学源于这些最初让基督教陌生的思想。
教父希望通过调和希腊哲学和旧约信仰以使基督教普世化,他们的努力让新约写作提前:这在亚历山大的斐洛(Philo of Alexandria)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此人作品中,柏拉图主义是如此地根深蒂固,以致我们常有这种印象:他将柏拉图视为希腊的摩西。事实上,圣灵启示的核心观念就是将逻各斯的普世分享延伸到为逻各斯而生的柏拉图身上。
教父统一犹太律法和希腊哲学的通常进路就是:强调柏拉图对旧约先知――尤其是对摩西――的依赖。
又有哪位诗人和哲人未尝畅饮过先知的泉水呢?哲学家用那泉水灌溉他们贫瘠的思想,因此,这便是他们从我们这儿获取的东西,这让他们能和我们相提并论 Tertullian, Apology〔德尔图良:《护教辞》〕, XLVII, ANF, III, 51 f..。
对某些基督教护教者而言,特别是对米兰的安布罗斯(Ambrose of Milan),最有诱惑力的想法是:根据不太可信的记载,可能在公元前([译注]原文漏“前”字,兹补上)六世纪末,在巴比伦入侵之后,耶肋米亚(Jeremiah)离开巴勒斯坦去埃及避难,而柏拉图也正好在那个时候游历了埃及。全然不顾此说法中明显的历史年代错误,他们又进一步说,柏拉图根据他从耶肋米亚那里听来的东西形成了自己的哲学。奥古斯丁试图更正此观点引发的误解。尽管有时他似乎也接受了柏拉图和耶肋米亚在埃及会面的传统说法On Christian Doctrine〔《论基督教教义》〕, II, 28 (43), NPNF, II, 549. 然而在奥古斯丁的 Retractations〔《更正》〕 ( II, 4) 中,他试图更正此错误。 ,但在其他的场合,他认为耶肋米亚没有直接影响柏拉图,他还认为,柏拉图不可能读过希伯来经文。
然而,通过仔细计算编年史记载的日期,我们发现柏拉图的出生日期比耶肋米亚作预言时晚了一百年……因此,在柏拉图游历的时候,他既不可能见过早已去世的耶肋米亚,也不可能读过那些还没被翻译成希腊语的经文,毕竟他只精通希腊语。当然,除非我们说,因为柏拉图强烈追求知识,他已通过某个译者研读过这些作品The City of God〔《天主之城》〕, VIII, II, NPNF, II, 151. 奥古斯丁此处的年代表仍然颇多错讹。在耶肋米亚去世和柏拉图所谓的埃及之行之间大约间隔两百年。。
在将一神教普世化的努力中,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步骤便是:结合犹太教创立者摩西和首位希腊理性宗教权威柏拉图。按克莱门和查士丁的说法,柏拉图分享同一天主分配给所有献身智识者的、普世化的圣灵启示。正是那同一个逻各斯在所有的哲学家体内运作。
伟哉柏拉图!汝业已手触真谛。切勿懈怠。与我一同探究至善。盖神圣之流射居汝体内浇灌,万众于此概莫能外,而于献身智识者尤甚矣Clement, Exhortation to the Heathen〔克莱门:《劝勉异教徒》〕, VI, ANF, II, 191.。
每个善言之士均相应地分享那充满生命力的圣言,因两者息息相关……所有的作者,在其体内圣言的播种下,均能在黑暗中参透事实Justin, Second Apology〔查士丁:《第二护教辞》〕, XII, ANF, I, 193.。
就柏拉图与摩西的关系,早期护教家展现了一副由不同立场所构成的光谱:从纯粹的赞美到剽窃的控诉。其中,查士丁就大费笔墨以控诉柏拉图剽窃摩西。――这颇有几分出人意料,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这与其普世化的逻各斯概念相矛盾,这同样与其对希腊哲学积极接近的总体态度相矛盾。在其《劝勉希腊人》(Hortatory Address to the Greeks)中,查士丁努力说明,让人作呕:当柏拉图在埃及时,他从摩西的传统中拷贝了哲学模板,并以此模板为基础构建了他的全部思想观念。然而,在柏拉图的著作中充满了他所受惠的诗人和哲人――这名单可列一长串;可在他的著作中,摩西的名字却无处可寻。查士丁当然明白这点,他解释说,柏拉图之所以绝口不提摩西,是因为他处于苏格拉底敢于介绍新的神圣观念而遭厄运的环境中。
虽然当柏拉图在埃及研学时,他很可能接受了摩西及其他先知关于唯一神论的信条,但因忌惮苏格拉底的厄运,……所以他在谈论神o时,就创造了一套繁复且模棱两可的话语Hortatory Address to the Greeks〔《劝勉希腊人》〕, XX, ANF, I, 281. (See also XXII, XXV, XXVI, XXXI .... ). 关于柏拉图剽窃希伯来人的说法亦可见Clement, Stromata〔克莱门:《杂缀集》〕V, XIV ff., ANF, II, 465-476.。
在查士丁《与特黎丰的对话》(Dialogue with Trypho)中,我们更容易理解他的立场,那本书的论证很自然地导向如下辩护:众先知是真理的唯一仓库。他还笨拙地谈到:应认为基督是所有先知的完满状态。因此,柏拉图就拉达曼迪斯(Rhadamantus)和米诺斯(Minos)的神话故事而对末日审判所做的思考,同样应被认为是因他偷师基督而得到的First Apology〔《第一护教辞》〕, V III, ANF, I, 165. 查士丁夸大其词,令人震惊。他主张哲学家从先知那里借取了灵魂不朽的概念,(同上, XLIV, 177). 而在柏拉图哲学中,有个元素是先知完全不知道的:灵魂不朽。同样让人奇怪的是,查士丁相信柏拉图拥有从摩西那里借取的十字架教条。(同上, LX, 183).。
优西比乌(Eusebius)颇为犹豫地想去证明柏拉图哲学的根本基础――现象王国和本相王国(the realm of the ideal)的二元论――也来自摩西和希伯来先知。
对无形无状、唯有用思维方能看见的事物,柏拉图同样遵照全知的摩西和希伯来先知的教导和沉思,(1)无论那是来自他听到的传闻……或者(2)来自他意外发现的事物真正本质,或者(3)无论如何,我们都认为那是无愧于来自天主的知识Praeparatio Evangelica〔《福音之准备》〕, XI, 8, 引自H.A. Wolfson, Philo: Foundations of Religious Philosophy in Judaism, Christianity, and Islam (Boston: Harvard Univ. Press, 1948), vol. 1, p. 161.〔沃尔夫松:《斐洛: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宗教哲学基础》,波士顿:哈佛大学出版社,1948,第1卷,第161页。〕。
要让人相信柏拉图主义和圣经神学结为一体,这种普世化思想自然需要实例。这些实例应强调三方面的共识:创世,一神论和普世之律法。这三方面均为教父学所关注。
《蒂迈欧篇》――柏拉图流传最广的著作――常被人拿来和圣经的创世故事相比较,在斐洛时代后更是如此。在查士丁著作中,有两大部分强调了《蒂迈欧篇》的摩西背景,以及圣经与柏拉图宇宙起源学并行不悖。虽然奥古斯丁没太强调柏拉图的宇宙起源学,但是他依然得出如下的结论:对《蒂迈欧篇》的研究说明柏拉图了解摩西的神圣作品The City of God〔《天主之城》〕, VIII, 11, NPNF, II, 152.。
在护教作品中,柏拉图从摩西那里接受了一神教的洞见,这说法或被默认或被公开表达。尽管教父并不愿得出这种结论:摩西的传统――在这一特定的神学领域――足够有力地影响了柏拉图,以致于改变了希腊宗教的方向。虽然柏拉图开拓了一神教的新领地,但是他也给予多神教同样的支持。看来,我们很难认同查士丁所说的:柏拉图传授“仅有一个神的教条” Hortatory Address to the Greeks〔《劝勉希腊人》〕, XXII, ANF, I, 282.。
克莱门强调柏拉图在制定律法时模仿摩西。既然摩西的立法不可超越,摩西的律法就成为所有伦理的泉源,正是从这泉源,希腊人导出了自己的伦理Stromata〔《杂缀集》〕, I, XXV, ANF, II, 338; II, XVIII, ANF, II, 364-369.。
哦柏拉图!何处寻觅汝赠与之真理?……盖律法与真理并行,亦与汝对天主之情感相契,汝实受恩惠于希伯来人Hortatory Address to the Greeks〔《劝勉希腊人》〕, VI, ANF, II, 191 f..。
因此,一神教的普世化建构在大量臆测之上,即使这些臆测礼赞柏拉图并授予他仅次于摩西及其他先知的二号角色。从基督教护教家的角度来看,只能在证明柏拉图卑于摩西的基础上,方可仰慕柏拉图。作为亚威宗教的潜在对手,仅在那种情况下,他才能接受基督教作家的礼赞。因此,为了所有现实的目的,只有在付出让历史上的柏拉图变形为犹太哲学门徒的代价后,圣灵启示的普世化和逻各斯的内在工作才能够得以进行下去Clement, The Instructor〔克莱门:《导师》〕, II, 1, ANF, II, 242; II, X, 263;Stromata〔《杂缀集》〕, I, XV ff. ANF, II, 142; 263; 316.。 在毕达哥拉斯主义者努墨尼W斯(Numenius)的格言中,让柏拉图从属于摩西的进程达到了顶峰:“柏拉图何许人也?岂非操阿提卡希腊语之摩西?”Clement, Stromata〔克莱门:《杂缀集》〕, I, XXII, ANF, II, 334 ff.
柏拉图主义哲学是一神教在普世化进程中强大的盟友。与此同时,教父在作品中声色俱厉地警告,以确保柏拉图恰当地隶属于新兴的基督宗教。克莱门尤其珍视保禄的位置:正是保禄摧毁敌意之墙进而统一信仰。正是因为他的努力,犹太与希腊才合为一体并共享拯救之赠礼。让柏拉图赞同基督教神学乃是护教家的唯一道路,他们无法认同排除柏拉图主义哲学有力宗教信条的普世化的一神教。然而,耶稣自己也有可能受教于柏拉图作品,但这观念却被教父彻底地拒绝了 Augustine, On Christian Doctrine〔奥古斯丁:《论基督教教义》〕, II, 28, 43, NPNF, II, 549; Letter〔《书信》〕XXXI, 8, NPNF, I, 260. 我们无法知道哪些柏拉图崇拜者断言耶稣曾师从柏拉图。安布罗斯讨论此问题的书籍业已佚失。。
参考文献:
[1]Alexander Roberts,James Donaldson.The Ante-Nicene Fathers[C].Grand Rapids:Eerdmans,1906.
[2]Philip Schaff. A Select Library of the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C].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56.
[3]William Temple. Plato and Christianity, Three Lectures [M].London: Macmillan, 1916:93.
篇8
西洋的学术进来,不同的学科遭遇了不同的命运。声、光、化、电等自然学科具有太强的实用性,而这些领域中国原本就是空白,接受起来比较容易;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也需要跟人家接轨,硬着头皮也得引进。
然而,人文学科则不同,西洋有文史哲,我们有经史子集。中国传统的史学、经学、考据和训诂,谁也不能说它不是学问。讲西洋的历史或者哲学,中国的学者也许不行,但讲中国的,多少还是有些自信的。
北京大学,在长校之前,中国的学界基本上是老派学者的天下。哲学系讲中国哲学史,要从三皇五帝、三坟五典开始,讲一年,才到商朝的《洪范》,孔夫子什么的连影子都还没见着。今天我们知道,在甲骨文之前的中国典籍,其实并不可靠,大多为后人伪托的。但是,当年的老派学者,却不能不这么讲。不讲足中华五千年,政治上就不正确。
先生回国之后,如果讲西洋哲学史,毫无问题,谁也不会说什么。但是,他偏要讲中国哲学史,一上手就是老子、孔子,而只把此前的诗、经,作为中国哲学的胚胎。讲到荀子,也就结束了。这样的讲法,在今天司空见惯(实际上所有中哲史学者,都是的余绪),但在当年,却让老派的学者受不了。学生也大吃一惊,用顾颉刚的话来说,就是“惊得挢舌不能下”,即张口结舌。
同样也讲中国哲学史的陈伯|老先生,听说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摇头晃脑地连说不通,说是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大纲,哪里有大纲之上还有大纲的道理?而瞠目结舌的学生们,受到了震动,臧否不一。最终还是由于学问最大的傅斯年,在认真听了的课之后,做了肯定的评价,大家最后才认账。傅斯年的评价是:虽然没有陈伯|有学问,但路子是对的。我想,学生跟老先生不一样,英文不错,多少看过一些西洋人写的东西。
其实,正如唐德刚的考证,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底子就是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的博士论文。但是,这个论文在答辩的时候,是“大修通过”的,所谓“大修通过”,近乎枪毙。
所以,离开美国的时候,并没有拿到博士学位。这个在美国差点被枪毙的论文(按唐德刚的说法,当时参与答辩的美国教授,其实并没有人懂中国的学问),到了中国,却大受欢迎。等于开创了用西方的学术形式(还谈不上方法)研究中国学问的先河。
从那以后,一干中国学人也就跟上了。所以,十年之后,爆得大名的的论文,也就无需“大修”,直接通过了。“博士”被叫了十年,才真正戴上了博士帽。
当然,这么一来,这个开先河的著作,也无需完成下半部了,因为后人跟上之后,做得比还好。后来,又写了若干半部书,都是开了先河,然后下面就没了,也无需有了。
西方人做学术,形式上讲究有体系。的大作,作为提交给老外的博士论文,当然符合这一要求。但是,中国人做学问,讲究书读得多,腹笥宽,肚子里的料要多。人家读过的,你没读过,或者读过了没记住,就不配跟人谈学问。不仅如此,学界还特别重传统,讲究家学。至于文章写出来是什么样子,大家并不计较。这个习惯,显然不那么容易被改变。所以,单单学生认账还不行,还需要学界认可。
篇9
一、哲学———关于理性的学说
哲学起源于古希腊。它是在东方、巴比伦、埃及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按照德国现代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考证和说法,古希腊早期思想家赫拉特里克最早使用“爱智慧”一词并用它来描述对于真理、智慧的追求。按现今可见的古代史料,第一个对哲学有明确自觉的哲学家大概是毕达哥拉斯。根据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记叙:“第一个使用哲学这个术语并称自己为哲学家或智慧爱好者的是毕达哥拉斯因为他总说除神之外没有人是智慧的。”被誉为近代哲学之父的笛卡尔认为“认真进行哲学思考,首先就要撇开偏见,细心怀疑我们之前所承认的意见知道重新考察之后发现他是真的,才能同意它们。”黑格尔在肯定和赞赏柏拉图关于哲学以把握普遍性概念理念为自己的任务时说“:认识理念就是哲学的目的和任务。”即使在经院哲学时期,在基督教的教义所划定的范围内,人们的思维可以自由地运用其才智,只要同既定的真理没有矛盾,人类理性可以随意的解释世界。经院哲学并非根本否认理性的作用。它主要是运用形式逻辑的发法从外在的权威即教会所解释的《圣经》出发演绎推出事实。它在运用理性、思维为宗教服务的同时,也在一定限度内维护理性的作用,为后来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逐渐摆脱了哲学取得了独立的地位。但是哲学与科学仍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说,哲学发展的阶段性与科学发展的阶段性是相适应的。我们可以看到,自古希腊以来,西方哲学家们对于哲学都抱有一种理性的态度来追寻世界的答案。从古希腊以来,不同哲学家对于理性从不同的角度作了不同的解释,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对于这一问题大家的意见却相对一致,普遍将这种理性理解为是一种历史的、批判的态度。即不借助于神的或者是其他一切不可知的力量,也不迷信于任何未知的力量,对于世界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也是哲学为什么是所有学科之母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从哲学的历史沿革中我们可以发现高擎理性主义的大旗、高扬理性主义的精神是哲学的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只有立足于理性,将所有问题都放在理性的视阈下来思考,哲学才具有真正的气度。
二、哲学———关于实践的学说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认识到了自古希腊以来大部分哲学家都忽视却又十分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实践的问题。这种局限性始终制约着哲学的发展,只有马克思才找到了克服这个问题的方法———实践的方法。实践这一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现象,早就引起思想家们的注意。在哲学产生以前,很多哲学家都从自己的哲学观点出发阐述过实践问题。不过由于哲学立场和阶级立场的局限,包括唯物主义在内的全部旧哲学多没有解决好什么是实践的问题,没有正确理解实践的内容,实践的本质及实践的作用等各方面的科学内涵。科学实践观的建立,是既批判了以往各派哲学在实践观上的片面性和错误,又吸取了其有关的合理思想的结果。而这一切同辩证而又唯物的理解社会历史,即唯物史观的建立是密不可分的。第一,哲学发现了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在对实践内容的理解上突破了旧哲学的狭隘眼界。为了正确揭示实践的本质和作用奠定了基础。当马克思恩格斯把物质生产作为实践首要的、决定性的形式和实践的最基本的内容时,他们所理解的实践是同物质自然过程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自觉的社会性过程。它不仅是人作为社会存在物而存在的基本形式,而且是人类同自然界既相对立又相统一的基本形式。第二,的创始人在人类物质生产活动这一类基本的实践活动当中,找到了使物质性、现实性与能动性、创造性统一的基础。从而把两者辩证的综合起来。哲学所理解的实践活动,首先是物质生产活动。因为物质生产活动不仅仅是使对象发生改变,同时还意味这人把目的性的因素注入自然界的因果链条中,使自然界的因果链条按照同样可观的“人类本性”发生运转。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也批判了旧唯物主义者把人类活动动物化、自然化的错误。第三,哲学的创始人正确揭示了实践对世界的革命改造作用,指出“理论的批判”不能代替实践的批判。马克思揭示了物质实践的“革命的”、“批判的”功能,批判了费尔巴哈对一切只诉诸感性直观的观点,指出即使是正确的理论,也只有诉诸实践才能取得实际的效果。当然,哲学主张对现存事物进行“实践的批判”,并不意味着任何现实的实践都是合理的。要求以正确的理论作指导,使“理论的批判”转化为“现实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以后,列宁提出了主体和客体,物质和精神的“交错的=人的和人类历史的实践”的观点。则进一步把实践看做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这些都从唯物观和认识论等方面深化了对实践的科学理解。
三、哲学———关于反思的学说
进入风云变幻的20世纪,由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哲学也形成了两种主要思潮:分析哲学、现象学。上述两种思潮在形式、结构和影响等方面都有着相当大的差别。分析哲学和现象学在学科内部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迹。此外这两种思潮的内部也发生了分化。分析哲学分为科学论和日常语言论。现象学则在人类学方向上拓展,并沿着本体论方向上深化,接着双管齐下,吸收了存在主义的现实性。两种现代思潮标志着现代对于传统的反思。即对于理性的重新定位。它主要表现在:第一,它不再像近代哲学那样一心关注自然、关注外部的物理世界以及人对世界的认识,而是专心致志于语言问题、符号意义问题和交往问题。海德格尔旧转向诗和语言的语义学以显示存在。第二,与此相联系,现当代哲学都从不同角度批判传统哲学那种崇尚超感性的抽象概念王国的旧形而上学。强调现实生活和人与人之间交往。第三,现当代哲学家不再像传统哲学家那样崇奉确定的、普遍有效的准则或规范。认为一切都可以发生变化,基于逻辑规则也可以有不同的约定。科学的倾向和形而上学的倾向两者各自作不同的追求分析哲学和现象学可以相互对立,甚至彼此相轻、朝着多元主义的方向发展。反思精神在哲学界占统治地位。这种反思精神的意义何在呢?它让我们思考在哲学经历几千年发展,许多问题依然不能很好地解决的情况下,哲学的作用是什么?哲学究竟何去何从?人类既见证了物质生活的丰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文化的发展。可是同时也见证了残酷的杀戮、自然界的报复、人类精神世界的困境我们究竟要追求什么?正是这种反思精神是人类深化对哲学的认知,使哲学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的发展。它使我们对于自己有了清醒的认识,人类不可能成为世界的主宰,我们必须按照规律办事。但是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只要我们满怀热情地为人类幸福美好的明天努力奋斗,我们就一定能够有所收获,摆脱现存世界的困境。这是反思精神的真正价值所在。
篇10
有一种说法认为西方哲学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型,一次是以苏格拉底为标志的从本体论哲学向认识论哲学的转型;一次是由近代认识论哲学向现代语言哲学的转型。
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也存在着严重不足。以苏格拉底为标志的从本体论哲学向认识论哲学的转型,严格地说应是向知识论哲学的转型,这我们在文章的后面论述。这种说法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是把希腊化时期、罗马时期以及中世纪基督教时期看作西方哲学发展的异端而加以略去的,将近现代西方哲学看作是对中世纪基督教哲学的反叛和对古希腊哲学的承继而加以接上的。因为,西方历史受外族入侵的影响很大,外族入侵常常改变了西方文化的精神、西方的社会制度及人种结构。中国虽然也多次遭到过外族入侵,但入族入侵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文化、社会制度和人种结构,而常常是被中国所同化。在这一点上特殊的是中国而不是西方,因为很多文明都因外族的入侵而遭到过毁灭性的打击,比如古巴比仑、古埃及、古印度文明,唯有中国,其文明并未因外族入侵而遭受过中断或根本改变--创造中国文明的依然是华夏人的后裔,不过1840年西方的入侵或许要成为例外。
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大帝虽然是古希腊文明的积极推广者和传播者,但由于多年战争所带来的不安全感使这一时期的哲学缺乏生机和活力,这使得这一时期的哲学以伦理哲学和人生哲学为主,而不是认识论哲学。罗马虽然也是希腊文明的承继者,但希腊文明的根本精神却已经改变,古希腊人热衷于理性思考,罗马人则只重实用技术。中世纪基督教时期更是西方文明的“黑暗时代”,古希腊的理性精神被所取代。
事实上,不仅西方哲学,西方文化和西方社会虽然完全忽略希腊化时期、罗马时期和中世纪基督教时期不考虑是不对的,但将近代西方文化和社会看作是对中世纪基督教时期的反叛和对古希腊文化和社会的承继却是非常恰当的。
关于所谓的西方哲学的第二次转型,即由近代认识论哲学向现代语言哲学的转型,这是不正确的。因为语言哲学只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流派,这个哲学流派并未起到统括现代西方哲学的其它流派的作用,并且这一哲学流派由于其自身的一些缺陷而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随着现代物理学的进一步发展而衰落了,取而代之的是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科学历史主义。
事实上,与其说西方哲学的第二次转型是由近代认识论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转型,不如说西方哲学正处于第二次转型的过程中,整个现代西方哲学正是这种转型期的哲学,并且其转型的方向也不会是语言哲学,而将是向古希腊早期的本体论哲学回归。当然,这种回归并不是指在同一层次基础上回到古希腊哲学的起始状态的本体论阶段,而是指在更高一层次的基础上的螺旋上升到类似于古希腊哲学起始时期的本体论阶段。
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方向非常象古希腊哲学从本体论哲学向认识论哲学转型的过渡阶段--诡辩家时期,这个时期的特征是“古代的风纪终于变得非常松弛。富有的人懒惰而奢侈,穷人犯法作乱,年轻人越来越对长上傲慢无礼,宗教遭到嘲弄,各个阶级都精神抖擞,抱有想法弄钱、把它花在声色享受上的共同欲念。”(《古希腊哲学》第一卷第74页)在西方哲学的第一次转型的过渡期是诡辩家盛行的时期,而我们这个时代则是非理性主义泛滥成灾的时期。
之所以说未来哲学将向本体论哲学回归,是因为认识论哲学所存在根本问题的解决必须求助于本体论哲学,正如本体论哲学所存在的问题的解决必须求助于认识论哲学一样。因为本体论和认识论是一个相互缠绕的“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正是有了宇宙才有了人,从而有了人的认识;但我们之所以知道有宇宙存在以及知道我们的宇宙的具体情况又是得益于我们的认识。
二、古代部分
最初的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印度哲学一样,热衷于思考宇宙的本原等本体论问题,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宇宙观。这一时期的哲学不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属于人类认识的非常低级的直观主义阶段。这里所谓的直观是指人类无意识的凭借自己的理性、认识功能从自然界中获取知识,而没有对人类的理性、认识功能进行反思,从而弄清楚人类认识自然的方法、途径和限度等问题,从而可以让更多的人通过学习掌握这种方法、认识原理,有意识的认识自然。西方哲学比中国哲学、印度哲学的进步之处就在于他们从直观主义阶段发展到了认识论阶段,而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则只停留在直观主义阶段。
认识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人类和动物的最大差异是人类有理性可以认识自然,而动物却没有这样的能力。中国哲学、印度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最大差距就是中国哲学、印度哲学只停留在无意识的运用自己的理性认识自然的阶段,而没能将人类的理性发展成为一种有意识的认识活动。当人类懂得通过垫椅子、架梯子的方式拿高处东西,通过拉的方式开门而动物却不会(动物只会通过推的方式开站)之时,人类和动物的巨大差距显露无疑;当西方人懂得通过观察和实验研究自然规律,并力图将人类的知识建立成为类似于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公理体系的形式,而中国、印度却不会之时,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印度哲学的巨大差距显露无疑。西方之所以能够发展出科学,并进而发展出工业文明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哲学从直观主义阶段发展到了认识论哲学阶段。科学其实是认识论哲学发展的必然果实,而工业文明则是科学发展的必然果实。
我们比较一下老子哲学中的宇宙观和现代科学中的宇宙观,就会发现直观主义的严重缺陷。老子哲学的宇宙观是一种相当深遂的宇宙观,但这种深遂的宇宙观却存在着两个严重的缺陷:一是它具有模糊性;二是它具有难以深入性。我们看老子哲学会感觉到它好象什么都说了,但又什么都没有说透,它给我们的只是一种蒙蒙胧胧的宇宙观,这就是它的模糊性;我们希望将它弄的更清楚、更详细,但又不知道该如何下手、该采用什么方法,这就是它的难以深入性。相反,现代科学中的宇宙观却是相当清晰明确的,并且我们还知道该如何将它认识的更清晰、更明确,这就是通过已有理论的推演并与观察和实验结果进行比较。其实,西方宇宙观的明晰性和可深入性早在希腊哲学的早期就已经显现,原子论就是一种明晰的宇宙,从泰勒斯的“水”到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就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这里其实蕴含着西方哲学能从直观主义阶段发展到认识论阶段的原因,西方人的思维注重刨要究底,而中国人的思维只求了其大概。
可悲的是,现今中国的很多民间思想者的认识还只停留在直观主义阶段,还在用佛老的方式研究哲学问题。江上朗网友说,现今的中国思想者99%的还在用古朴的方式研究哲学。这是实情。我曾说过,如果中国未来有可能产生新思想家,那么他们九成将来自民间,一成将来自学院。因为学院知识分子主要是学问家,而不是思想家,他们是前人知识的承继者,而不是新思想的开拓者;民间知识分子则相反,他们是新思想的开拓者。就学问而言,民间知识分子一般是赶不上专业学者的,但就知识的广度和创新精神而言,则是学院知识分子远不及的。但我也曾说过,民间知识分子百分之九十几的是研究学问走入误区了的“神汉”性的人物,只有百分之几的是研究学问走对路了的人。“学海无涯,十见九谬”,这话对于民间知识分子特别具有警醒作用。我认为,民间知识分子应该经常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思,反思自己的思想是不是陷入了误区?经常和别人交流,根据别人的批评意见思考自己的观念是不是真的有问题?我这里之所以说这么多,是因为我认为中国未来的新思想的希望在民间,而民间知识分子由于社会资源的缺乏、缺少前人的指导等先天不足,因此很容易走弯路、走错路,我希望民间知识分子少一些无谓的牺牲。
我在上面指出过,西方在直观主义阶段就已经蕴含有发展为认识论哲学的因素,而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则不具有这种因素。不过,相对于唯物主义而言,毕达哥拉斯的客观唯心主义对于西方哲学从直观主义阶段发展到认识论阶段起了决定性作用。事实上,如果我们说唯物主义旨在寻求一种正确的世界观的话,那么唯心主义则旨在寻求一种有效的认识方法。相对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而言,毕达哥拉斯认为万物的本原是“数”显得荒谬不经。不过,毕达哥拉斯的“数论”却显示了人类的认知梦想,即将一切知识都表示为严谨的数学形式。关于概念,关于推理方法,关于证明,所以这些重要的方法问题,在毕达哥拉斯那里都突然显现。正是毕达哥拉斯的客观唯心主义促使西方哲学从直观主义阶段发展到了认识论阶段。
柏拉图是第一个建立完整认识论哲学并由此构建庞大哲学体系的人,自此以后西方哲学的重点就转为了认识论哲学。柏拉图继承了毕达哥拉斯学派对数学知识的偏好,对数学证明的追求。数学知识是一种相当清晰明了的知识,数学证明一旦被确认为是正确的之后它便无可怀疑。柏拉图认为只有象数学知识这样的知识才是真实的知识,象数学证明这样的方法才是可靠的方法。柏拉图的目的就在于寻找到这些真实的知识,并用类似数学证明的方法将它们从最基础的知识开始,建构成严密的体系。不过柏拉图不认为这些知识存在于感官所知觉的世界,而是一种天赋或先验的存在。因为,柏拉图认为感官所知觉的世界是变化流动的、是现象和虚幻,是不真实的。而真实的知识是一般的、普遍性知识,一种常住不变、永恒的东西。柏拉图认为,在人的灵魂中蕴藏着作为其他一切知识起点的最真实、最普遍性的某些知识、原理、观念或理念,其他的知识都是这些最基本的知识的推演。柏拉图认为,人们学习和得到知识的过程,就是灵魂逐渐“回忆”的过程。而感官对客观世界的知觉则对这种“回忆”起到激发作用。
亚里斯多德明确的将类似数学证明这样的可靠方法用三段论的形式表述为演绎逻辑,比如:
所有的人都会死
苏格拉底是人
─────────
所以苏格提底会死
这是用三段论的形式表述的演绎推理。亚里斯多德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一套完整的逻辑学体系。另外,亚里斯多德还研究了另外一种不象数学证明那样可靠、那样具有必然性的推理方法--归纳逻辑,比如,我们看到“张三会死,李四会死等”,然后推出“所有人都会死”,这就是运用的归纳法。归纳推理只具有或然性,因此亚里斯多德对这一方法并不十分看好。不过关于知识的来源问题,亚里斯多德并不象柏拉图那样排斥经验世界,认为是灵魂对先验知识的“回忆”,而是认为人类的知识是通过归纳法从客观世界中归纳得到的,没有对经验的归纳不可能有知识。不过由于他对归纳法并不看好,因此他还保留了柏拉图的先验真理论。他认为,没有对经验的归纳,不能认识真理;没有对隐然于人心的先天理性中的真理的演绎,知识不具备必然性。他在这方面是矛盾的、二元论的。
欧几里德是第一个将亚里斯多用三段论形式表述的演绎法用于构建实际知识体系的人,欧几里德的几何学正是一站严密演绎体系,它从为数不多的公理出发推导出众多的定理,再用这些定理去解决实际问题。比起欧几里德几何学中的几何知识而言,它所蕴含的方法论意义更重大。事实上,欧几里德本人对它的几何学的实际应用并不关心,他关心的是他的几何体系内在逻辑的严密性。欧几里德的几何学是人类知识史上的一座丰碑,它为人类知识的整理、系统阐述提供了一种模式。从此以后,将人类的知识整理为从基本概念、公理或定律出发的严密的演绎体系成为人类的梦想。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就是按这种模式阐述的,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同样如此。
三、近代部分
近代西方哲学对古希腊哲学有所发展,但总的来说并没有超出古希腊哲学的范围。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为人类的认识确立了一个无可怀疑的出发点,那就是人的思维、理性、认识功能或柏拉图说的“灵魂”。但是关于人类知识的来源却还有先验论和经验论之争;关于人类认识的方法也还有演绎法和归纳法之争。这种争论表现在整个认识论哲学上就是唯理主义与经验主义之争,唯理主义在人类知识的来源上是先验论者,在人类的方法论上是演绎主义者,他们认为存在着一些先验真理,人类的知识来源于这些先验真理,人类的方法是演绎法,通过演绎法可以从这些先验真理出发推导出其他一切知识;经验主义在人类知识的来源上是经验论者,在人类的方法论上是归纳主义者,他们认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先验真理,一切知识都来源于人类的经验,而人类从经验中获取知识的方法就是归纳法。但是由于哲学家们的思想并非总是前后一致的,而是常常有矛盾的,因此也存在着这样的哲学家,他们在人类的知识来源上是经验主义者,在方法论上却是演绎主义者;还有这样的哲学家,他们在人类的知识来源上既是先验论者,又是经验论者,在人类的方法论上既是演绎主义者,又是归纳主义者,他们是二元论者。另外,许多哲学家所研究的领域常常侧重于哲学的某个或某些领域,因此也存在着这样的哲学家,他们在认识论上只考虑了知识的来源问题或方法论问题,而没能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系统的认识论哲学。通常所说的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常常是根据哲学家们的主要思想倾向来区分的。
认识论中的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之争早在古希腊时期已显现,柏拉图是一位唯理主义者,亚里斯多德则主要是经验主义者,尽管他的思想也具有较重的唯理主义成份。在近代,英国的哲学主要倾向于经验主义,欧洲大陆的哲学主要倾向于唯理主义。就哲学家而言,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兹、康德、黑格尔是唯理主义者;培根、霍布斯、洛克、贝克莱、休谟是经验主义者。笛卡尔为认识论指出了一个无可怀疑的起点,但他的哲学存在很多问题,他以后的哲学家围绕着这些问题同样展开了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之争。笛卡尔是一位唯理主义者,不过他也极为注重经验。笛卡尔被视为“近代哲学之父”。到了康德那里,康德试图调合由笛卡尔开始的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之争,但是他本质上也是一位唯理主义者。他认为知识的内容来自经验,但是,心灵是按唯理的方式思考经验的。康德的哲学存在着许多矛盾,康德之后的费希特、谢林、着手解决这些矛盾,他们所采用的方法就是从康德的先决条件出发,认为精神是知识的本原,将人类的认识看作是精神的活生生的演化过程,并认为这种由精神演化出知识的过程也是客观宇宙的创造演变过程,因此人类的认识和宇宙的创造、发展和演变是同一的。到了黑格尔那里,这种解决康德哲学矛盾的思路终于完工。黑格尔认为,整个宇宙是从客观的“绝对理念”或“绝对精神”出发,按照辩证法的模式演绎的,而人的认识活动不过是它外化的一个阶段。自此,黑格尔建立了一个唯理的宇宙观,人类的认识也变成了不是由人类主动的从客观世界中获取知识的过程,而是被动的接受“客观精神”演绎的过程。黑格尔的哲学使我们想起了柏拉图的(或许应该说是苏格拉底的)“灵魂回忆”说,在柏拉图那里,人类的认识被看作是“灵魂”回忆其本身固有的天赋理念、先验知识的过程。如果说黑格尔的哲学是客观唯心主义,那么柏拉图的哲学则是主观唯心主义。黑格尔和柏拉图虽然都建立了包罗万象的唯理的哲学体系,但是他们的哲学在认识论上其实都导向了非理性主义,因为在黑格尔那里,人类的认识失去了主动获取知识的能力,而在柏拉图那里,“灵魂”回忆知识的方法变成了难以言说的激发过程。他们虽然是演绎主义者,但是演绎法在他们那里其实都变成了精神创造知识、从而创造世界的过程而失去了方法论的含义,方法意味着我们能够通过学习的方式掌握和运用它来主动的去获取知识。
黑格尔从“绝对精神”或“绝对理念”出发,按辩证法的模式演绎出整个宇宙的理论,是一套包罗万象的自恰的唯理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这种哲学得到了普鲁士国家的支持,从1820年到1840年在德国占统治地位。不过,这种理论毕竟显得荒谬不经,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这是一种“头脚倒立”的理论,另外,这种学说的认识论本质是非理性主义的,因此好景不长,黑格尔死后不久,这种唯理的哲学一反变成了反理性主义称之谓非理性主义。
事实上,从更深的层面说,黑格尔的哲学其实是以反证的方式说明了,将演绎法作为人类的根本理性、根本认知方法最终结局的荒谬性,就是它必将导致认为人类的知识增长过程和宇宙的演化过程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阶段的唯心主义观点,以及在认识论上的反理性主义。因为演绎法是从前提推出结论的方法,它的推理方向和宇宙的演化方向以及人类知识的表述方向是一致的,但和人类的认知方向(获取知识的方向)却是相反的。人类获取知识的方向是破坏一个基本前提,从而建立一个更基本的前提,这和归纳法的方向是一致的,但唯理主义都常常以归纳法的非必然性而否认这种方法,但是否认这种方法的结果只能导致直觉主义、神秘主义等非理性主义。
不过,黑格尔的哲学象所有演绎主义哲学一样,反映了人类的认知雄心,即试图将人类的所有知识表述为由一些为数不多的基本前提为起点的统一的体系;另外,黑格尔的哲学也象所有演绎主义哲学一样反映了宇宙的演化方式,即宇宙是从最初的起始状态开始的演化体系。事实上,所谓演绎法反映的正是宇宙的演化模式和构建模式,而人类的知识又是对客观宇宙的反映,这就使得人类的知识也是演绎的。但是黑格尔哲学认为宇宙的演化和人类知识的发展是同一的却是不对的。其实人类的理性象一面镜子,镜子里面的世界--即人类的知识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但是这个虚拟的世界是对客观真实世界的反映,而人类之所以能象镜子那样透视客观世界在于人类的理性具有归纳能力,而客观世界又是可归纳的或可被镜子透视的。
四、现代部分
一般将黑格尔之后的哲学称之谓现代哲学,现代哲学的最大特点是近代唯理主义一反变成了反理性主义或非理性主义,近代经验主义则顺利的发展为现代经验主义--实证主义。
非理性主义在哲学史上一直都存在,但是在唯理主义昌盛之时它被压制,黑格尔建立了包罗万象的唯理主义哲学体系却也为非理性主义打开了大门,因此他之后的唯理主义迅速转向了非理性主义,这种反理性主义思想倾向的出现也得到了来自科学界的支持。随着非欧几何的出现(后来又相继出现了集合论、相对论等),那种认为存在着一些绝对正确的先验真理,企图将人类的一切知识都建立在这些先验真理的演绎主义梦想破灭了。欧氏几何长期以来被看作是这种先验的演绎主义的标准模式,非欧几何的出现说明被看作先验的绝对真理的欧氏几何的公理并非是先验的,也并非是绝对真理,它只是后验的、相对真理。但是这种先验的演绎主义的唯理哲学的失败并非是证明了非理性主义的正确性,而是非理性主义失去了来自这方面的压制,从而得以兴盛。事实上,这种先验的演绎主义的唯理哲学的失败证明的是经验主义的正确性,一切知识都来自经验,人类是通过归纳法获取知识的,尽管归纳法是或然的。非理性主义从本质上讲是行不通的,因为非理性主义也必须寻找种种理由来说明自己是正确的,而这种寻找理由说明自己是正确的,这本身就是理性主义的任务。
现代经验主义是对近代经验主义的发展,孔德确立的将知识局限于主义经验、反对深入到现象背后的实证主义原则标志着现代经验主义的开端,穆勒、斯宾塞发展了这一哲学,马赫更是将这一哲学发展为第二代实证主义,罗素则进一步将其发展为第三代实证主义,即逻辑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是马赫实证主义的数理逻辑化,即用现代数理逻辑、符号逻辑解释实证主义。日常语言哲学和和逻辑实证主义具有亲缘关系的哲学,它们都属于第三代实证主义。通常所说的语言哲学就是指逻辑实证主义和日常语言哲学,所不同的是逻辑实证主义属于形式语言或人工语言哲学,而日常语言哲学则赞同自然语言,主张自然语言是完善的。与逻辑实证主义同时产生,但在之的流行的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或称之谓批判理性主义)是对实证主义的反对,他认为科学的发展是“经验证伪”的,而非“经验证实”的。实证主义强调科学发展中的肯定因素,而证伪主义则强调科学发展中的否定因素。取证伪主义而代之的是科学历史主义,科学历史主义是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的结合。科学历史主义将人类科学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动态的、逐渐进步的过程,其中既有实证主义所强调的肯定因素所导致的量上的增长,也有证伪主义所强调的否定因素所导致的质上的增长。我们在文章的开头说过,将语言哲学看作是西方哲学的第二次转型,即由认识论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转型是不对的,因为语言哲学本身已被证伪主义和科学历史主义所取代,并且它也无法解决非理性主义泛滥的问题。真正能看作西方哲学的第二次转型的是整修现代西方哲学,因为先验的唯理主义的失败使得西方哲学失去了一个统一的基础,即将一切知识构建成由基本公理开始的统一体系。经验主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经验主义将人类的经验仅仅局限于主观经验、现象界则是不对的,这样使得以经验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科学研究常常将自己局限于各自的狭隘的研究领域,而对别领域的毫无了解。这样就使得人类的科学研究是各自为阵的,而缺乏一个统筹按排和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
事实上失败的根本就不是唯理主义,而只是先验的唯理主义,但经验的唯理主义却是正确的。人类的知识来源于经验,是通过归纳法获得的,但人类的知识却是用演绎法表述的,并且这种知识的演绎体系是对客观世界的演绎性和唯理性的反映。它不象唯心主义所认为的宇宙的演绎过程和知识的演绎过程是同一的,而是象唯物主义所认为的只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
尽管归纳法是或然的,经验也并非完全可靠,但这其实恰恰真实的反映了人和宇宙的关系,人只是宇宙的微小一部分,而不是象主观唯心主义所认为的,宇宙是人的意识的演化,或象客观唯心主义认为的,宇宙是客观精神的演化产物。因此,作为宇宙的微小一部分的人并不先天的具有可以推演出整个宇宙的先验知识,而只能通过自己的理性对客观世界的不断观察和实验,不断归纳和总结。
另外,宇宙究竟能不能认识,以及怎样认识?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类理性的问题,而更是一个宇宙本身的形成和结构的特点的问题。如果宇宙本身是变化莫测、彼此毫无联系和共性的,那么宇宙是不可认识的,不论人类的理性有多强和采用哪样的方法。宇宙的可认识性在于宇宙存在着广泛的同源性、同质性和同构性,即许多不同的事物常常是起源于一个共同的初始状态,许多看似差异很大的事物常常是由共同的质料组成的,并且事物与事物之间常常存在着相同的结构。而宇宙中的所有事物则起源于一个共同的初始本源和由一个共同的本原(单位)组成。这使得宇宙是一个统一的、演绎的、唯理的体系,而人类的认识则是对宇宙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层次的本源和本原的归纳。
归纳法的有效性取决于宇宙的某种同源、同质和同构的范围,当我们归纳的事物未超出某种同源、同质和同构而得到的知识却是关于这一范围的同源、同质和同构的知识,那么归纳法就是有效的,我们得到的知识就是可靠的;如果我们归纳的事物超出了这种同源、同质和同构的范围,那么我们归纳得出的关于这种同源、同质和同构的知识对这一事物就是我效的,我们就需要归纳更广泛的同源、同质和同构的知识才能适用于这一事物。正是由于宇宙存在着广泛的同源性、同质性和同构性,所以宇宙是有规律变化的、相互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和共性的宇宙,所以宇宙才能被人类的归纳理性所认识。
总的来说,宇宙应该存在着一个最初的起源,尽管它的起始时间可能无限遥远,其它所有事物都是由这个最初的起源演化而来的;另外,宇宙也应该有一个最根本的本原,即组成单位,其它所有事物都是由这个最根本的本原组成。我们只要认识清楚了这个最初的起源和最根本的本原,那么万事万物的状态都可以由关于这个最初的起源和最根本的本原的知识推演出来。但是这需要我们通过无限的时间、步骤和努力才能得到。
宇宙的同源性、同质性和同构性也就是宇宙的统一性,宇宙的广泛的同源性和多层次的同质性说明宇宙是一个庞大的统一体系。而宇宙的统一性和宇宙的演绎性是一种互逆的表述方式,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宇宙的统一性的表述方式是,“宇宙统一于其本源或本原”,宇宙的演绎性的表述方式是,“宇宙由其本源或本原演绎”。宇宙的演绎性说明了宇宙是一个唯理的宇宙,而不是一个非理的宇宙。正是由于宇宙的统一性、演绎性和唯理性,才使得人类通过归纳法归纳的关于客观宇宙的知识也是统一的、演绎的和唯理的。人们通常所说的演绎法其实并不是认知方法(获取知识的方法),而是知识的一种表述方法,我们是用演绎法来表述人类的知识体系的,但我们获取知识的方法是归纳法。
当然我们上面所说的唯理的宇宙只是经验的唯理的宇宙,而不是先验的唯理的宇宙,它是根据人类的经验从客观宇宙中归纳出来的,而不是象先验的唯理的宇宙是从先验的知识、存在、意识和精神演绎的。由于归纳法在没有对整个宇宙都进行完全归纳之前,它只具有或然性,因此经验的唯理的宇宙观也并不能说是绝对真理,它只能说是我们通过对人类的有限经验归纳后得到信念,但是这种信念对于指导人类的进一步认识却是非常重要的。毕竟我们的未来发展和认识不能是盲目的,而是根据已有有经验所总结的规律或信念作指导的。这种经验的唯理的宇宙观和知识观可以解决纯粹经验主义(只将经验局限于人类的主观经验或现象界)所导致的科学研究的狭隘性和各自为阵性,并且它本质上和经验主义是一致的和统一的,而不是象先验的唯理的宇宙观和知识观,是和经验主义相矛盾的。另外,它也可以有效的消灭现代西方哲学中非理性主义泛滥成灾的问题。
我认为西方哲学的未来发展方向就是确立这样的唯理的经验的宇宙观和知识观,和建立与之相统一的哲学体系。如果这个论断是正确的,那么整个现代西方哲学则可以看作是由先验的唯理的知识观、宇宙观向经验的唯理的知识观、宇宙观的转型。将经验限定在人类的主观经验和现象界的实证主义是这种转型期的经验主义,是不成熟的经验主义。五、西方哲学的未来
人们常常把第一阶段的西方哲学称之谓本体论哲学或宇宙观哲学,而把第二阶段的西方哲学称之谓认识论哲学。但事实上,第二阶段的西方哲学主要发展的是演绎法以及与之相统一的先验的唯理主义哲学,演绎法到罗素那里已经符号化,发展为数理逻辑,先验的唯理主义到黑格尔那里也发展到了极致。但是归纳法到目前为止连其基本问题--“归纳合理性”的哲学问题都还未解决,经验的唯理主义也自今还未发展起来。我认为未来的西方哲学将重新返回到本体论哲学和宇宙观哲学阶段,当然这种返回的严格地说法是更高层次上的螺旋上升,而并非同一层次上的往复运动,因为这是解决“归纳合理性”问题的需要。归纳法的合理性问题只能用本体论哲学和宇宙观哲学来解决,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具有广泛同源性和多层次同质性的唯理的宇宙观哲学。休谟认为归纳法是人的心理习惯和信念,但这只能说明人类具有这样的心理基础,而并不能说明归纳法具有合理性,能有效的从客观世界中获取知识。归纳法的合理性只能用具有广泛同源性和多层次同质性的唯理的宇宙观哲学来解决。这样经验的唯理的哲学就必须确立,这样认识论哲学又必须转回到本体论哲学或宇宙哲学。
人类在认识论哲学主要发展的是演绎法以及与之相统一的先验的唯理的宇宙观和知识观,而不是认识论哲学本身,因为认识论哲学应该是关于获取知识的方法的哲学,而不是关于表述知识的方法的哲学。人类在第三阶段的本体论或宇宙观哲学阶段主要将发展的是归纳法以及与之相统一的经验的唯理的宇宙观和知识观。人类有时在事后才会明白先前所认为和某种东西与后来所认识清楚的东西并不一致,先前的认识只是一种错觉。总的来说,第二阶段的西方哲学主要发展的是知识论哲学,而不是认识论哲学;我个人认为人类在第三阶段的哲学阶段才会真正的发展认识论哲学,不过其基石和总体表现将是本体论和宇宙观哲学,因为归纳法的合理性问题依赖于本体论哲学和宇宙观哲学。作为人类知识表述的方法的演绎法,发展的高级阶段是数理化或符号话,我认为作为人类认识宇宙的方法的归纳法,发展的高级阶段应该是和人类的观测工具和实验工具结合起来。因为人类的知识的表述本质上就是语言表达的问题,而数学语言和自然语言是人类的两种不同的语言形态,演绎法本质上就是和它们紧密相连的,这也是演绎法发展到高级阶段--数理化和符号化导致语言哲学兴盛的根本原因。而人类的认识本质上就是和人类的感官以及人类感官的延伸--观测工具和实验工具紧密相关联的,因此作为人类的认知方法的归纳法发展的高级阶段必然和人类的观测工具和实验工具紧密的相结合。
当然,有人也可能认为本体论或宇宙观现在已经转化为科学家的任务而不需要哲学家来操心,以此来否定未来的哲学将重归于本体论哲学或宇宙观哲学。我个人并不赞同这种观点,我认为那种认为哲学的某个领域成熟后就转化为科学家的任务,而不需要哲学家操心的观点是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的误区,因为任何成熟的理论的最前沿都是不成熟的,这样哲学家就有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另外一个区别就是,科学家总是将其研究建立在观察和实验事实的基础上或原有理论的逻辑推理之下,而哲学家更愿意透过观察和实验事实或原有理论看本质。
上面我们在论述了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型及未来可能发展的方向之后,有必要再回到语言哲学的问题上。我们在前面说过,语言哲学是伴随着演绎法的数理化和符号化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哲学流派。语言哲学的实质是关于概念的演绎逻辑。我们在前面还说过,演绎法就其本质而言,它不是认识方法,而是知识的表述方法,这种知识的表述方法是对客观世界的演绎性的反映。而语言的作用就是我们用于表述客观世界的,只是语言有自然语言和数学语言之分。自然语言是一种较灵活、较模糊的语言,而数学语言则正好相反,是一种很严谨、很精确的语言。演绎逻辑其实就是将自然语言的灵活、模糊与数学语言的严谨、精确相结合研究语言的内在结构和形式的学科。
演绎逻辑的语言实质在柏拉图和黑格尔的哲学中表现的很清楚,这两个人都创建了包罗万象的唯理的哲学体系。柏拉图哲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理念”,他所说的“理念”说透了就是具有主观实在性的概念,柏拉图是一位主观唯心主义者,他认为概念具有主观实在性,只有关于概念的知识才是真实的知识,关于概念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经验世界是虚幻的、不真实的;黑格尔哲学的基本概念是“绝对理念”,他说的绝对理念说透了就是具有客观实在性的概念,黑格尔是一位客观唯心主义者,在他看来概念具有客观实在性,整个宇宙就是从真实的绝对概念出发,按辩证法的模式演绎出万物,又回归到绝对概念的过程。
- 上一篇:风景园林工程监理实施细则
- 下一篇:安全监理工程师的职责
相关期刊
精品范文
10哲学伦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