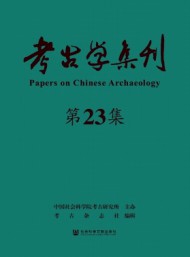考古学文化范文
时间:2023-10-20 17:32:07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考古学文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中图分类号:K8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9-0100-02
考古学文化的区,指的是文化区。在考古学上的意义就是指一个考古学文化分布的地理空间范围。一般情况下,一种文化分布的地理空间范围(相对比较大的地理空间)就是一个文化区。研究它的首要目的,是为了区分各种考古学文化在一定时期内的空间分布,从而为进行较大范围内的横向考古学文化研究奠定基础。
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学是建立在文化遗存之间或遗址之间的比较之上的。比较是人类认识事物的最基本方法之一,也是人类思维中最经常的一类活动。有比较才有鉴别,没有比较,人类认识事物的过程就不可能完善,人类的知识体系也无法存在。只有在研究中比较考古学文化的不同现象,才有可能发现出他们各自得内涵,才有可能对他们产生概念上的认识。区、系、类型的研究方法就是一种比较法,这里所指的比较不是潜在的、无意识的,而是刻意的、有意识的。世界上各事物都存在某种联系与依托,同时,这些事物都处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只有通过比较,才能使事物的特征更加鲜明。
由于不同地域的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获取生活资料的方法各不相同,生活方式也各有特色,因此,古人遗留下来的文化遗存或多或少地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就是我们区分不同考古学文化或不同文化类型的关键依据。
我们在做判别和区分的时候,是离不开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来做依托的。首先,我们应根据考古地层学原理,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借助现代科学测年法,确定某一地区考古学文化发展的序列及相对年代;其次,在具体开展考古发掘和研究时,应先从单件的器物,或个体遗迹入手,从对遗迹遗物形态特征的研究,上升到聚落群体的研究,其中包括聚落内各遗迹之间的关系。接下来,从聚落之间的比较上升到聚落群的比较,通过聚落群之间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因素的比较研究,确定文化区,这便是所谓的从器物本位上升到聚落本位,再上升到文化本位,最后上升都最高层次,即社会层次。在对某地区的田野考古发掘积累到一定量之后,根据一定数目的已发掘的遗址,设法搞清某种考古学文化的特征,包括墓葬、建筑、陶器、农业生产等。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通过考古类型学的研究,在更大范围内比较不同遗址,从而认定同一考古学文化的分布范围。要确定一个考古学文化区,一定要经过反复比较;同时,这些要比较的遗址,必须经过正式发掘并具备一定量的遗迹遗物基础。在进行两个遗址比较时,主体部分至少应有50%以上相似特征的文化因素,这样才可确定两个遗址或两个遗址中的某个文化层属于同一文化。如果仅有少量相似的文化特征,一般情况下,仅仅能视作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而非同一文化。
同时,在比较中,我们还应注意某一文化区周边器物的其它文化区。在同一文化区内,最典型的文化特征集中的地区为中心地,即文化中心。而离文化中心最远的地区为文化边区地区。这些边区的文化由于多数情况下处于两种文化区的交界地,一般都是两种文化的交界处,包含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因素。因此,划分边区文化区的范围十分繁杂,一定要格外留意,要经过正式发掘并且加以量的比较,才能比较准确地做出划分。当然,确定文化区的中心也很重要。如果中心确定不准确,那整个文化区的范围就会被划大或是圈小。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文化区的范围,即文化边区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动态的,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不断变化的。因此,我们要通过精确的分期及大量的研究比较,才有可能确定出不同时期文化区的范围。
考古学文化的系,是指文化发展的系统或者系列,也就是考古学文化纵向的发展脉络。一般情况下,它是由若干个有时间发展关系的考古学文化构成的,是某一区域内文化发展的先后序列。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都有一定的时间范围,与此同时,每种文化又一定与该地区先后的文化有着某种关系。反映到考古学文化上,则表现为每一种考古学文化都具有其产生渊源及发展方向。所以,每一个考古学文化系统都是由若干纵向发展关系的文化构成的,而要确定一个文化系统,也必须建立在考古地层学与考古类型学的基础上。具体来说,考古地层学主要靠研究判断在某地区内各种考古文化出现的先后顺序,而考古类型学则是通过对具体的遗物的研究分析,以此来确定器物之间前后承袭的发展关系。
考古学文化的类型,指的是文化类型。关于它的具体含义,目前还存在一定争议。多数学者认为它指的是在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区域内由于微环境的条件差异,包括自然环境、地理条件、其它文化的影响等因素,在主体文化因素一致的前提下,表现出某种地域性的差异。这种地域性的差异通常就会用考古学文化类型来定义。当然,每种文化类型也存在一定的区域性。
一种考古学文化可能由几种考古学文化类型(地区类型)构成,由分布在一个区域内相似的若干个遗址构成。因此,尽管文化类型也有时间上的差异,但更多的表现却是空间上的不同。这种文化类型,也可以叫做文化分支,它对于进一步了解考古文化发展的复杂性,是相当有意义的。
在人类学研究中,人类文化即有普遍文化与亚文化之分,亚文化表现出不同的地域性、民族性、甚至是职业性。在文化的主题因素一致的前提下,文化类型就可以视为一种考古学文化的分支、或是类似于文化人类学上所说的亚文化。文化类型主要表达的,是一时期内不同空间上所表现得文化差异,而分期则注重表现相同空间内不同时期的文化差异,应该把它们的侧重点搞清,不要混淆。
从理论上讲,统计的器物类型越多越好,这种文化因素分析法是从具体的器物、遗址、到遗址群、再到文化区、最后再到不同文化区之间的文化因素比较,也包括早晚文化的比较,这样才能建立出某一地区文化发展的时空框架。
在运用比较法的时候,我们不能仅依据某单一方面,如果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只能依据一个方面,也必须尽可能得从多角度全面加以分析。例如,一个考古学文化的陶器比较,我们要从纹饰、器形、陶质、陶色、制法等多方面,只有这样才能比较准确地判别出文化的属性及某些文化因素的来源与早晚关系,不能仅依靠简单的比较就得出某两种文化属于同一考古文化或不同文化,一定要有一个全面的定性、定量的研究。
在考古学的研究中,无论是在史前时期还是在历史时期,区、系、类型学都是一项基本的研究问题。在史前时期,尤其是新石器时代,它更是一项基本任务。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框架的建立,为我们从宏观上探讨历史文化,探究民族的形成发展以及民族文化的变化等重大问题奠定了基础。区、系、类型学是从实践中得出,再回到实践中检验,并且在反复检验中指导更高层次的研究方法。确立区、系、类型学的基础前提是正式发掘的大量田野考古资料。也就是说,只有当考古工作者通过考古发掘获得了一定量的可靠的资料,才能设法确立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同时,这个区系类型必须在日后的发掘中不断检验并完善,并进一步指导更高层次的研究分析。要通过反复的验证,不能拘泥不变,轻易下结论。我们知道,仰韶文化是我国第一个被确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然而,自从它最初被确立开始,直到今天,有关它的认识都是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不断发展,资料的不断丰富,以及研究的逐渐深入日益完善并改进的。并不是从它一经发现便得出今天的结论。我们对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的研究,都要经过反复验证,要掌握大量的真实材料,同时采取科学的态度。
任何文化都有一定的时空范围。对于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来说,区是块、系是条、类型则是分支。这三个方面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在研究中,我们要从宏观上加以注意,不能将它们割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考古学文化有一个更为科学的认识。
篇2
摘 要:石家河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分布于长江中游的考古学文化。本文主要依据肖家屋脊石家河文化遗存,在已分期的基础上,重新把石家河文化早期晚段遗存分为前后两组,基本能够反映出石家河文化从繁荣到衰落的过程。同时结合文献,指出石家河文化衰落到衰亡的原因与尧、禹征伐三苗有关。
关键词:石家河文化;衰落;中原龙山文化;尧禹
石家河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分布于长江中游的考古学文化,其以巨大的城址、随葬品丰富的大墓,较为浓厚的宗教遗存,使其成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独特且发展水平不亚于同时期其他文化的区域文化中心。已有考古发掘显示:石家河文化在经过早、中期繁荣之后,演变到石家河文化晚期,却突然衰落下来,甚至其后衰落不存在。关于该文化的衰落,目前学术界主要集中于两点,衰落的时间和原因探讨。前一点学术界比较认同:在石家河文化晚期,其文化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肖家屋脊发掘者更是认为,肖家屋脊晚期遗存“与早期文化有相当大的差别,与早期文化之间呈现出一种断层想象”。[1]但也有学者曾独到的认识到在石家河文化中期后段,石家河文化文化面貌已经在发生了较大的变化[2],这一点我们赞成。对于第二点,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如中原文化南下[3]、生态危机[4]、社会生产和社会组织发展呆滞[5]等,对于研究石家河文化的衰落原因起到很大的作用。本文愿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最近新的研究成果,去进一步探讨石家河文化衰落的时间及其原因。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石家河文化分期
石家河文化分布范围较广,北至汉水中游、丹江下游、南阳盆地、桐柏山、大别山一线,东至麻城、薪春、大冶、通城一线,南至洞庭湖南岸乃至湘中丘陵北部一带,西至大巴山、武陵山、巫山山脉一线均发现有石家河文化遗存,江汉平原中北部特别是石河镇石家河遗址群是其中心分布地带。[6]
关于石家河文化的分期,这是我们讨论问题的基础。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做的很多,如王劲[7]、李龙章[8]、何介钧[9]、张绪球[10]等先生都对该问题有深入的探讨,其中张绪球先生关于石家河文化三期说较有代表性,基本反映了石家河文化在该地区存在的各阶段。我们暂且沿用张续球先生关于石家河文化三期说,参照石家河文化中心区域邓家湾[11]、肖家屋脊等把石家河文化分为三期:
早期:典型遗存为邓家湾一期;中期:分为两段,早段相当于邓家湾二期、肖家屋脊早期前段,七里河石家河一期晚段也归入该阶段。关于晚段遗存,可以细分为两组:第一组以肖家屋脊H161、H434为代表,七里河二期应归入该组,第二组以肖家屋脊H42、H43为代表,所谓七里河三房湾文化应该归入该组;晚期:主要为肖家屋脊石家河文化晚期遗存。早中晚三期四段基本反映了石家河文化在腹心地区发展各个阶段。
关于肖家屋脊石家河早期晚段遗存,其实发掘者在分期时已经注意两组之间的不同,在分期时有意将两者分开。查看灰坑登记表,我们发现其实两者差距还是能够分开的,现划分为早晚两组。
在第一组,该组以H434、H161等为代表,其器型主要有高领罐、中口罐A、BI、CI型、缸、臼、钵AI、BI、擂钵AI、豆、斜腹杯、罐型鼎、盆形鼎、壶形器、碗等。该组继承了较多肖家屋脊石家河文化早期早段器型,如高领罐、中口罐A型、缸、臼、斜腹杯、鼎、碗、壶形器等,同时出现了一些新器型,如中口罐B、C型、钵、擂钵、广肩罐等。
在第二组,以H42、H43为代表,原第一组较为常见器型数量已接近消失或器型没发生变化,如高领罐、碗、壶形器、盆形鼎、小鼎等几乎已经消失或者数量极少;缸、臼、罐形鼎、中口罐A型、斜腹杯等器型多无明显变化;原第一组新出现的器型变化较为明显,如中口罐B型、C型由第一组的鼓腹变成深弧腹,钵A型由深腹到浅腹,漏斗形擂钵由深盘口到浅盘口,另外该组还新出现了盘、高圈足杯、碟、三足杯等。
另外,从陶质、陶色来看,两组遗存相差也较大,以H42、H43、H434、H161为例,虽两组单位均有泥质陶、夹砂陶,且均以泥质陶为主,但是在第一组夹砂陶占有较大的比例,而在第二组夹砂陶数量很少,泥质陶占有绝对的比例;在泥质陶中,第一组以黑、灰陶为主,红陶比较较少,到第二组,红陶的比例较多,且多于泥质灰陶和泥质黑陶;另外在第一组还发现一定数量的夹炭陶,而第一组却没有发现。从纹饰来看,两者均有较多的篮纹,一定数量的方格纹,少量弦纹、绳纹、镂空、附加堆纹等,但是弦纹、附加堆纹等第一组数量稍多,且在第一组中没有戳印纹、刻花纹、红衣等装饰。
二、从肖家屋脊遗址看石家河文化中期以来的变化
肖家屋脊遗址位于湖北省天门市西北约16公里处,南距石河镇0.5公里,面积约15万平方米。为深入了解江汉平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点和谱系关系,以及探讨石家河遗址群的内涵及其在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地位等问题,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于1987―1991年先后八次发掘肖家屋脊遗址。该遗址文化堆积厚薄不均,东周楚墓、石家河文化、屈家岭文化三种文化遗存顺次叠压,以石家河文化遗存最丰富,共发现石家河文化房址6座、灰坑499个、灰沟23条、井1口、路3条、窑2座、陶臼遗迹7处、水塘遗迹1处和109座墓葬等大量遗迹。肖家屋脊遗址石家河文化遗存早晚期遗存,基本反映出石家河文化在江汉平原从繁荣到不断衰落的全过程,对于它的研究,对于我们研究石家河文化的发展到衰亡的过程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肖家屋脊石家河文化早期遗存(相当于石家河文化中期),分前后两段。前段,其器型主要有高领罐、壶形器、盆、碗、豆、斜腹杯、高劝阻杯、小鼎、器盖、缸等,其他如罐型鼎、盆形鼎等数量较少。在邓家湾同时期遗存中,罐形鼎、盆形鼎较多,且罐形鼎、盆形鼎多为炊器,应是其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用具。对此,我们认为石家河文化盆形鼎、罐形鼎、小鼎、高领罐、壶形器、高圈足杯、缸、碗、豆、器盖等应该为石家河文化腹地其最主要的器型。检视该时期器型,其不仅在石家河文化早期发现较多,即使是比其更早的屈家岭文化晚期也能到其渊源。
到了肖家屋脊石家河文化早期晚段(石家河文化中期晚段)第一组,其主要器型开始发生了变化,该时期器型有三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部分原石家河文化比较常见的器型到了该阶段形制变化较为单一或数量很少,如碗、尊、高圈足杯、小鼎等。
第二.部分原石家河文化较为常见器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高领罐,原报告分为三型,观察其变化,A型高领罐,早期多为宽凹沿,鼓腹,器身整体较高,到了晚段第一组,其多为直口,球腹,较为矮胖,另外B、C型高领罐也基本上略同该形制;红陶杯,数量较多,整体来看,该时期胎壁较厚,腹腔变小;盆形鼎,在早期上腹壁向外斜直,到该段折沿,上腹壁向外斜弧,下腹内折起棱;缸,原报告分为三型,其中Aa型缸数量较多,变化较为明显,在石家河文化早期其多为宽沿外撇,上腹壁斜弧,下腹内折起棱,到了该时期宽沿外折,上腹斜直,下腹内折起棱。另外罐形鼎、豆、长颈罐、盆、臼等较早期都有较大的变化。
第三.出现了一些新器型,钵、擂钵、广肩罐、簋、橄榄形罐(中口罐B、C型);观察新出现的器型,观察起来源,应该是来自青龙泉三期类型无疑。以七里河遗址为例,钵,厚缘作风,石家河文化主要为圈足碗,如钵这样的器型很少,而在七里河同时期发现较多,在比其较多的早段中也有较多的发现,可以肯定,应属于青龙泉三期类型无疑。擂钵,从早到晚发展很明确,A型擂钵,出现在七里河石家河文化一期后段,一直延续到七里河三房湾文化;B型擂钵在七里河遗址发现更早,在石家河文化一期前段就发现较多。另外高领瓮、簋在七里河遗址早期遗存中都能找到其渊源。
肖家屋脊遗址早期晚段(石家河文化中期晚段)第一组主要器型
1―11H552:1、H107:48、AT405③:1、JY7:4、H434③:17、H434②:72、H161①:7、H88:13、H394:1、H56:8、H434③:63
肖家屋脊遗址早期晚段(石家河文化中期晚段)第一组新出现器型
1―5H434④:3、H434②:71、AT604②B:2、H434③:9、AT7604②:13
相对于中期晚段第一组而言,到了第二组其变化更为明显,涉及面更广,表现在原从石家河文化以来较为流行的器型如高领罐、中口罐A型、壶形器、碗、高圈足杯、盆形鼎等已经接近消失,而缸、臼较为形制单一,且与第一组相差不大。第一组新出现的器型到了该组也有了较大的变化,如钵到该组变的较浅,擂钵在第一组多为深盘口,直筒形腹到该组盘口变浅,筒形腹上粗下细、簋等;同时出现了一些新器型如三足杯、高圈足杯、盘、碟等。总的来说,到了该阶段,原石家河文化文化因素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肖家屋脊遗址早期晚段(石家河文化中期晚段)第二组主要器型
1―10H414:1、H43:21、H427:4、H42①:30、H116:6、H42①:9、H42①:34、H42①:150、AT3017:4、H42①:54
三、石家河文化衰落的历史学观察
从以上分析来看,在石家河文化中期早段,石家河文化基本保持自屈家岭文化晚期、石家河文化早期的器物组合,但中期晚段开始,石家河文化开始逐渐发生变化,在中期晚段第一组,从石家河文化北部青龙泉三期类型文化传播过来的擂钵、豆、高领瓮开始出现并流行。到了第二组,这种趋势更加明显,具有北方青龙泉三期文化类型的因素更具强烈。石家河文化到了中期晚段第二组基本上原有石家河文化因素已经很少,以至于到了石家河文化晚期几乎已经消失,而此时中原文化因素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对此其变化的原因,许多学者多是从自身原因和自然环境变化去研究其衰落的原因,除此之外一个很大的原因应该是中原王湾三期文化南渐造成的。考古发掘显示,王湾三期文化已经发展到很高的程度,如农业生产工具比较先进,形制复杂多样,有铲、撅、刀、镰等;农作物种类较为丰富,有粟、黍和水稻等,、、觚形杯、等饮酒器具的大量出土,表明酿酒饮酒之风盛极一时,它应是农业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反映。制陶业此时期已普遍采用了快轮制陶技术,烧制火候比较高,有的可达1000℃以上,另外还发现了青铜残片。在此基础上,在该时期还发现大量的城址,如后岗、孟庄、古城寨、新碧、王城岗、平粮台、郝家台等,尤其是王城岗面积,从而使王湾三期文化发展到足以影响及占据石家河文化的水平。
《尚书・尧典》,“窜三苗与三危……而天下咸服。”这是最早记载尧征三苗的文献。另外《吕氏春秋・召类》:尧占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论衡・儒增》“尧伐丹水”。《帝王世纪》“诸侯有苗氏处南蛮而不服”,“尧征而克之于丹水之浦”。《墨子・非攻(下)》记载“昔者三苗大乱……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文献详细记载了中原文化两次大规模的征伐三苗的过程。第一次,尧征丹水,尧征服了唐白河流经的南阳盆地以及丹江中下游地区,迫使三苗势力南退,从而使原石家河文化分布区的丹江中下游地区文化性质改变,大寺龙山文化遗存[12]应该就是尧征三苗后还保留较多的原石家河文化因素,原中原文化因素还不够稳定的表现。而此时,在石家河文化中心分布区其文化性质还未改变,但是却融入了较多的原青龙泉三期类型的因素,这正是三苗文化在尧占丹水后南退的反应。第二次,禹征三苗,彻底打破了原有石家河文化体系,以至于到了石家河文化晚期,在石家河文化的中心地区石家河文化因素已经很少,而王湾三期文化占据了主要的位置,这种文化面貌反应在豫东南杨庄遗址[13]甚至在鄂西石板巷子[14]种情况也依然存在,从而在较大范围内文化面貌表现较为一致性的反应。(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参考文献:
[1]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等石家河考古队:《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年。
[2] 白云:《关于“石家河文化”的几个问题》,《江汉考古》1994年3期。
[3] 樊力:《略论三苗族及其文化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原文物》1998年第1期。王红星:《石家河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外力作用问题》,《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7年。
[4] 何弩:《可持续发展定乾坤――石家河酋邦崩溃与中原崛起的根本原因之对比分析》,《中原文物》1999年第4期。
[5] 童恩正:《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6] 郭立新:《石家河文化的空间分布》,《南方文物》2000年第1期。
[7] 湖北省博物馆等:《房县七里河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江汉考古》1984年3期。
[8] 李龙章等:《浅议石家河文化》,《江汉考古》1985年3期。
[9] 何介钧:《长江中游原始文化初论》《湖南考古辑刊》第1辑。
[10] 张绪球:《石家河文化的分期、分布和类型》,《考古学报》1991年第4期。
[1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石家河考古队:《邓家湾》,文物出版社,2003年。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龙泉与大寺》,科学出版社,1991年。
篇3
我国东部沿海的大汶口文化、北辛文化、岳石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马桥文化等,都是这一时期命名的,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苏秉琦先生根据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提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对于我国考古学向纵深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对于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研究,无疑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区、系、类型”理论的前瞻性主要有二:根据“区、系、类型”理论,苏秉琦先生将我国群星璀璨的考古学文化归纳为六大区,“区、系、类型”中的“区”不仅空间大于考古学文化区,而且“区、系、类型”中“区”的层次也高于考古学文化区。苏秉琦先生从全新的高度将“考古学文化区”的概念上升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的“区”,不仅为考古学建立了更加广阔的时空框架,也为宏观地对考古学文化进行动态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苏秉琦先生在提出考古学文化的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的同时,还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一体”模式、从“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观点到“古国、方国、帝国”的理论和“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为国家形成的三种模式等文明起源理论,因此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区、系、类型”理论实际上已成为通过考古学方法研究和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理论基础③。考古学理论来源于考古学实践,考古学理论应对学科研究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三十年过去了,当年苏秉琦先生基于现有资料对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探索虽具有前瞻性,然这一理论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实践中也日渐显现出理论的不完善和受考古资料的局限而出现一定的局限性。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局限性主要有二:同一律和普遍性等基本概念不明确。“区、系、类型”理论中出现了考古学文化的“区”、考古学文化的“系”和考古学文化的“类型”,苏秉琦先生对“区、系、类型”的定义如下:“在准确划分文化类型的基础上,在较大的区域内以其文化内涵的异同归纳为若干文化系统。这里,区是块块,系是条条,类型则是分支。”显然,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与原有的“考古学文化”、“考古学文化类型”等考古学专业名词文字相同而概念或定义不同。根据苏秉琦先生的定义,“区、系、类型”中的“区是块块”,属于空间范畴;而考古学文化区也同样属于空间范畴。在苏秉琦先生划分的六大区系中,“东部沿海的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主要指“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分布区,即海岱地区;尽管苏秉琦先生认为胶东半岛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属另一个文化系统,实际上胶东半岛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可归属海岱地区的一个亚区。而“长江下游地区”则包含了太湖地区的“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宁镇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和江淮西部的“薛家岗文化”等不同的考古学文化。
根据苏秉琦先生的划分,“东部沿海的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大致相当于“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分布区;而长江下游地区却包含着“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北阴阳营文化”和“薛家岗文化”的分布区。因此“区、系、类型”的“区”似乎既可等同于一个考古学文化区,又可包含若干个考古学文化区。此外,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的“区”,或以省命名,如“陕甘晋”“、山东”和“湖北”,或以流域或方位命名,如“长江下游”“、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等。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有考古学的基本标准④,而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中“区”的命名,既无统一的标准,又无规律可寻。“区、系、类型”中的“系是条条”,显然属于时间范畴;而考古学文化的分期和文化的发展演进也同样属于时间范畴。根据苏秉琦先生对大汶口文化发展演进为龙山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发展演进为良渚文化的论述,“区、系、类型”中的“系”主要指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发展演进而不包括考古学文化的分期。在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文化分期属于量变,而文化的发展演进则属于质变,质变是由量变的积累而发生的突变。因此,“区、系、类型”中的“系”与文化分期、文化演进的相互关系的区分,“系”的时间概念与文化分期和文化演进的时间概念的区分,显然存在着概念上的不确定性。在同一考古学文化中,由于分布范围或文化面貌存在一定的差异,往往又分为若干类型,如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史家类型”、“庙底沟类型”、“秦王寨类型”、“大司空村类型”和“西王村类型”等,而龙山文化则有“城子崖类型”和“两城镇类型”等。在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区、系、类型”中,“系是条条,类型则是分支”,显然“区、系、类型”中的“类型”与考古学文化的类型有着不同的概念。
“系是条条,类型则是分支,”既然有分支,也必然有主干,主干与分支也同样存在概念上的不确定性。综上所述,“区、系、类型”的“区”不等同于考古学文化区的“区”“,区、系、类型”的“类型”也不等同于“考古学文化类型”。考古学理论既须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为理论基础,又须符合形式逻辑的基本原理。一个学科中用同样文字的专业名词表示不同的概念或有着不同的定义,似乎有悖于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同一律。考古学理论应具有普遍性,应适用于不同时期的考古学研究。“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如仅适用于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似乎又缺乏普遍性。区系的划分割裂了东夷民族文化区。受考古资料的局限,苏秉琦先生在“区、系、类型”中划分的六大区系是在尚存若干考古学文化空白区的情况下划分的,尤其是淮河的中游地区与下游地区。因此六大区系的划分出现局限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江淮东部和江淮中部地区在当时还是考古学文化的空白区,还没有龙虬庄、侯家寨、凌家滩、双墩等遗址的发掘,还没有龙虬庄文化、双墩文化、侯家寨文化和凌家滩文化的命名。徐旭生先生根据对古史传说的研究,划分了华夏、东夷和苗蛮民族集团的空间分布范围。其中将渤海湾以西到钱塘江以北划为东夷民族的分布空间⑤(图一)。而苏秉琦先生将我国东部沿海划分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显然割裂了东夷民族文化的分布区,显然强调了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考古学属性而忽略了区系划分的民族学属性。“‘考古学文化’是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同一地域内的、有一定地方性特征的遗迹和遗物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应该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集团的。由于这个社会集团有着共同的传统,所以在它的遗迹和遗物上存在着这样的共同性。
篇4
按认识规律和内在逻辑,把中国考古学的现状和最新研究成果,客观、系统、全面地揭示出来,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教材主要面向:
考古学一级学科内各专业在校本科生
本科阶段非考古专业的考古学研究生
地方文博单位的业务人员
一、中国考古学研究的现状
以1970年代中期为界,之前,中国考古学处在一个波浪式的发展阶段。
之后,中国考古学则进入一个持续发展时期。
-田野考古规模不断扩大,研究水平迅速提升。
-其原因,有外、内之分。
1970年代后期以来,各文化区新石器至早期青铜时代的文化发展序列和谱系的建构,是中国考古学的主轴和中心任务。
苏秉琦先生的“区系类型”学说,顺应和指导了这一阶段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这期间,各大区系一系列新的考古学文化得以面世和确立。
以五大区系为例-中原、海岱、环太湖、江汉、燕辽地区。
从1980年代中期以后,在以年代学为重心的文化史研究的过程中,中国考古学研究开始出现一些新的趋势,如:
1985年,夏鼐先生《中国的文明起源》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1986年,苏秉琦先生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的问题。
此后一段时间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和研究逐渐增多。
稍前,张光直在北大、山大举办的系列讲座,介绍了“聚落考古”等欧美考古新观念。
在欧美“新考古学”的影响下,关于国内考古学所处阶段、存在问题的讨论。
1991年2月,“考古工作涉外管理办法”正式颁布。
随后,以区域调查和田野发掘为主的中外合作考古项目得以开展和实施。
到1990年代中期,以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为主的各大区系,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和文化谱系基本建立起来。
此外,中国考古学研究进入一个转型时期,即从以年代学为中心的文化史研究,向以人为中心、以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环境、资源及其互动关系为基本内容的社会考古研究转移。
要全面研究和揭示古代社会,客观上需要更多的不同门类的新资料。
于是,采用聚落考古的方法,全面改进田野考古工作,引入各种有用的现代自然科学技术,以求在田野考古和后续的工作中,获取更多的研究古代社会的信息和资料。
2009年版《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的内容,就是上述新发展和新情况的具体体现。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研究的转型进展迅速,出现一系列新变化和新进展。
聚落考古-得到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者的理解、支持和实践。
区域系统调查,在全国各地迅速普及。并在实践中结合中国各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予以调整和完善。
考古发掘方面的变化更多,聚落考古方法和社会考古研究,体现在考古发掘的各个阶段和层面。可以获取有用信息和资料的所有手段,在田野考古发掘和后期研究中同等重要,所获资料均为考古学研究之基础。
在上述坚实的田野考古工作基础上,综合性的考古学研究得以向更为宽广的领域拓展。
篇5
【关键词】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五次年会;环渤海考古学研究;论文综述
2012年11月21日至25日,由中国考古学会主办,河北省文物局协办,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承办的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五次年会在石家庄市召开。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考古文博机构、高等院校等团体会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会成员,以及河北省各文博机构列席代表共23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王巍研究员主持,河北省人民政府特邀咨询孙士彬,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张忠培,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霁翔,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等出会开幕式,并分别致辞。大会共收到论文及摘要139篇,根据提交论文所涉及的历史时段及研究方向,与会代表分六个小组进行了学术研讨和交流。与会的专家学者本着百家争鸣、畅所欲言的精神,围绕大会主题“环渤海考古学研究和其他考古学问题”展开认真研讨,会议讨论气氛热烈,收获颇丰。现就本次年会的主要研究内容作简要综述。
一、环渤海考古学研究
中国考古学会年会是第一次在河北省召开,而以环渤海考古为主题的考古学会议,自1986年由苏秉琦提出以来,已先后在长岛、临淄、大连、石家庄、天津举行了五次,这是第六次召开。
(一)整个环渤海地区
甘才超在《环渤海地区旧石器考古及相关问题探讨》中,系统介绍了环渤海地区旧石器考古发现及研究状况,归纳出了这一区域内旧石器时代文化的一些阶段性特点,并探讨了该地区旧石器文化发展与自然环境演变的关系。周向永研究了环渤海背景下的辽北史前考古学文化变迁的历程。在《环渤海新石器考古学文化研究》一文中,霍东峰将环渤海沿岸地区划分为六个地理单元,把该地区新石器时代划分为三大阶段五期,构建了环渤海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从考古学文化、文化圈、文化系统三个不同的层次和角度,对该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研究做了一次较为全面的归纳和总结。段天在《夏时期环渤海地区文化互动的考古学观察》中,对环渤海地区夏时期诸考古学文化遗存进行了梳理,将其分成环渤海地区东部的泰沂山地、胶东与辽东半岛、环渤海地区东北部的下辽河平原与辽东丘陵北部、环渤海地区北部的燕山以南地区、环渤海西部和南部的华北平原等文化区域,揭示了各区域的文化结构和特征,并考察了各区域间的文化互动与交流。姚乐音的《试析渤海文化中的汉文化因素》一文,从史籍记载的思想意识形态、、社会习俗和考古资料,如都城形制、墓葬形制、陶器类型等方面,展现了渤海文化的多元化,重点探讨了渤海文化中的汉文化因素。王永波认真研究了黄、渤海两岸考古学文化与古族关系。
(二)燕赵地区
关于燕赵地区的考古文化研究。郭明在《燕山南麓筒形罐遗存初探》中,对燕山南北出土的筒形罐进行了梳理,认为燕山南北地区人群的交流方式存在差异,在较早阶段筒形罐特征的相似性是由于受到了来自北方地区持续影响的结果,而在相当于赵宝沟文化时期的第三期则表现出了燕山南北地区相互影响的态势,最终燕山南麓地区逐渐脱离了筒形罐文化区。在《冀南豫北地区龙山时代早期文化初探》中,乔登云对冀南豫北地区龙山时代早期文化遗存的考古发现及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探讨了该遗存的文化内涵与特点、文化源流及年代、文化命名等问题。张晓峥在《试论邯郸地区漳河型下七垣文化遗存》中,将邯郸地区漳河型下七垣文化遗存分为六段,合并为早、中、晚三期:早期遗存年代定在二里头文化二期至三期早段,中期遗存年代定在二里头文化三期晚段至四期早段,晚期遗存年代定在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至早商文化一期。徐海峰根据夏至早商时期遗存的文化面貌,以唐河为界,将冀中地区分为南、北二区,冀中北区夏时期存在下岳各庄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及大坨头文化,冀中南区以南马遗址为代表的遗存地处太行山东麓山前平原地带。石磊从燕的兴起与灭亡、构成燕文化的要素、燕文化的特征等方面,阐释了燕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和诸文化之间相互影响,不断发展,并逐渐融合为一个整体,形成更大的统一。张星德在《西寨遗址陶器再认识――兼谈赵宝沟文化起源》中,对西寨遗址出土的陶器进行了详细分期,探讨了其文化特征与赵宝沟文化早、晚期的对应关系,认为西寨遗址遗存属于赵宝沟文化,而赵宝沟文化是兴隆洼文化三期与磁山文化碰撞的结果。在《富河文化、小河沿文化、魏营子文化、凌河类型新考――关于辽西地区四种考古学文化遗存性质的再认识》中,赵宾福对辽西地区四种考古学文化遗存的性质提出了新认识:富河文化是赵宝沟文化分布在西拉木伦河以北的一个地方类型;小河沿文化与红山文化中晚期同时,并且是红山文化的平民遗存;魏营子文化是高台山文化晚期拓展到辽西地区的一个地方类型;凌河类型是双房文化拓展到辽西大小凌河流域的一个地方类型。赵晓刚在《新乐上层文化聚落形态初识》中,从对新乐上层文化遗址在分布和选址,聚落内部环壕、房址、墓葬、灰坑等遗迹形态和聚落布局等方面的分析,总结出了新乐上层文化聚落形态的一般特点,并对其中所反映出的人类行为或社会结构等进行了探讨。张翠敏在《论双砣子一期文化》中指出,小珠山三期文化与双砣子一期文化是深受山东龙山文化强烈影响的同一文化谱系下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主体均属于辽南土著文化系统,双砣子一期尚未进入青铜时代。贾笑冰以近年在辽东广鹿岛小珠山、吴家村和洪子东遗址的考古发现为基础,对辽东半岛的史前文化序列和谱系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朱乃诚根据之前的考古发现与反映红山文化文明化进程有关的一些考古学现象,探讨了辽西地区早期文明的特点及相关问题。杨建华在《夏家店上层文化与欧亚草原的远程交往》中,将图瓦阿尔然大墓与夏家店上层文化进行了比较,发现两者具有很多相似的文化因素,说明了它们可能通过技术转让或者文化认同的方式进行了远程交往,但它们的起源是各自独立的。洪猛的《浅析冀北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与玉皇庙文化的发展及其相关问题》,探析了以冀北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与玉皇庙文化发展为中心的区域文化演进、生业变化和族属等问题。在《昌平张营遗址与周邻早期青铜文化的交流》中,郭京宁对北京市昌平区张营遗址进行了文化因素分析,比较其与夏家店下层、朱开沟、岳石、下岳各庄、晋中、下七垣诸考古学文化与地区的联系,总结了张营遗址与外界交流的特点及原因。王嗣洲以辽东半岛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考古学文化现象为基础,分析了其文化发展的强弱态势和内在关系。肖景全、郑辰以抚顺地区的考古资料为中心,探讨了辽东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相关问题。
关于燕赵地区的遗址、城址研究。王法岗、谢飞在《泥河湾盆地泥河湾层中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指出,泥河湾盆地泥河湾层内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的石器工业可以归为石片石器的工业类型,属于中国北方以小石器为主的主工业类型,表现出很强的继承性,体现出区域渐进的特点。盛立双、王春雪在《天津地区旧石器材料及石器工业类型的初步研究――兼论与环渤海地区石器工业之间的关系》中,对天津地区旧石器材料及石器工业类型进行了研究,认为天津地区和泥河湾盆地、东北地区南部等环渤海地区在文化面貌上有着密切联系,同属于一个大的文化区,这种文化上的相似,应理解为类同,而非趋同,是某种文化特征在时空上连续分布所造成的传播迁徙。赵春青在《动态解读北福地一期聚落》中,探析了北福地一期聚落的布局、动态变化过程,认为北福地聚落开创了凝聚式、向心式聚落布局的先河。邢台市文物管理处介绍了邢台任县南宋村商周遗址的考古发掘情况。廊坊市文物管理处对廊坊地区史前遗存的发现与研究进行了梳理。张童心、王斌对河北元氏龙正遗址与汉常山郡(国)发掘所出器物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龙正遗址可能为常山郡(国)周边一处制陶作坊遗址。张守义结合考古调查资料及相关史料,对太子山在地理上的定位进行了考证。白瑞杰对丰宁境内辽金时期的古城址、遗址、墓葬、塔址等进行了研究。田淑华、白瑞杰对承德辽金元时期的重要窖藏做了概述及考证。陈山、刘明对辽阳、沈阳、抚顺境内的部分明代城址的规模、结构、功能和历史沿革进行了研究。田立坤在《金岭寺建筑址为“庙”说》中,对金岭寺建筑址的年代及性质进行了研究,认为它的年代上限当晚于龙城始建的341年,是礼制性建筑,为“慕容庙”。胡强对州的历史沿革及其官署遗址出土的建筑遗物进行了研究。刘子龙根据平泉会州城城址的现存遗迹、城内出土的文物和标本及附近的古遗迹情况,对其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进行了研究。徐文英对燕下都和灵寿故城的异同进行了细致比较,并分析了其形成原因。陈伟、雷建红的《论战国中山灵寿城的“市”》指出,《战国中山国灵寿城:1975~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中九号、十号夯土建筑遗迹的性质为“市”,并依据城址出土的相关遗物和遗迹,进一步探讨了灵寿城内“市”产生的原因。黄信在《论河北的宋元考古――陶瓷、城市、冶金》中,回顾了河北的陶瓷、城市及冶金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并对进一步开展研究提出了看法。田建文通过对柿子滩遗址与南庄头遗址进行细致比较,得出柿子滩遗址群可分三期的结论。
关于燕赵地区出土器物的研究。王继红在《玉皇庙文化青铜带钩研究》中,对玉皇庙文化的青铜带钩进行了分类及分型分式,并对其分布地域和分期断代进行了研究,从而总结出不同类别的几种主要型式的带钩在发展演变过程中的规律性特点,并就青铜带钩的起源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在《略论大凌河流域商周窖藏铜器的年代及相关问题》中,胡传耸考察了辽西大凌河流域的马厂沟、北洞村、山湾子、小波汰沟等地先后发现的六处商周时代的铜器窖藏,对这六处窖藏集中形成于西周前期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它们可能分别形成于商代后期、西周前期和西周中期等三个时期。秦进才对满城汉墓铜器铭文纪年进行了研究。相军在《京津冀地区两汉诸侯王墓随葬陶器和车马研究》中指出,西汉中期偏早阶段的仿铜陶礼器在陶器构成中占有重要地位,西汉中期早段全国尚未形成明确统一的车马随葬制度,至西汉晚期,车马随葬制度逐渐统一。刘成文、孟繁峰研究了井陉盘龙冶炉前押官周承遂妻李氏墓随葬的精美陶瓷器的具体出土地点、窑口、产地、特征、窑口性质、意义等,这对进一步认识井陉窑具有重要意义,且为唐与五代陶瓷器的形制演变和年代划分提供了重要依据。王蔚波的《北宋皇陵出土定窑白瓷及其相关问题》认为,北宋早期定窑就已发明了覆烧工艺。在《我国北方瓷器出现及相关问题的初步研究――以窑址为中心》中,王建保通过对临漳曹村窑和巩义白河窑等北方早期窑址的考察和初步研究,认识到北方青釉瓷器有自己的发展路径,而白釉瓷器则是沿着“化妆白瓷”和白胎白釉瓷器两个轨迹发展。韩维龙、冯永驱在《河南境内发现宋金元时期磁州窑系瓷器的考古学观察――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平顶山段考古发现为例》中,从种类、器形和装饰等方面,将河南境内已发现的属于磁州窑系的瓷器与河北观台磁州窑的瓷器进行了对比分析,探讨了宋金元时期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问题。
关于燕赵地区墓葬及相关问题的研究。韩立森在《赵王陵陵园规制初探》中,从陵区选择、陵园布局和形制、陵区的防御设施、陵园建筑和陵墓形制等方面,分析了赵王陵的陵园规制。成瑭重新审视了燕下都辛庄头30号墓的年代与性质问题,认为该墓葬的年代应该在战国晚期,墓主应该是与东北地区及朝鲜半岛有密切联系的燕国将领。滕铭予、张亮在《葫芦沟墓地的年代及相关问题》中指出,葫芦沟墓地的年代跨度大体上从春秋中期晚段到战国早期,墓主很可能是与同墓地其他墓葬以及玉皇庙文化其他墓地墓主人不同的人群,二者之间既有很紧密的联系,又有所区别。张瑞在《唐河北道南部地区隋唐纪年墓葬类型分析》中,从墓葬形制和神煞俑两个方面,对唐河北道南部地区隋唐纪年墓葬的类型进行了详细分析。郭济桥在《河北隆尧唐陵平面格局暨名称考略》中,介绍了河北隆尧唐陵的勘探成果,确定了其范围、布局。梅鹏云在《宣化辽代壁画墓乐舞“大曲”说辨析》中,分析和研究了宣化辽代壁画墓乐舞的情况,对“大曲”说表示质疑,并提出了新见解。在《试论大兴北程庄辽墓墓门建筑》中,于璞就北京大兴北程庄墓地中发现的辽代墓门仿木建筑进行了探讨,将墓门的建筑情况分为四型,提出墓门的结构、装饰与墓葬的年代有关,可能是建墓时所参考的现实中的建筑有所差异造成的。张林虎对2003―2004年石台子山城墓葬出土人骨进行了研究。
关于燕赵地区长城研究。李文龙在《河北北部战国燕北长城的调查与研究――兼论东周燕文化的北渐》中,对河北北部战国燕北长城的调查与研究进行了梳理,认为燕国北长城不是以“复线”的方式修筑了南北两条,而只有南面一条,北侧的“赤北长城”是秦代所修。郑立新梳理了河北明长城碑刻,重点从功能和形制上对其进行了分类。郑绍宗在《河北省古代长城综合研究》中,详细介绍了河北近年长城调查的情况,对明代之前的长城分布、走向以及长度、形制作了具体的介绍,特别是对长度的测量已十分精确。朱永刚探讨了燕秦汉长城与东北早期铁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关于燕赵地区动植物研究。罗运兵在《华北地区先秦时期鳄骨遗存解析》中,对鳄骨骸遗存进行了分类梳理,着重讨论了鼍类在华北的生态分布及其开发利用情况,特别是有关墓葬中出土的鳄皮制品,并对相关的古史传说(如豢龙、御龙)作了解析。高建强等在《中国家猪的起源驯化研究――来自磁山遗址古代猪遗存的信息》中,分析了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距今约7400年的7个古代猪遗存的考古学信息和线粒体DNA,推测黄河中游以北的河北磁山遗址和以南的河南贾湖遗址范围内,可能正是中国北方地区家猪的起源驯化中心。
(三)齐鲁地区
关于齐鲁地区考古文化的研究。刘延常、徐倩倩在《山东地区燕文化遗存分析》中,探讨了燕文化与齐鲁文化的关系。在《胶东地区周代地方文化遗存》中,王富强梳理了胶东地区周代地方文化遗存的聚落分布和特征,指出珍珠门文化晚期的一些遗址虽然发现了少量齐文化的绳纹陶器,但也只能看作是齐文化的影响所致,齐文化真正对东方的经营应该是从西周中期开始。
关于齐鲁地区遗址、城址研究。曹斌的《试论高青陈庄遗址的性质》讨论了该遗址的性质,认为是西周前期(武王至恭王)周公翦灭薄姑之后,将太公庶子封于此地坚守的边防要地。高明奎、郑同修则讨论了高青陈庄西周祭坛的性质,认为它是祭祀地的社坛,城址为齐国卿大夫级的城邑,故社坛可能为“置社”。方辉从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的地望、墓地延续时间入手,结合历史文献及海岱地区商末周初聚落形态的变迁,推断其属于商周时期的薛国遗存。在《营丘考疑――昌乐营陵城新探》中,魏成敏认为营陵故城不可能是太公所都之营丘,也不会是春秋时期杞国之都缘陵,营陵城营建于西汉早期,或为始建于西汉早期的营陵侯国之都城,或为北海郡所营建之郡城。
关于齐鲁地区的器物研究。陈雪香、方辉介绍了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的商代陶范,曹锦炎对齐侯子仲姜鬲进行了考证。
关于齐鲁地区的盐业考古。党浩在《齐国制盐业探析――从昌邑盐业调查看起》中,依据山东省昌邑市大规模的周代盐业遗址群的调查材料,对周代齐国的盐业发展状况作了细致分析。
关于齐鲁地区的动植物研究。宋艳波在《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出土鱼骨研究》中,运用动物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了山东新石器时代先民对鱼的使用情况。王芬在《即墨北阡遗址大汶口文化先民的食物结构考察》中,提出北阡先民主要采用渔业和农耕为主、狩猎或养殖为辅的生活方式。靳桂云、王海玉在《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稻作农业的植物考古证据》中,对距今5000年前后稻作农业才从长江流域传播到黄河流域这一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作为海岱地区核心地带的山东高地周围8000年前的遗址中已经有稻遗存出土。
二、其他考古学问题
本次年会除重点讨论环渤海地区考古研究成果外,也涉及我国其他地区考古学研究的诸多领域和方面。
考古文化研究。冯小波以湖北省郧县人遗址和广西百色盆地那赖遗址为例,总结了南方旧石器早期文化的特征。高峰、何林珊在《中国南方的新石器文化》中,对世界范围的人类起源和南方最早的新石器遗存进行了细致分析,认为西方提出的“中石器时代”应该摒弃,重新解读了“新石器时代”的概念,提出新石器起源于最后冰期最大值前后时期的中国南部和东南半岛的北部区域,为掌握和平工业技术的北部边缘人群,也即我们炎黄和百越民族的祖先的结论。何金龙探讨了哀牢国的发展历程,认为哀牢国在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中国境内存在过的唯一由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民族建立的古国。刘晓东认为,松花江上游的遗存主要有榆树老河深上层遗存、永吉杨屯三期遗存、永吉查理巴墓葬,贯穿了勿吉后期至渤海建国时期,存在鲜卑、高句丽、三种文化因素,进而对遗存中文化因素进行了分期研究,并讨论了这几处遗存在文化中的年代位置,及各分期与各发展阶段的对应关系。刘志岩梳理了金沙江下游地区新石器至汉代遗存,初步建立起了该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和时空框架。陈淑卿以大南沟、姜家梁、哈喇海沟墓地为例,对小河沿文化性别进行了研究,认为前人所谓的小河沿文化“社会生产男主女从、社会地位男高女低”的结论并不成立。陈祖军通过对曲贡遗址早期遗存出土的陶器在器物形态、类别等方面进行了比较,重新划分了器物类别与型式,结合器物出土层位关系、组合与型式演变趋势,认为曲贡文化可划分为二期三段。赵东升研究了商王朝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进取模式和统治策略,以及隐藏在背后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深层原因。
有关遗址、城址研究。王新金、陆永福、李文鑫通过对贵州省贞丰县鲁容乡洒若桥史前文化遗址所获材料进行器物分类、特征描述、对比分析,探讨了该遗址的文化特性。徐长青以靖安老虎墩考古发现为基础,推断老虎墩上层文化遗存可能是江西省一支新的古文化类型,距今约5000―4500年左右。林强对广西近年出土的一种极富特点的大石铲及相关遗址进行了介绍,并研究了其起源、原料选择、加工技术、文化性质等问题。何艳杰在《商代祭祀中“毁庙”遗迹假说――从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青铜构件谈起》中,对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建筑构件的实物形制、埋藏地点、废弃原因等进行了分析研究,提出此建筑构件应该是檐饰,是人为废弃的,废弃原因一是因为商代可能存在“毁庙制度”,另一原因是“九世之乱”中的人为毁庙。潘玲对内蒙古、山西和吉林境内八个与鲜卑相关的遗存年代进行了探讨。魏坚、张晓玮从古城形制和建筑规模入手,对比居延地区调查测绘的汉代边城考古成果,认为该城始建于汉代,并是汉代这一地区最早的行政建制,魏晋以后沿用。何继英对上海志丹苑发掘的元代水闸进行了细致研究,梳理了文献资料,对建筑工艺以及成就形成了结论。王元林对东亚早期建筑文化的传播和发展进行了考古学考察。楼建龙对福州城市考古进行了综述。王志刚重新审视了国内城的年代问题,认为城的始建年代应不早于4世纪。孟华平探讨了石家河古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以及原因。王育龙对西汉时期的儋耳郡城与珠崖郡城城址的研究情况进行了综述,讨论了两郡郡治尤其是珠崖郡治的具置。田亚岐从考古学视角分析了秦九“都邑”所显现出的不同功能所形成的层次结构,提出它们分别是秦都城、秦城与秦邑三类。戴向明介绍了山西绛县周家庄遗址近年发掘的主要收获。惠夕平介绍了荥阳官庄遗址2011―2012年的重要发现。何国俊就海南昌化江流域史前遗存考古调查的初步收获做了简述。高大伦介绍了米仓道考古探险调查的主要收获。
出土器物研究。崔兆年对青海史前文化的玉石器进行了探讨。李新全通过对神树纹瓦当造型与纹样的研究,揭示了天圆地方、两极、统一等思想,并指出其源头在古蜀国,而不是燕国。宫希成介绍了安徽出土的5件铜铙,对它们的年代即“最早为商代,最晚为春秋”提出了质疑,认为应是商代晚期,并探讨了铜铙的功能,认为小铙是用来演奏旋律的,大铙是用于祭祀山川、湖泊、风雨、雷电、星辰之神器。聂菲对湖南地区楚墓所出漆器进行了全面梳理,在对楚漆器进行分区与分期的基础上,对各区漆器的特点、区域内漆器所反映的文化特征进行了探讨。霍巍在《试论考古发现的早期金属器和“早期金属时代”》中,对近年来考古出土的早期金属器进行了考古学的年代学、类型学分析,认为从进入金属器产生和流行的时代、金属工艺的表现形式、金属器所反映出的文化特征等各个方面,都与周边地区大体上同步或仅仅稍晚,其间并不存在巨大的落差。梅建军探讨了我国北方系青铜器科学价值的意义,并提出了新看法。闫介绍了长宁遗址出土的细石器,比较了它与青海史前细石器之间的异同,认为长宁遗址出土的细石器归属于华北细石器传统的延续,青海齐家文化的细石器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和甘肃武威皇娘娘台等齐家文化的细石器工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可能代表了青海齐家文化的地域特点。韩金秋在《从靴形器看骑马术在北方地带的出现和扩展》中,对1978年山西省柳林高红墓葬出土的铜靴形器进行了研究,揭示出高腰皮靴的兴起与北方地带传统的低腰皮靴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与骑马术在北方地带的兴起有密切关系;高红靴形器的出现与商周之际北方民族游动性增强的趋势相符,以高红墓葬为代表的人群可能直接导致了此后骑马术在北方地带的扩展;靴形器在中原的出现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影响的直接反映。黄锦前在《说“盏盂”――兼论楚系盏盂的形态与功能》中,从文字和器形两方面加以考察,认为作为器物自名的、等字,应释作“盂”,进而主要据楚系有自名的盏的有关材料,从器物形制、自名及古书的相关记载等方面作了综合分析,认为盏与鼎、盆及盂等器类之间有着很密切的亲缘关系,盏虽系楚系铜器中所特有的器类,但其部分类型明显受同时期中原文化的影响,在礼器中的功用与地位大致与敦、相当。院文清对仿铜漆礼器的类别、造型、组合、性质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胡金华在对已发现的西汉黄金货币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西汉麟形象的考证,重新对《汉书・武帝纪》中记载的西汉麟趾金进行了辨析。魏曙光在《汉代出土陶圆炉的发现与研究》中,对汉代黄河中下游地区出土的陶圆炉进行了梳理,认为陶圆炉的时空分布特点的形成是有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原因的,同时其时空分布的变化是与汉代气候的变化相适应的,是人们适应气候变化的产物。梁志龙根据带扣外部扣环的形状,结合扣舌的形制、位置及安装工艺等的不同特征,将高句丽带扣划分为四种类型。丘刚依据海南岛的出土文物,研究了南海海上丝绸之路。陈杰、夏浙新从考古实证与文献资料两方面,对历史时期琮的意义进行了细致研究,认为琮在传播的过程中虽然逐渐丧失了良渚文化时期原有的宗教观念,但是作为玉礼器之一,却被历史时期的文献典籍不断强化,成为中国玉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文化元素。林强、何安益根据历年调查、发掘、研究的相关成果,从广西永福窑田岭窑址青瓷器所体现的工艺特征角度考察,尝试梳理该窑址的青瓷器技术发展脉络,认为窑田岭窑址不应完全归入耀州窑系。
墓葬及相关问题研究。蒋志龙分析了云南江川李家山墓地的结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石寨山文化的社会结构。史党社探究了马家塬战国墓地发掘的意义。丁岩以咸阳原战国秦陵园布局模式为例,认为王后合葬、妃子葬的形式是秦陵园布局模式的新发展,汉承秦制,西汉也实行帝后并穴合葬、妃子葬的陵园布局形式。孙伟刚从建筑结构、特点及管理等方面论述了秦汉帝陵寝园,认为秦汉帝陵的寝园开始于秦始皇帝陵,秦始皇帝陵封土北侧西部的陵寝建筑遗址为秦汉帝陵寝园的雏形,为秦汉帝陵中结构最复杂、形制最完善的寝园建筑,并奠定了汉代及以后各朝代帝陵寝园的形制结构。申茂盛通过对秦陵地区考古资料的梳理、整合,认为在秦始皇帝陵园考古中必须建立起陵区、陵兆域、陵园、帝陵园的概念,明晰它们各自的范围,理清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秦始皇陵应该是四墓道的“亚”字形大墓。田正标对浙江先秦墓葬的形制变迁与越国墓葬制度的形成进行了分析。梁云对泾河上游西周时期的殷遗民墓葬进行了系统研究,指出这些墓葬的年代集中在西周早中期,墓主人的身份应是为周王朝戍守北疆的武士或周王朝直属部队的军事将领,墓地的分布大致反映了王朝戍边部队的驻地范围。郎旭峰、杨金东从土墩墓的形制与结构、随葬品组合及其演变规律、墓葬叠压打破关系等方面,探讨了杭州萧山柴岭山、蜈蚣山土墩墓群的分期和年代,认为这批墓葬可分为七期,年代从商代中晚期延续到春秋末至战国初期。李东通过对自己发掘的扶余明墓的整理研究,对以往所谓的“至正”款玉彩瓷器的年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修正了将其认作元代器的观点,认为岱吉屯、欢迎砖厂墓地和扶余油田砖厂墓地均为明代中晚期的墓地。吴松岩通过对内蒙古中部早期鲜卑墓葬的形制、葬俗、随葬品以及文化因素的分析,并结合相关文献的记载,认为这些墓葬是拓跋鲜卑联盟时期的遗存,即以拓跋鲜卑为主体,同时包含匈奴、乌丸等其他民族在内的联盟组织,年代应该在3世纪中叶至4世纪末。吴荭对河西魏晋墓葬的照墙进行了比较研究,探索了其墓葬特征及年代。赵永军在《金墓中所见墓主人图像释析》中,对金墓中以壁画、石刻等方式体现的墓主形象题材进行了排比、分析,认为对墓主人进行供养,是这类墓主人图所折射出的基本主旨和内涵。王会民、马冬青提出在中国古代夫妻墓葬中,由于男女各方面差异的存在和“男尊女卑”等观念的影响,埋葬时的相对位置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展现出不尽相同的特点,主要经历了一个从葬位尊卑不明显到右尊主流再发展到左尊主流的漫长、曲折的历史过程。
篇6
关于挹娄文化遗存的认识
《三国志》、《后汉书》有挹娄传,对挹娄人活动地域有所记载,两书内容基本相同,说挹娄在夫余东北千余里,东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及。目前的考古学研究,对夫余和沃沮文化遗存进行了比较可信的辨识。泡子沿晚期、老河深二期、大架山上层代表的夫余遗存的分布,北界可到黑龙江宾县一带,东至张广才岭,团结下层、新安闾下层、一松亭代表的沃沮遗存分布北界可抵穆棱、林口一带。依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可推断挹娄人活动区域大致在张广才岭以东、穆棱河以北,东滨大海的广大范围内。目前这一地区发现的两汉时期古代遗存面貌并不一致,分属多个考古学文化类型,主要有滚兔岭文化、东兴文化、东康类型、桥南文化、波尔采—蜿蜒河文化(图一)。滚兔岭文化以双鸭山市滚兔岭遗址为代表④,大体分布在北至松花江,西到锅盔山,南抵穆棱河,东至乌苏里江、完达山一线的区域内。文化面貌以角状把手罐为特色,陶器有罐、壶、碗、钵、杯等,皆为夹砂陶,呈红褐、灰褐色等,少量为红衣陶。素面为主,极少量有附加堆纹、凸弦纹等。皆为手制,器壁厚薄不均。石器较少。有罐、壶、碗、钵、杯等陶器,刀、镞、刮削器、磨盘、磨棒等石器,刀、凿、镞、甲片等铁器,房址为圆角方形的半地穴式。
东兴文化分布范围较小,在牡丹江中下游地区,以海林市东兴遗址⑤为典型代表。该文化以大口小底深腹罐、敛口鼓腹罐为特色器物,陶器器纽发达,且柱状、角状并存,应是与滚兔岭文化和团结文化有较多交流,受到二者较深刻的影响。陶器有罐、瓮、甑、壶、碗、钵、杯、盆等,以夹砂陶为主,少量泥质陶,呈灰褐、红褐、黑褐、黑色等。多素面,少量有附加堆纹、划纹、压印纹和乳丁纹。均手制,多采用泥条套接法。石器有斧、刮削器、镞、磨盘、磨棒,铁器有刀、凿、镞、等。房址为方形或长方形半地穴式。东康类型分布在牡丹江中游一带,以宁安市东康遗址⑥为代表。陶器有瓮、罐、钵、碗、豆、壶、杯等。陶质有夹砂和泥质两种,呈红褐、黄褐、黑褐色等。火候较低,陶质疏松,均为手制。素面为主,有纹饰器物极少。石器有斧、锛、凿、刀、镰、铲、磨盘、磨棒等,其他还有骨、角、蚌、牙器。东康遗址还出土3件铁器。房址均为半地穴式建筑。桥南文化遗存,目前仅发现位于依兰县城南牡丹江右岸二级阶地上的桥南遗址⑦一处。遗存分早晚两期,但时代相距较近且有明显的继承关系。文化面貌以小底饰多条凸弦纹的瓮、罐和发达精致的骨制品为特色,陶器有瓮、罐、壶、盆、钵,质地以夹砂为主,少量泥质,呈黄褐、灰褐、黑褐色,还有红衣陶。纹饰有凸弦纹、指压纹、附加堆纹、划纹等。骨器有锥、针、镞、锄形器、鱼镖及一些饰品。二期遗存相较一期出现一些新器型,如带齿状附加堆纹口沿的陶罐、带角状把手的单耳罐、骨制回旋鱼镖等,同时二期遗存中出现铁器,有刀、凿、鱼钩等。房址均为方形或长方形半地穴式。波尔采—蜿蜒河文化以俄罗斯的黄陡崖、波尔采遗址⑧和我国绥滨县蜿蜒河遗址⑨为代表,分布在黑龙江中下游沿岸直达入海口,向南达到俄罗斯滨海地区,在我国境内最南可至友谊县境。这类遗存分3期,各期间有承袭关系。文化面貌以球腹喇叭口罐为典型特色,陶器多纹饰,有球腹罐、敞口短颈高体罐、敞口斜壁碗、浅腹椭圆形陶杯、角状单把罐等,纹饰以方格纹、弦纹、附加堆纹、篦纹、细绳纹最常见。其他器类有石、骨、铁、铜等。房址为方形或长方形半地穴式,其内为木结构。
《三国志•东夷传》载:“东夷饮食类皆用俎豆,唯挹娄不,法俗最无纲纪也。”《后汉书•东夷列传》也载:“东夷夫余饮食类皆用俎豆,唯挹娄独无,法俗最无纲纪者也。”这是最利于辨识挹娄遗存的史料。上述五种考古文化类型中,东康类型是有豆文化,可以认为不是挹娄遗存。其余四种文化都无豆。桥南文化只发现一处遗址,其文化性质有待进一步的确认,且其年代似乎也比其他几种文化略早,研究表明它的存续年代约在战国至西汉,从这个角度讲,它是挹娄遗存的可能性很小。东兴文化与滚兔岭文化和团结文化都有较多交流,从其无豆、室内无烟道等特点及陶器的整体形态看,应与滚兔岭文化有更近的亲缘关系。滚兔岭文化符合“在夫余东北千里、南与北沃沮接、无豆”的条件,但这一文化遗存的分布却未能到达滨海地区。波尔采—蜿蜒河文化符合“在夫余东北千里、东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无豆”的条件。综合上述的分析,波尔采—蜿蜒河文化应该是最符合挹娄遗存标准的,但“东夷饮食类皆用俎豆,唯挹娄不”是否应该这样解读,“东夷民族饮食都用豆,只有挹娄没有”。这样,东兴文化和滚兔岭文化虽然每一个都不能完全符合文献对挹娄记载的条件,但如果将它们与波尔采—蜿蜒河文化放到一个大的系统中考虑,则完全可以认为它们也是文献中所称“挹娄”的文化遗存。“在夫余东北千余里,东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及”。从《三国志》的这条记载看,作者是本着严肃的态度对历史进行记录的,“其北未知所及”说明不知道的东西没有记,也可以证明“在夫余东北千余里,东滨大海”、“东夷饮食类皆用俎豆,唯挹娄不”等记载是可信的。有学者注意到,七星河流域汉魏遗址群的要塞遗址或设置在扼守七星河水道的七星河两岸,或设置在防范松花江流域的北侧,推断当时地处松花江南、北岸的居民之间矛盾尖锐,且因此处松花江两岸文化遗存面貌有较大差异,而认为波尔采—蜿蜒河文化不能与滚兔岭文化同为挹娄遗存。其实并不能因此时松花江南北两岸的对峙的局面而给二者是否同族下结论,正如不能因靺鞨时期粟末、黑水两大集团的对抗而否认二者同族同源的关系。同一民族的文化遗存是可能包含不同考古学文化的。因此笔者认为,即使事实上分属不同的民族,文献中所称“挹娄”的遗存至少应该包含波尔采—蜿蜒河、滚兔岭、东兴这三个考古学文化。亦即在古代历史记录者的认识中,留下上述三种考古学遗存的人群都是挹娄人。
靺鞨文化遗存
《旧唐书•北狄传》载:“靺鞨,盖肃慎之地,后魏谓之勿吉,在京师东北六千余里。东至于海,西接突厥,南界高丽,北邻室韦。”靺鞨,在晋到南北朝时期称勿吉,南北朝后期到隋唐时称靺鞨。二者本是同族,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称谓,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北史•勿吉传》对勿吉七部及勿吉的风俗记载大体与《隋书•靺鞨传》相同看出来,虽然《北史》有从《隋书》取材的可能,但这也证明了在唐朝人的认知中,勿吉与靺鞨是同族。开元二年,唐鸿胪卿崔忻出使渤海册封大祚荣,归途中于旅顺黄金山凿井立碑记事,碑文为“敕持节宣劳靺羯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有学者从音韵学的角度考证“靺”应从“未”声,“靺羯”应读“未羯”,与“勿吉”是音转关系⑩,这也可作为二者为同一民族不同时期称谓的一个证据。《北史•卷第一•魏本纪第一》载:“平文皇帝讳郁律,资质雄壮,甚有威略。元年,岁在丁丑。二年,刘武据朔方,来侵西部,帝大破之。西兼乌孙故地,东吞勿吉以西,控弦上马将百万。”北魏平文皇帝二年,正值公元317年,说明最晚在公元317年之前,已有勿吉的称谓了。依据文献考察,勿吉—靺鞨的发展大致可划分为3个阶段。一为勿吉早期阶段,此时勿吉在高丽之北,夫余东北;二为勿吉南下阶段,在此时期形成了勿吉七部,占领了原属夫余的第二松花江流域,最南已抵长白山一带;三为靺鞨阶段,靺鞨之名最早出现的年代为《北齐书》记载的武成帝河清二年(公元563年),“是岁,室韦、库莫奚、靺鞨、契丹并遣使朝贡”。由于文献对勿吉、靺鞨有了较多的记载,且对靺鞨的社会组织结构及各部族的分布进行了描述,这也让研究者对靺鞨活动的地域有了较为清楚的了解。目前靺鞨文化分布区内发现分布最广泛的魏晋隋唐时期考古学文化为以绥滨同仁一期瑏瑡为代表的包括绥滨四十连遗址瑏瑢、特罗伊茨基墓地瑏瑣等一大批遗存,被称为同仁一期文化。这类遗存分布在除三江平原以外的南至长白山,西到九台、哈尔滨一线,北到黑龙江两岸,东濒大海的地域内。此类遗存以一种侈口鼓腹,口下饰齿状花边或重唇的陶罐为典型特色,陶器夹砂、泥质均有,手制、轮制并存,陶罐肩部往往饰有篦点纹、凸弦纹、水波纹,有的在颈、腹饰拍印的方格纹,陶器种类主要为罐,其他还有碗、斜口器等。遗存中出现了较多的铁制品,主要有刀、矛、镞、甲片、马具及斧、锛之类的生产工具。遗存中还有少量石器的存在,主要是石镞、砺石等物,遗存中还有数量较多的青铜带具、牌饰和玛瑙、料珠等饰品。房址一般为方形或长方形半地穴式,有的四壁有木制结构。墓葬多为土坑墓。过去的研究将这类遗存识别为靺鞨遗存,学界基本达成共识。除同仁一期文化外,靺鞨文化分布区内还存在三江平原地区以凤林晚期遗存瑏瑤为代表的凤林文化、牡丹江中游地区河口三期、振兴三期瑏瑥为代表的河口遗存等年代相当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图二)。
凤林文化陶器有瓮、罐、壶、碗、钵、豆、盆、杯、盅、器盖、纺轮、网坠等。以夹砂陶为主,次为泥质陶,还有少量红衣陶和黑皮陶。均为手制,多为套接而成。素面为主,纹饰主要有拍印纹、戳印纹、刻划纹、按压纹等,有的钵器表饰有黑色彩绘图案。部分器物有器耳,器耳有圆柱状、角状、乳丁状等。少量器物有圈足或假圈足。另外还有陶制的猪、马等动物形象。石器有刀、凿、磨盘、磨棒等。骨角器较多,主要为生产工具和装饰品。出土较多牛、羊肩胛骨制成的卜骨,上有较多明显的灼痕。有一定数量的铁器和铜器。房址有两种形制,一种为设曲尺形火炕的房址,另一种则无火炕,但其灶的形制结构复杂多样。部分房址沿穴壁内侧亦有一周用于竖立木板的浅槽。河口遗存目前仅见于莲花水库淹没区这一狭小的范围内。该类遗存盛行乳丁状纽为主要特色,陶器以大型筒形罐和缸居多,且口部多呈椭圆形,其他还有碗、杯、盅、舟形器、网坠、轮等。以夹砂红褐陶、灰褐陶为主,泥质次之,还有少量的黑褐陶和灰陶,一些陶胎内掺有滑石粉。陶器手制为主,少量采用轮制技术。陶器多为素面,有极少量附加堆纹。骨角器较发达,石器和铁器较少。房址为方形或长方形半地穴式。在河口、振兴的遗址中,河口遗存直接叠压或打破东兴文化的遗迹;但从陶器群看,河口遗存与东兴文化却没有明显的承袭关系,反而和东康类型在陶器组合和主要风格方面更为接近,都以带乳丁状纽的深腹筒形罐、瓮为主要器物。河口遗存应该是东康类型向北扩张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新的文化类型。同仁一期文化从文化面貌上看,与波尔采—蜿蜒河文化有较多的联系,一般认为是由波尔采—蜿蜒河文化发展而来,由于目前考古发现的限制,二者之间尚存在缺环,缺乏直接连系的纽带。但二者之间存在谱系关系,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凤林文化是在滚兔岭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周边地区的团结和波尔采—蜿蜒河文化因素发展而成的新的文化类型,这一点已有学者作了可信的分析和论述瑏瑦。
河口遗存在文化谱系上与东康类型存在承袭关系,可以排除在挹娄—靺鞨系统之外,在年代上大致相当于魏晋时期,与勿吉—靺鞨发展的早期勿吉阶段大体相当。《北史•勿吉传》载:“其傍有大莫卢国、覆钟国、莫多回国、库娄国、素和国、具弗伏国、匹黎尔国、拔大何国、郁羽陵国、库伏真国、鲁娄国、羽真侯国,前后各遣使朝献。”在勿吉—靺鞨的这一发展阶段,勿吉附近还存在这样12个非挹娄—靺鞨族系的国或族,河口遗存或与其中之一存在对应关系。同仁一期文化年代跨度较大,碳-14年代测定数据表明,最早的绥滨四十连遗址为公元前140±80年,最晚的特罗伊茨基墓地为公元1150±110年,其余数据大多在公元300~700之间,考虑到碳-14数据的误差,一般认为此类遗存的年代在公元前后至公元1000年左右。这类遗存的上限至少可到东汉时期,下限达到唐代。同仁一期文化经历了勿吉—靺鞨的发展阶段。凤林文化一般认为属魏晋时期遗存,也相当于勿吉—靺鞨发展的早期勿吉阶段,但从目前掌握的考古材料看,在凤林文化的分布区内,凤林文化之后,只存在少量的金代遗存,未发现靺鞨和渤海时期的遗存。这样是否可以考虑凤林文化以同样的文化面貌在靺鞨时期继续存在过一段时间呢,虽证据尚不充分,但凤林城址中出土的带齿状花边的侈口鼓腹罐还是留下了思考的线索。此型罐明显带有同仁一期文化类型陶器的风格,说明凤林文化与同仁一期文化可能存在交流。此罐在形态上与桦林石场沟、海林羊草沟、二道河子等墓葬出土的同类罐较为接近(图三)。乔梁先生对同仁一期文化的陶器进行过研究,将之划分为4期9段,并根据测定的碳-14年代数据、器物类型演变以及相关历史事件对各段遗存作了年代学的讨论,文中认为桦林石场沟遗存的年代大体在唐代的中晚期(凤林文化发表了一组碳-14数据,ZK—2842校正后年代为公元425~635年;ZK—2843校正后年代为公元714~1012年;ZK—2844校正后年代为公元261~441年;ZK—2845校正后年代为公元257~439年;ZK—2846校正后年代为公元437~641年;ZK—2847校正后年代为公元251~441年)。也表明了凤林文化下限存在进入隋唐时期的可能性。通过前面的总结分析可以看出,在挹娄—靺鞨发展中,大体以牡丹江、松花江下游段、松花江汇入之后的黑龙江中段及乌苏里江为界,存在两个不同谱系的考古学文化,牡丹江以西、松花江、黑龙江北岸、乌苏里江以东的区域为波尔采—蜿蜒河—同仁一期一系的考古学文化,牡丹江以东、松花江、黑龙江南岸乌苏里江以西的三江平原地带为滚兔岭—凤林一系的考古学文化。这两系文化应该皆属于文献中所称的“挹娄”、“靺鞨”的文化遗存。《隋书•靺鞨传》载:“自拂涅以东,矢皆石镞,即古之肃慎氏也。”也暗示着以拂涅为分界,东西两个区域存在着不同的考古学文化系统。
篇7
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联合举办,广西博物馆、广西民族博物馆、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广西民族研究所等单位联合承办的“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暨百越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12月9~13日在广西南宁举行。本次年会是继1981年在桂林举办的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二届年会后16年,在广西的考古学、民族学调查研究取得一系列重大收获的背景下,再次回到西瓯、骆越故地广西。来自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海南、湖北等十多个省(市、区)和香港、台湾等地,以及美国、越南等国家的92名专家、学者与会,除了会前收到论文中精选50篇编辑成67万余字的论文集《百越研究》(第一辑),由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10月正式出版外,会议期间还有十多位境内外的学者向大会提交了精彩的民族考古调查研究新发现。老、中、青三代学者共聚一堂,缅怀百越先民,重温东南历史,大兴学术争鸣。这些成果既有百越民族文化的总体研究,更多的是百越各支系文化的深入探讨,还有百越民族与其他系统民族文化关系、百越与当代华南民族文化关系的探讨等专题,将百越民族史的学术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
一、百越民族的总体或跨地域研究
近10篇论文是从全局或跨地域的角度对华南、东南百越文化的总体研究,不乏创新之作。如江瑜在《古代铜鼓社会功用再考察》中,认为古代铜鼓上的太阳纹和青蛙装饰,并不代表对太阳神和青蛙的崇拜,太阳纹的作用是分散铜鼓受敲击的力度和传播的声音的,青蛙是人们对农业丰收的向往,是人们对自身居住环境的观察思考,而且不同时空的铜鼓涵义、功能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很有新意。周幼涛《论地域文化视野中的越文化研究》主张百越虽支系繁多,但又存在四个相对集中的地域文化系统,即江浙地区句吴、于越所在的“北系”,闽台地区东瓯、闽越所在的“东系”,两广地区杨越、西瓯、骆越等所在的“南系”,云贵地区夜郎、滇所在的“西系”,体现了对百越文化谱系结构的深入思考。钟《吴越水乡地域古城形态之“夹城作河”构造初探――东南百越地域原生文化型式探索之一叶》,从淹城、苏州、绍兴、嘉定等城市平面中外濠、内堑两重河道的“夹城作河”构造,不同于中原城市规划传统,是百越水乡原生态的筑城形式。黄启臣《先秦岭南古越族土邦小国的社会性质》一文,全面钩沉历史文献记载中存在于岭南地区的骧头国、缚娄国、阳禹国、儋耳国、雕题国、西呕国、骆越国、伯虑国、苍梧国等九个土邦小国社会,主张它们多是生产力水平低下、国多无君的部落社会。Barry Rolett在《中国东南与南岛语族航海术的出现》一文中,认为东南史前航海术的出现、史前人类移民太平洋的主要原因,是全新世中期的海平面上升、沿海农耕地的较少所致。此外,高蒙河在《百越民族考古遗存考辨》、吴春明《东南汉民人文的百越文化基础》、陈山漫《吴越竹文化述论》、盘立《百越文化区域中的“道缘”文化》等文也都有类似的全局角度。
二、百越各支系文化的调查与探索
西瓯、骆越、夜郎、滇、南越、闽越、东瓯、于越、句吴、干越等百越各支系的民族文化与考古发现、研究,占本次年会提交论文的半壁江山,其中西瓯、骆越及相关的广西考古研究自然是重头戏,有不少新的观点。
在西瓯、骆越的关系与性质上,覃圣敏《西瓯骆越新考》系统回顾西瓯骆越研究中“同支说”、“异支说”之学术史的基础上,主张两说没有矛盾,先秦时期两族各自独立,秦汉时期结成联盟,他还把武鸣马头作为骆越古都、瓯骆联盟的中心,把越南河内的“古螺城”作为败退南迁的新都。蓝日勇的《骆越无国论》则从历史文献记载、元龙坡和安等秧山等墓地所反映的社会状况、城防设施的缺乏等角度,论证骆越族还没有建立起国家组织。
在西瓯、骆越的文化方面,蒋廷瑜《西瓯骆越青铜文化比较研究》首次以青铜器资料为据,系统论述“西瓯文化”、“骆越文化”的内涵特征、两支青铜文化的异同,反映了广西青铜文化研究的新高度。李珍在《贝丘、大石铲、岩洞葬――南宁及其附近地区先秦骆越文化的变迁》研究中,主张8000~5500年前的贝丘遗址、起于5000年前左右的大石铲文化、起源4300年前左右的岩洞葬-文化,是一个文化系统的不同阶段,是骆越人文化的三个阶段。陈远璋、熊昭明《广西贺县河东高寨四号墓及其文化因素分析》则运用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分析了河东高寨四号墓所出的陶器、铜器、玉器等所反映的秦、中原、越等文化因素组合。梁旭达《广西瓯骆文化浅析》系统描述了骆越的大石铲、稻作、干栏建筑、铜鼓文化、图腾崇拜等文化内涵。此外,谢日万、何安益《桂南大石铲应是骆越先民的文化遗存》、韦江、杨清平《广西武鸣河流域先秦墓葬的初步研究》、林强《广西都安北大岭遗址出土的玉器及其族属的初步探讨》也就考古资料中骆越的大石铲、墓葬、玉器等文化分别展开论述。
在西瓯、骆越的社会习俗与经济上,覃芳《广西新石器时代葬制与古越族食人埋骨的关系》则根据广西新石器时代屈肢葬、二次葬、肢解葬中的资料,结合文献与民族复原古越人的食人埋骨习俗。彭书琳《广西古代拨牙风俗》则收集研究了广西岩洞葬的人骨标本,分析了起源商周时期、盛于宋元明清时期的广西古代拔牙习俗的源流、分布与性质。陈桂芬《秦汉时期瓯骆社会经济发展述论》一文,阐述了文献记载的秦始皇统一岭南后,瓯骆道路建设、郡县设置、军人与移民实边、城市与商贸发展等。杨清平《略论东周时期岭南越人的农业经济》则更多从考古出土实物来说明类似的课题。
此外,也有一批论文涉及百越的其他支系。彭长林《滇文化族属再探》运用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深刻分析了滇文化中濮、越、氐羌三大因素的构成,是迄今研究云贵高原越文化最深入、清晰的成果。郑超雄《夜郎国的文化渊源及社会文明》一文,也以考古材料出发,分析夜郎国的文化渊源,主张濮就是越,并研究了夜郎的王权政治与社会文明。邱立诚《香港早期历史――百越族群中的地缘与文化关系》,分析了上起万年前后的打制石器时代,下迄秦汉南越与南海郡时期,香港考古文化与珠江三角洲的同源一体关系。蒋炳钊在《闽越的都城与“冶”》中,论证了史、汉所记闽越“二王二都”分别在崇安汉城和福州北郊汉城,而余善所都崇安汉城就是无诸王城“冶”。是闽越都城研究中的一个新看法。王炜在《试析虎林山遗址的文明因素》一文中,依据虎林山墓地出现的高等级墓葬、牙璋礼器、戈、矛武器、刻划符号等,分析外力作用下的闽南早期文明进程。陆建芳在《江苏无锡鸿山越国大墓发现的玉器》中,介绍了吴国地域范围发现的越国大墓玉器内涵。
陈元甫《汉代东瓯国的发现与研究》则介绍了浙南温岭塘山大墓及大溪古城的考古新发现,主张大溪古城就是东瓯国都。徐长青在《江西靖安县李洲坳东周墓葬》中,首次披露了这座重要的干越墓葬的考古新发现。张崇根《台湾大坌坑文化来源初探》则提出了台湾大坌坑文化来源于黄河流域大汶口文化的新看法。连照美在《从考古学论古代百越时空分布上的台湾》,在总结台湾史前文化与大陆关系之研究史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台湾新石器文化谱系中东南沿海的卑南文化内涵及其与大陆史前文化的异同关系。
三、百越民族与周边民族的文化关系
楚越关系历来是百越民族周邻文化关系研究的重要方面,朱燕英的《楚文化对江南百越文化的影响和融合》一文,运用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方法,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楚文化对湘资流域杨越、长江下游吴越、赣鄱流域干越、闽江流域闽越、岭南的南越与瓯骆等百越文化的影响。丁兰《纪南城周边楚墓地出土青铜越式鼎现象初探》则谈到了越文化融入楚文化、成为楚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考古证据。此外,石奕龙《两周时期句吴与邻族的经济、文化联系》,则从传世文献、铜器铭文、考古器物的角度,分析了句吴与邻族的产品交换、技术交流与文化互动关系。熊传善《论中原民族与南方民族的战争与融合》依据文献记载,比较全面描述了五帝、三代、秦、汉时期中原王朝与南方民族间的和战关系。漆招进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洞庭湖农业文化的南传》中,分析了湖南洞庭湖地区稻作农业文化通过越城岭山区及湘桂谷地传播到广西地区的考古证据。
也有学者分析了百越文化的跨界(国)关系,如蒋远金在《史前日本列岛与百越先民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考古学观察》一文中,提出新本列岛的旧石器、细石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与农耕源于华南百越地区的看法,从而证明两地的海洋文化交流。西村昌也《从民族史的观点来理解越南北部的铜鼓》比较全面地分析了越南北部出土铜鼓的类型、年代与使用民族,并分析这些现象背后的民族间战争、馈赠、交易等民族关系史问题。邓聪在《岭南与北越弓形格铜剑文化圈》中,提出了弓形格青铜剑的时空分布所反映的岭南地区与越南北部的先秦汉初文化交流。
四、百越后裔及现代南方族群的文化变迁
现代南方壮侗语族、苗瑶语族、南方汉人族群是百越的后裔或与百越源流关系密切的族群,是百越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冯孟钦在《广东俚人遗存的考古学观察》中,以洛湛铁路沿线、高州、信宜、电白、廉江、遂溪、海南等地墓葬考古资料为据,讨论东汉至唐代广东、海南的越人后裔――俚人的陶器、铁器、铜鼓、居址、墓葬等文化内涵。王献军在《黎族早期的物质文化》中,通过考古与文献资料,论述了黎族的食物形态与饮食器具,服饰、耳饰与文身文化,船形脚屋等居室文化的内涵与特点。李勃《黎族来源新探》、王逍《畲族传统文化禀赋述论――兼论畲族经济转型》,董建辉、林宏杰《族群认同与民族身份的确认――以金竹畲族乡的成立为例》,也属于类似的研究。
蛋民形成也与古代百越民族的海洋文化活动有关。黄向春在《福建闽江口“蛋民”研究――兼论百越民族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中,阐述了闽江口越人后裔蛋民的分布、姓氏、生态与生计、习俗与社会组织、神灵庙宇、口传记忆等,并提出闽越物质文化的民族考古学研究与蛋民认同“闽越”的符号意义之认知考古学研究同等重要。兰达居在《百越海洋人文与福建区域人文模式》一文,在论述百越海洋文化内涵的基础上,综合了两广、福建、浙江、海南、台湾等沿海作为百越海洋人文传承者的水上蛋民文化,并提出福建百越海洋人文在当代传承的三种模式――福州模式、湄洲模式、惠东模式。
此外,还有学者重视百越与南方汉人文化的传承研究。吴春明《东南汉民人文的百越文化基础》着力钩沉当代东南汉民人文中的土著文化因素积淀,如海洋文化精神、土著宗教与惯习、越式聚落与丧葬、原始制陶与无纺树皮布、汉语方言的越语底层等,并从文献与考古资料中所见的越人汉化、汉人越化中寻找民族考古学的解释。彭维斌《闽南民间信仰的文化分层与汉越文化融合》一文,将历史层位分析法引入闽南民间社会文化研究中,探讨了以天公、土地、星辰、龟、蛇、狗、虎等自然崇拜为代表的百越先民“万物有灵”崇拜的底层特征,以吴本、妈祖、临水夫人、清水祖师、三平祖师、王爷等救生神灵为代表的百越土著巫鬼信仰的核心,汉式佛道为代表的表层特征,并从民间信仰层位的形成过程研究汉越文化融合。林汀水则在《也谈闽方言的形成与发展变化》中,提出闽方言源于江浙的吴方言、吴方言与古楚语是闽方言的底层、唐宋以后随着中原汉人的南迁又重叠着上古中古汉语,这是现代汉语方言研究上的全新观点。
五、多学科协作、多层面探讨与国际性视野的学术盛会
在这次学术会议上,与会学者围绕百越史研究的不同专题,从多学科、多层面和国际性的角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展开了热烈的学术研讨,表现出如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1 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参与、协作。考古学是百越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和知识源泉,考古学者的大量参与、考古资料和方法的全面运用是本次会议的重要特点。多数与会考古学者不再是简单列举考古文物资料,对历史问题作出粗浅的说明和解释,而能通过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研究、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探讨百越族群文化的谱系、关系、性质,甚至还将考古类型学方法运用到当代民族文化的分析、研究中,体现了考古学研究在百越史研究中的深入和提高,象西瓯与骆越青铜文化的区分、滇族的三种文化因素构成等研究都是这方面的成功作品。百越史的研究离不开历史学,传统百越史研究主要仰仗史、汉的若干篇章,这次会议上纯粹历史学的研究不多,但也不乏深度,如对先秦岭南古越族九个“土邦小国”的历史钩沉,就是代表。民族学的研究成果是本次会议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壮侗语族的民族文化的调查研究成果有限,但也有突破,尤其是将南方汉人的社会文化纳入百越史的研究范畴,就是一个新的尝试和亮点。在历史地理学方面,从江南城市布局的地理变迁中,找寻吴越城市的“外濠内堑”的底层特征,很有新意。语言学方面,关于南方汉语的越语底层、闽方言的吴语特征等,都是对传统语言学理论的挑战。
2 多方面、多层面的探讨。本次会议除了民族与文化性质、族群源流、文化谱系、文化因素分析与区域文化关系等基础性时空关系研究外,还有百越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多层面的探讨。在物质文化层面上,吴越城址、建筑聚落、崖洞墓葬、航海舟筏、铜鼓、大石铲、竹器与玉器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专题论述。在精神文化层面,百越的海洋精神、万物有灵与巫鬼神灵等、图腾崇拜、南方汉语方言与语言、婚姻习俗、拔牙习俗、食人埋骨习俗等内容,都有学者涉及。在社会与经济层面,骆越的建国、南越的土邦小国、商代闽中的文明因素等国家文明问题,百越同秦汉王朝、荆楚文化的战争与融合问题,以及农业生产与经济生活等问题,也都有争论或讨论。
篇8
所谓“文献”和“实物遗存”,两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在有的场合,两者却能得到某种程度的统一。这是因为所有的“文献”总有一定的载体,不管是金文、石刻还是简牍,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实物遗存,成为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其次,研究对象的不同决定了研究方法的区别。历史学家往往寻求并研究特定的历史事件的记录,然后加以比较和辨伪。将它们置于年代序列中,按照前因后果对事件进行解释。考古学则以地层学和类型学为基本的研究理论和方法,①通过发现的遗迹和遗物,研究古代人类更广泛领域的生活方式,力求全方位揭示人类活动发展变化的轨迹。科学的考古学的真正要义在于超脱文献而独立研究物质遗存。但是考古学现在的主要理论方法地层学和类型学,只是整理材料的分析方法,大量考古发掘报告的器物罗列和描述不能有效地反映历史信息。考古工作者在解读考古遗存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能力上的欠缺,直接影响了考古发掘报告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比如在描述某一个器物的特征时,常出现“弧腹”、“微弧腹”、“腹稍弧”等词语,除了报告的撰写人外,读者很难领悟到器物的具体形态特征。这也导致许多历史研究人员无法读懂考古报告,这种情况下文献和考古发现难以契合。②
多数人对考古学的作用还局限于“正经补史”的阶段,还停留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认识上,从而忽视了考古学的本质就是超越历史文献,通过实物遗存反馈历史信息。考古学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从生态环境、生存方式、技术经济、社会结构乃至意识形态等各个层次来全面分析历史时期的各种演变,从而探寻影响社会文化的各种因素。③在进行考古工作的过程中,可以参考文献材料,但是不能被其主导、引导,更要杜绝“先入为主”式的考古发掘,而是让材料牵着鼻子走,④通过以物论史,透物见人,为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作出新的贡献。因此,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泰教授在谈论文献和考古的关系时,认为文献的甄别和与考古结合的工作不一定是考古学家一定要做的,考古学家的主要任务是要把物质文化研究清楚,然后把结果报告成历史等学科的专家能够使用的方式,然后让文献学和考古学的研究并立而存在,两者结合的地方不一定能够找到,当然两者是同一个现象的不同侧面。⑤这种观点也是西方考古学界所共有的,也对现阶段中国考古学发展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在商品经济的“唯利是图”的大背景下,一些专门宣传考古与文物收藏的栏目出现在大众的面前,如《探索发现》、《鉴宝》、《寻宝》和《天下收藏》等,平面媒体的宣传作用不容小视。随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全民的考古以及文物收藏热潮。中国传统考古学还没有完全适应这种快速的发展,从而带来许多的被动和质疑。但是,中国考古学应该在自身学术规范健全的基础上,去逐渐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公众的需求,并借机宣传自己,一举两得。而如何向大众展示规范的考古学,让他们能接受考古的新发现,减少质疑和批评的声音,这是我们下面讨论的重点。首先,在田野考古发掘的过程中,规范考古发掘的流程,严格按照国家文物局颁布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⑥进行,杜绝挖宝式的考古和唯经费至上的抢救性发掘。其次,尽量避免破坏性的发掘,做好发掘后期的善后工作,给公众留下良好的印象。考古遗存是不可再生的资源,保护意识应贯穿着发掘工作的始终过程。发掘的遗迹是现场保护还是迁移保护,是现场展示还是就地掩埋,亦或就地回填等问题,需要妥善处理考古发掘与保护文物原状的关系,还涉及到可移动文物的现场提取和保护问题,也包括不可移动遗迹的长期保护相关问题。为解决上述保护中存在的问题,考古工作者在发掘的过程中,邀请文物保护和科技相关人员参与到考古发掘中。《科技日报》提及的“文物保护航母”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它是一个跨学科、跨领域、跨行业、跨部门的产物,由敦煌研究院、国家博物馆、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等单位共同研发的,是我国首个“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自2009年起,先后多次出现在山西、陕西、山东和湖北等地的考古发掘现场,为考古工作提供比较系统的技术,并且及时地处理和保护了出土文物。⑦这种模式值得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中国传统考古学一直缺少与外界的有效沟通,在曹操高陵的世纪辩论中,甚至有考古人员提出“非专业人士不能质疑”的说法,遭到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的强烈反对,他认为考古不仅是一个专业问题,还牵涉到共同的学术规范,而这些学术规范适用于任何一个学科领域。⑩这也就要求相关专家和部分在向公众公布信息时,一定要做到全面、严肃,尤其是考古的结论,应避免学术的浮躁,经多方面考证确认为定论后,才能公布于世。英国考古学家特里格认为,如果把考古材料作为一种宣传工具为政治和社会服务,其结果对我们是有害而无益的。尤其是曹操高陵的商业价值,有学者估算出每年能为当地带来至少4.2亿元的经济收入。这就不免产生地方政府之间争夺名人效应的现象。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在当今日新月异的社会,中国考古学的学术规范性直接影响了学科的发展,对树立考古学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极为重要。每一名考古从业人员和研究人员都有义务维护其学术规范,从而促进中国考古学健康快速地发展。诚然,在进行考古学研究的过程中,道德规范是考古研究人员的学术操守,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学术抄袭和学术不端行为,并同时尊重不同的学术思想,积极开展健康的学术争鸣,不为学术研究沾染任何功利性的色彩。在考古学文章成文的过程中,首先要忠于原始材料,引用第一手的材料,如考古报告和简报等,避免因转引造成不必要的错误和争端。(本文作者:张倩单位:河南省济源市济渎庙管理处)
篇9
【摘要题】比较研究
【关键词】李济/苏秉琦/邹衡/考古类型学
在近八十年的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类型的考古类型学研究,这些各具特色的类型学研究不仅记录了重要的考古资料,而且反映了学科方法论的发展历程。从社会学的视角看这些类型学研究在认识和实践方面存在的差别,一方面和研究者所处的学术环境以及考古学科发展状况有关,与此密切相关的另一方面是研究者本人的学习经历和知识体系结构。本文拟选择三位在中国考古学史上产生影响但学习经历不同的考古学家及其代表作,试图从个体社会化差异方面探讨造成学术研究方面差别的原因。
这三位考古学家及其代表作是: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上篇》(注:张光直、李光谟编:《李济考古学论文集选》,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苏秉琦《陕西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得瓦鬲的研究》(注: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及《瓦鬲的研究》(注: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注: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出版。)及《天马——曲村(1980—1989)》[5]。
一
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上篇》是对小屯10座墓葬中出土的76件青铜容器所作的类型学研究。他研究青铜容器形态时,像处理人头骨数据一样,把每个容器视为由若干部分即形态元素组成的复合体,为了便于研究他对容器的各部位进行了划分,并列表给出各部位的名称。
在此基础之上再进行容器型式的划分,起到了明显的规范作用。至于青铜容器的形式划分,作者仍沿用《殷墟陶器图录》提出的容器的分类标准,有以下四条:
(1)以最下部作为第一数的标准:圜底000—099、平底器100—199、圈足器200—299、三足器300—399、四足器400—499,……
(2)每目内再按照上部的形态,定0—99的秩序,大致依口径与体高相比的大小容器的浅深为准;口大的,身浅的在前;口小的,身深的在后;中间又以周壁与底部的角度,唇缘的结构等作更详细的划分准则:向外撇的居前,向内拱的居后。
(3)他种形式上的变化,如周壁的曲线,最大截面所在;耳、把、鼻、柄、嘴、流等,附着品的有无,往往构成该件器物的个性;这些变化并无秩序可循,只能随着具有这些附着品的器物一般的形制排列;序数后加罗马字,分辨型别,表示它们的个性。
(4)在形制上可以独立的器物,即构成一“式”,照所列秩序,予一数字,以为标本,名为“序数”;每一式内再分若干“型”,用罗马字标明,以类别形制相近而有小异的标本。
李先生的分类,首先将容器整体分解成上部“容量部分”和下部“底或足”,也就是非容量部分;器物下部为分类的第一标准,根据形态特征分为五类,即五“目”,器物上部的几何轮廓由倒梯形—宽扁长方形—正方形—高扁长方形—正梯形的顺序用01至99加以区分。首先,每种器物外轮廓的基本形态以三位代码的形式标记识别,编码打破了整体器形的限制,如在三足目中305、313、325、368都是鼎形器,中间的310却是爵形器,这种编码的实质是对器物形态分类的一种管理手段,而不是对器形整体演进的排序。其次,同一序数标记的器物,以更细致的外形要素的特征,特别是通过测量和计算得出的数据作为区分型别的指标。如248式觚形器,用腹径比体高的百分数得到高宽指数,数据区间为10.4至30.48,每进五点即设一个新型,由此得到P、Q、R、S、T由粗矮至细长五个型别。这种用数据的区间范围划分型别进行分类的方法,和自然科学研究的分类方法颇为类似,比如按光波的波长由长到短分为红外线、可见光和紫外线三类。李济称:“这样分目排列的办法只具有一个极简单的目的:便于检查。至于这个排列的秩序是否可以看出形态上的关系出来,却是另外的问题”。举个例子,如M388出土的觚形器标记为248Q,其中第一位数字(2)和第二、三区位的数字(48)均为序数,第四位罗马字(Q)为型别。
苏先生首先从全器的结构和腹足的形式即基本形制特征研究如何分类,继而提出从产生原型去探讨不同形制陶鬲谱系的问题。后来他在《瓦鬲的研究》一文中又对这四个类型鬲的相互关系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前后两篇文章使用的类型符号及其指代的陶鬲的命名对照见下表。
《瓦鬲的研究》用单个大写英文字母表示型,与之对应的小写字母表示亚型,两个大写英文字母表示中间型,大写字母加阿拉伯数字表示组别。作者有着鲜明的追求历史过程的研究取向,以进化论的思想按发生学的原则论述了瓦鬲由产生而经历从A演进至B,从B演进至C,进而演进至D并最终衰亡的过程。《瓦鬲的研究》一文“结论”里提出的陶鬲发生、发展及其谱系关系,充分表达了作者对于陶鬲的分类系统的认识。本文根据《瓦鬲的研究》一文“结论”的文字和附图制成表5,结合这个表阅读有关瓦鬲的论述就不难发现,作者先拟定出一条陶鬲进化的链条,每一类型下的组排列成具有演进关系的小链条,各个类型之间在通过中间型连接成更长的、较完整的链条。因此在陶鬲类型学研究中,作者排序的逻辑思维十分突出而分类的逻辑思维却不很清晰,《陕西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得瓦鬲的研究》提出的分组标准,既含有排序又含有分类,推测作者原本打算先把标本区分开,待找到确切的证据后再将其排序,但实际上并没有做到。
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的类型学研究对象,是殷墟各地点的发掘报告中对于作者而言有分期意义的陶器和铜器。该文首创的表述器物型式的语言范式,已为当今中国考古学界普遍使用,即用汉字标示“类”,大写英文字母标示“型”,小写英文字母标示“亚型”,大写罗马数字标示“式”。例如陶器的型式有三种情况,最多见的是划分型、亚型、式三个层次,其次是划分型、式两个层次,最少见的是只用式别来区分。按照作者对17种陶器研究的先后顺序,归纳出陶器的类型学研究的体系结构,这一体系结构如左图一所示。从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个类型学研究体系包括分型和分式两部分核心内容,即分类和排序,换言之,分型就是分类,分式就是排序(注:陈畅:《试论考古类型学的逻辑和原则》,华夏考古,待刊。)。体系中的型式符号突出体现了标本之间的形态逻辑关系,但却不能由型式符号得出标本的具体形态,也就是说,这种型式符号所代表的仅仅是一种抽象的关系。
如果要说《天马—曲村》一书和《试论殷墟文化分期》一文在类型学研究方面的区别的话,前者是田野考古报告,首要的问题是准确真实地发表好资料,因此在这个前提下,报告编写者着重考虑的是器物类型规范化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器物标本编码体系和器物标本形态特征之间关系的探索,并以青铜容器和戈、圭、璋三种非容器作了实验。
报告将青铜容器分为“底或裆”、“足”、“领、口或沿”、“肩”、“腹”五部分,分别将各部分的形态特征分类列表,并给予每类特征一个指定代码,参见表6。所有青铜容器都按照以上五部分的顺序用符号表示,形成该器物的型别编码,这样,一件青铜容器标本的整体基本形制特征的“标准化”通过其各个组成部分特征的“标准化”得以实现。例如如果将《天马—曲村》与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的类型学研究相比较,就会发现二者均以便于发表资料和研究为目的,按器物形态组成要素的特征进行分类,用大写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为代码标示。邹衡将器物的组成部位大致按照非容器部分和容器部分分开,先列出底、裆、足的特征代码,之后再由从上至下的顺序列出领、口、肩、腹的特征代码,似乎也是受了李济的影响,但又有别于李济的划分方式,如《天马—曲村》中铜甗M6069:2,型别为HFC01′,这件甗为弧裆、柱足,显然“裆”是一种特殊的“底”,和“足”不能混淆,不同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将甗归入“三足目”的做法。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天马—曲村》的分类系统采用面分类的方法,《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则基本采用了线分类的方法,即分类模式的差别(注:关于面分类方法和线分类方法,陈畅:《试论考古类型学的逻辑和原则》,华夏考古,待刊。)。
二
考古类型学研究是研究者的思维能力尤其是抽象思维能力和方法的体现。而抽象思维能力是个人接受社会化的一个重要条件,抽象思维能力的形成与提高是和学校的教育与培养分不开的。从三位考古学家所接受的高等教育和学术成长过程的学科背景中可以领悟出他们各自的研究风格背后传递的学术思想。
李济在清华学堂毕业后,先后在美国麻省克拉克大学学习心理学和社会学,后转入哈佛大学学习人类学。“他的志向是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一下,寻出他所属的人种在天演路上的阶级来”(注:张光直:《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李济先生》,李光谟编《李济与清华》,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后来他对器物形态的研究深受量人脑袋的启发,特别注重器物形态元素的组合方式,而其研究目的则深受美国人类学学科人本主义精神的感染,试图通过器物分析探究社会文化而非考古学文化的变迁,即意在研究人。例如,他认为小屯出土的原始土质爵形器的器形脱胎于龙山文化,这一点符合文化传承,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口部结构的演变则是工匠长期实践不断改进提高器物的实用功能的结果。李济按器物形态元素特征分类的类型学体系,为早期的中国考古学的器物研究打下一个新基础,并且一直影响到今天。
苏秉琦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由于学习中国史学的经历和史学传统的学术背景,致使他认为“近代考古学的目标就是修国史”(注: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商务印书馆(香港)1997年出版。)。他的考古类型学研究大都采取史学的研究方法,十分注重事件的因果关系及过程;而发轫于生物界的进化论理论,又恰好满足了他以物的发展过程序列为研究目的的研究方式,于是进化过程和历史因果关系,构成了他的研究特色。这种特色在《陕西省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得瓦鬲的研究》1983年《补序》(注: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里表现得最为充分。“系统的类型学理论,是瑞典人蒙德留斯(OscarMontelius)在1903年出版的《东方和欧洲古代文化诸时期》第一卷《方法论》中开始建立起来的。在我国,至三十年代,蒙氏的书有了两种中文译本;四十年代以后,苏秉琦先生则在大量实际分析、综合考古新材料的工作中,从中国考古的具体研究出发,为正确运用和发展这种方法论,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注:俞伟超、张忠培:《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编后记》,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超级秘书网
邹衡最先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两年后转入史学系,之后又学习考古学并取得硕士学位。他的类型学研究强调层位依据,即客观证据,型式的逻辑严谨、结构清晰,很明显同他最先学习法律有关系。从他的《我和夏商周考古学》(注:邹衡:《我和夏商周考古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考古学研究》(五),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中了解到,他学习考古学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解决史学问题,因此依然带有强调因果过程研究的史学特征。他最先用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铜器,进而延伸到商文化的分期。他的类型学研究体系清晰地表现了分类和排序两种思维模式,在以类型学研究为基础的年代学研究中,他把考古学文化理解为由各种遗迹、遗物为元素组成的结构,不同文化具有不同的元素以及元素不同的结合方式,元素及其结合方式发生了变化,文化也随之变化,这种以器物组合变化为依据进行文化分期的方法和李济的类型学研究法反映了不同研究层次的同种思维模式。
二十世纪的一个时期里,中国大陆学术界对李济大都回避甚至批判。但是现实中许多考古工作者的类型学研究,又往往不自觉地袭用李济式的类型学模式,称为“某式某型”,将李济的“序号”和“类型”混同苏秉琦的“顺序”和“类型”,这样一来,在一个适用于器物形态元素的分类系统里,导入器形演进的思维方式,其结果必然导致很长一段时间内类型学思想和概念的混乱。虽然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发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才将分类思想和排序思想协调起来,并逐渐规范了类型学的研究模式和语言范式,但是至今还没能彻底摆脱类型学研究中强调历时过程和因果关系的史学影响,而李济那种人本主义精神的考古学研究依然很难看到。
篇10
[关键字]汉书遗址;半山遗址;考古文化
汉书遗址位于吉林省大安市月亮泡镇汉书村北,月亮泡南岸的大坎子上,是松嫩平原青铜时期考古学文化的一个标志。而青铜时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继金石并用时代之后,铁器时代开始之前的历史时代。其主要特征是青铜铸造技术的发明和应用。由于人类发明了青铜冶铸技术,并广泛应用青铜金属原料制作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使社会生产力发生了质的变革,社会生活也由此出现了大的变化,标志着时代的进步,石器时代的结束。考古学界将青铜文化的出现,青铜工具的应用和铁器还没有出现之前的这段历史时代,称为青铜时代。
一、汉书遗址与汉书文化
位于吉林省大安月亮泡镇汉书北村的汉书遗址,在1958年前称为端基屯,为纪念在中英勇牺牲的时任五区区长骆汉书烈士而改名为汉书村。1960年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吉林省文物工作者发现了位于汉书村北,月亮泡水库南岸的这处文化遗存丰富,分布面积较大的遗址,并定名为汉书遗址。1974年6月,吉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和吉林大学考古学专业师生组成联合考古队,由时任吉林大学考古系主任的张忠培先生为指导,对汉书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共开探访15个,发掘面积700平方米,发掘了房址、墓葬和窖穴等遗迹,出土了一批较为典型的文物,如陶器、骨器、青铜器及少量的石器、铁器等。
根据考古队发表在《东北考古与历史》丛刊,1982年第一期《大安汉书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一文记载:汉书遗址的地层和文化内涵,初步区分汉书遗址有两种不同的文化层相叠压,其下层文化成为汉书一期文化,上层称汉书二期文化[1]。根据吉林省《大安县文物志》记载汉书一期文化时期,其历史年代下限相当于我国历史上的西周时期,在距今3100-2500年前后,而汉书二期文化相当于我国历史上的西汉时期,在距今2000多年以前。
汉书一期文化的器物有泥质红褐陶,器型为筒形深腹罐,罐上饰有几何纹饰图案;青铜器都为范制,有背面带有横梁的圆形铜扣及圆形铜片。这说明,汉书一期文化的居民已较广泛地使用青铜器,汉书一期文化已进入青铜时代。
汉书二期文化遗物相当丰富,有陶器、骨角器、石器、青铜器及少量的铁器。其出土的陶器既有生活用具,又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有鬲、罐、钵、碗、权、支座、舟形器等。从陶的质地、颜色看,有泥质红褐陶和彩绘泥质红褐陶,只有极少数的陶器属夹砂红褐陶。施有纹饰的陶器较多,主要纹饰有绳纹、按压纹、彩绘和锥刺纹。金属器主要有青铜器和铁器两类。青铜器主要有刀、锥、扣以及属于青铜短剑附件的石枕状物。出土铁器,主要有銎形斧和刀两种,它的形制同于战国至西汉时期内地居民使用的同类器物。在汉书遗址发掘中,未见冶铸铁器的遗存,这说明当时的冶铁规模是极其有限的。
那么,在汉书遗址叠压在一期文化之下的遗存,清理到一批晚于汉书二期的墓葬。2001年9月以吉林省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考古队对汉书遗址的第二次发掘说明了这一点。一期遗存以台底罐、台底钵为特征,属于嫩江流域近年命名的小拉哈文化范畴,年代相当于夏商时期;二期遗存以大袋足鬲、深腹壶为代表,年代相当于商至周初[2]。
二、半山遗址与小拉哈文化
小拉哈文化是以我市肇源县小拉哈遗址第二期遗存命名的,是松嫩平原上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青铜文化遗存。陶器基本为素面,只有少数施附加堆纹或刻划几何纹,个别陶罐的口沿下面有一周附加堆纹或将口沿压成锯齿状花边,器型主要以直口圈足器为主,小拉哈遗址二期陶片的热释光检测结果,其年代距今3830±340年,相当于我国历史上的夏商时期[3]。而位于我市大同区和平牧场九队的半山遗址是2009年4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的遗址,该遗址土质为黑褐细沙地,沿遗址四周踏查,从地表看,极为丰富,经探查,在该遗址西南角探测地表0.5米处发现大量的极为明显的陶片71片,采集石器61件,动物牙齿5枚,骨器2件,人类头骨残片24片。那么,从半山遗址采集的文物看具有以下特点:一是采集的陶片质地、颜色看,有泥质褐陶、黑褐陶,只有极少数陶片属夹砂陶,施有纹饰的陶片较少,主要纹饰有绳纹、按压纹等,多数为素面,个别陶片口沿下面有附加堆纹或将口沿压成锯齿状花边等,这与小拉哈文化出的文物器型、纹饰和汉书一期出土的陶器类型有相同之处,这说明半山遗址与小拉哈文化、汉书文化属同时期文化;二是采集的石器比较丰富,有石核、石叶、小犁园刮削器、圆头窄身刮削器、高脊背圆头刮削器,石镞有窄身三角形凹身石镞等,这与汉书二期文化还不相同,说明半山遗址的时期早于汉书文化的遗存;三是采集的骨角器比较少,骨器型有锥、镞等,这与汉书二期文化遗存发现的骨器有相同之处,但没有更多类型的器物出现;四是采集人类头骨残片分析,有墓葬址存在,但目前因没有大规模发掘未发现墓葬址,但从头骨残片如将其复原,较其是一个完整的头骨,但从下颌骨牙齿分析是柱状牙齿,与汉书遗址发掘现场墓葬有相同之处,但牙齿不相同;五是铁器、青铜器目前还没有采集到,但汉书遗址发掘中也未发现冶铸铁器的遗存,这一点与汉书遗址目前还有相同之处。
尽管我对白金宝文化、小拉哈文化、汉书文化内涵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加强,但对半山遗址的研究,应引起考古学界的高度重视。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指示:“考古学族属问题的研究,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除了古籍所记族人是否等同于考古文化外,还存在文献记载、疏、注及考证和对考古学遗存的认识问题”[4]。这如此丰富的古代遗存,不仅考古学家重视,也引起了历史学家的极大关注。
参考文献:
[1]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吉林省博物馆考古队.大安汉书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东北考古与文化(1),文物出版社,1982,9.
[2]金旭东.田野考古集粹.文物出版社,2008,11.
[3]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肇源小拉哈遗址调查简报.北方文物,19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