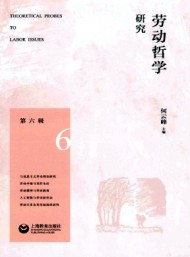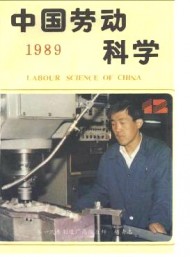劳动力迁移的原因范文
时间:2023-10-09 17:29:29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劳动力迁移的原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中图分类号]G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962(2013)05(a)-0212-01
1.农民参与劳动力转移培训现状
1.1参培率较低。近两年我镇参训人数分别为716人、833人,培训人数占从业人员的比重分别为1.8%、2.2%,参培率低得可怜。
1.2主动性缺失。农民虽对有关培训政策表示出一定程度地欢迎和拥护,但往往是在多方劝说下才同意参加,主动参训少之又少。
1.3思想顾虑重。受多种因素制约,农民参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存在诸多顾虑。
例如,2012年仪征市月塘镇劳动力转移培训,主观不愿意参训的人数占10.8%,认为补贴标准偏低、缺少吸引力的占26.4%,觉得不培训也能顺利就业的占38.7%,认为培训时间难以保证的占13.6%,怕培训后就业困难、没有积极性的占8.3%。
2.转移培训叫好不叫座原因分析
2.1农民培训意识普遍淡薄
受历史、地域、经济发展等因素影响,现有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偏低,造成自我发展能力受限。在农民自己看来不存在需要像中小学生那样学习的必要性,也看不到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学习的紧迫性以及智力投资的重要性,仅把培训当成政府的强迫行为,被动接受。
2.2培训补贴标准明显偏低
目前,我镇对参训农民,每天仅能给予20元的务工补助,培训项目也仅限于玩具、服装加工等非热门项目,农民想参加餐饮服务、机械操作、出国劳务等热门培训必须到市区,按政策规定他们虽可享受一定补贴,但由于标准偏低,补贴费用仅占培训费用的极小份额,加上还需支付一笔数量可观的交通、食宿费用,农民需要自掏腰包,因而积极性不高。
2.3培训时间难以得到保证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时间一般为15天左右,但部分参训农民因害怕耽误生产造成经济损失,连基本的时间都无法保证,培训单位也只能压缩培训时间,简单传授一些基本知识和技能,农民无法学精学透。
2.4就业准入制度执行不严
近几年,企业用工难现象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企业为了生产需要,相应降低了就业门槛,无培训照样上岗,加之培训后就业与未培训就业工资水平差距不大,种种现象使一部分农民认为参与培训费时误工。还会影响收入。
2.5服务保障体系尚未建立
目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大多停留在培训层面上,培训后服务保障体系尚未完全建立。主要表现为:(1)不能及时向全体参训人员提供各种就业信息,(2)没有与用工企业签订定向培训协议,推荐就业岗位;(3)对培训后因失业而返乡的农民未能提供免费的二次培训,促其再就业,四是对转移就业的农民缺少必要的后续跟踪服务,如权益保护、法律援助等。
3.调动农民参与培训积极性对策
3.1加大舆论宣传,着力提高农民思想认识
通过广播、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广泛宣传农村劳动力转移实施目的意义,扩大宣传广度和深度,使广大农民及时了解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精神实质,积极主动地参训,深入宣传那些通过转移培训外出创业中涌现出的典型人物事迹,大力开展表彰奖励活动,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扩大社会影响,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3.2提高补贴标准,切实减轻农民培训负担
切实加大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补贴力度,提高补贴标准。地方政府应落实好相应经费,并纳入财政年度预算。逐步建立政府主导、用人单位与农民共同投入的费用分担机制,在保证政府投入的前提下,引导企业加大培训投入,鼓励民间捐资,简化农村劳动力转移补贴环节,及时足额地将补贴发放到参训农民手中,让农民真正得实惠。
3.3创新培训形式,不断提升农民就业技能
整合各类教育资源,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吸纳本地优势教育资源参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以培训机构的品牌效应吸引农民参与培训。从农民的愿望出发,从企业的需求出发,从市场发展角度出发,科学设置培训专业,采取位点下移、就近培训,就地转移等培训模式,让农民不出远门就能参与培训。加强与行业协会、劳动力市场、用工企业等的合作,举办具有行业特点、针对性较强的专业技能培训,走先培训后输出,定向培训、定向输出的路子,以培训促输出。坚持严格考核、合格发证制度,切忌走形式,走过场,让经过培训的人员真正学到一种技能,得到市场的认可。
3.4强化政策引导,逐步实施就业准入制度
逐步完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就业配套政策,建立先培训再就业制度,使培训成为农民个人自觉行为。逐步实施市场准入制度和劳动力预备制度,严格实施持证上岗制度,提高用人单位使用合格劳务人员意识,规范用工行为。要不断强化政策引导力度,使每位农民知晓就业准入制度的实施,并不是人为阻止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而是引导农村劳动力自觉接受职业技能教育和培训,从而更好地实现转移就业。
篇2
关 键 词: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劳动力流动
中图分类号:F0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4-0016-06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劳动力流动问题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劳动力流动也呈现空前的规模。与此同时,中国的收入差距也日益严重,并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已成为中国经济协调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巨大障碍。理论上说,劳动力流动会缩小收入差距,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种与理论相悖的现象并不是中国独有,许多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有过类似经历。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又有其特殊性。本文将围绕中国的收入差距与劳动力流动的特殊性、收入差距与劳动力流动之间的关系、劳动力流动为什么没有缩小收入差距等问题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和分析,以便更好地理清这些问题的研究思路。
一、中国的收入差距:现象与原因
1. 城乡收入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收入差距呈先缩小后扩大的态势。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一个转折点,之后城乡收入差距又呈不断扩大态势。从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两个指标的比较来看,若考虑零售物价指数的变化,城乡收入比率(以农村收入为1)从1978年的2.6一度下降到1988年的1.5,随后提高并达到2003年的2.4。[1]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这里使用的城乡收入概念并不完全可比,如果把城市居民享受的其他福利折合成收入,城乡收入差距还会大幅度扩大。[2]此外,从我国东、中、西部的城乡差距来看,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的城乡差距一直高于同期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1980-1985年间,东部和中部地区城乡差距呈缩小趋势,而西部地区维持不变。其后,三大地区的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但西部地区的变化趋势更为显著。1980年,东、中、西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分别为2.01、1.63和2.11。然而,到2000年,中、西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上升为2.49和3.62,而东部地区却只有2.30。[3]城乡差距在不同地域上的严重程度不同,这也是我国城乡差距的特征之一。
对于不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与解释。从我国经济发展历程来看,城乡收入差距始于城乡劳动力市场的行政分割。195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形成了几乎延续至今、阻碍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框架。这种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所造成的劳动力市场扭曲,被认为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4-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地区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均倾向于城市集聚,加之城乡之间产业结构的根本差异,导致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城乡收入差距存在自然扩大的趋势。同时,政府在基础教育等资源分配上的城市倾向,以及对城市计划控制部门的工资和福利的制度保护,都会加剧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8]此外,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对外贸易的发展、劳动者素质的差异、就业的所有制结构调整、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分配不公以及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等,也是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9-10]
2. 地区收入差距
与城乡收入差距相一致,中国地区收入差距也呈上升趋势,[11-14]而且根据收入差距分解显示,地区间收入差距本身就与中国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有关。[15-16]地区差距的扩大在20世纪90年代尤其明显,[17]1980年中、西部人均收入分别相当于东部的78%和70%,到2000年,它们占东部的比例分别降到了62%和54%。[18]为此,学者们提出了各自的观点。概括地说,不断扩大的地区差距与政府政策、要素流动、市场化进程、资源禀赋、教育投资等因素有关。
王小鲁和樊纲(2004)通过考察资本、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在各地区间的流动和配置状况、市场化进程在各地区间的差异、城市化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等方面,指出我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主要是由于生产率的差别以及由此引起的资本流动所导致。[18]陈秀山和徐瑛(2004)经过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要素投入、市场化进程与要素的使用效率是影响地区差距的因素。[11]林毅夫和刘培林(2003)指出,地区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下形成的生产要素存量配置结构与各地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符合程度不一致。[12]蔡和都阳(2000)通过考察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中存在着俱乐部趋同以及条件趋同的现象,认为中西部地区存在着一系列不利于向东部地区趋同的因素,如人力资本禀赋稀缺、市场扭曲和开放程度不足。[19]还有一些研究将中国地区差距与城乡差距的原因归结于外商投资,[20-23]以及中央政府的地区倾斜政策或地理、文化等因素。[24-25]他们认为,国外资金的流入、中央政府对东部地区的优先投资是中西部地区落后于东部地区的根源,同时,中西部不利的地理条件也限制了这些地区的发展。
二、中国的劳动力流动:规模与特征
1. 劳动力流动的规模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以及人口迁移、户籍政策的逐步松动,我国劳动力流动规模越来越大。根据我国1990年、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和1987年、1995年两次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82-1987年间中国劳动力迁移规模是3053.3万,1985-1990年增至3412.8万;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迁移规模在1990-1995年间达3642.6万,而1995-2000年高达13122.4万。[26]
2. 劳动力流动的特征①
按流动人口的迁移距离划分,可以分为近邻流动、中程流动和远程流动。②在全国流动人口中,属于近邻流动的人口为6563.4万人,占45.5%;中程流动人口为3633.8万人,占25.2%,两项合计占总流动人口的70.7%。远程流动人口为4241.9万人,占29.3%。此外,劳动力远程流动多发生在经济相对较发达、体制创新快、工业贸易发展较活跃的地区。从三大地带看,沿海地区是远程流动比重最高的地区,达39.9%,远高于中部地区(10.5%)和西部地区(21.1%)。[27]这说明迁移规模与迁入地和迁出地的经济差距成正比。
从劳动力流动的方向看,沿海地区成为劳动力净流入地区,净流入人口总计3195.8万人。内陆地区成为劳动力净流出地区,净流出人口为2358.4万人。从各省区来看,广东、上海、北京、浙江和福建的外来人口中来自于内陆地区的比例分别为76.74%、59.2%、53.99%、91.06%和91.7%;而内陆地区的四川、安徽、湖南、江西和河南则是主要的劳务输出省,其迁往沿海地区的比例分别为72.04%、91.88%、92.14%、95.71%和73.32%。[28]由此可看出,地区收入差距对于劳动力流动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按户籍是否变化分类,所有的迁移人口可分成两类,即户籍迁移和非户籍迁移。后者占全部迁移人口的65.1%,其中以务工经商为迁移目的的占45.9%,反映了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的跨地区就业。城市到城市的迁移和农村到城市的迁移,构成了全部非户籍迁移的80.3%。实际上,这些迁移者构成了城市就业的重要组成部分。[29]
三、收入差距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
由上述数据可看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了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与劳动力流动规模不断扩大并存的现象。按照经典的迁移理论,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是诱发人口和劳动力流动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而劳动力流动又会缩小收入差距,但中国的事实并非如此。理论与事实的相悖引起了研究者们的极大关注,学者们就收入差距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由于数据获取等原因,目前直接研究收入差距对迁移决策影响的实证结果还较少。[30]从现有的研究看,由于研究的角度和采用的方法与数据不同,其得到的结论也存在差异。
1. 收入差距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一些学者应用实证分析方法就收入差距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进行了研究。Zhu(2002)使用probit模型的结构方程(structural equation)证实了城乡收入差距在中国农村向城市迁移过程中的正向作用。[31]蔡(1996)研究了本地农村人均收入与全国农村人均收入的比率对于迁移的影响,发现这一比例的增加可以减少迁移。[32]林毅夫等(Lin,et al.,2004)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地区收入差距与人口流动之间的关系,其结论是,20世纪90年代末,迁移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反应显著提高。[33]Zhang和Song(2003)利用时间序列和横截面分析,指出收入差距是省内迁移和省际迁移的巨大推动力。他们认为,既然省际迁移主要是从内地的农村迁往沿海的城市,那么任何减少内地与沿海收入差距的方法不仅可减少这种迁移,而且可为广大内陆省份提供大量的发展机会。[34]Wu和Yao(2003)在人口无限供给的假设条件下,运用需求导向模型,对中国的省际迁移与省内迁移进行了研究。其结论是,城乡收入差距是迁移产生的原因,但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其他决定劳动力流动的因素。[35]王春超(2005)也有相似的观点,他利用相关的调查数据分别从“收入差异和劳动力流动性”以及“劳动力就业集聚”两方面做出检验,得出的结论是,城乡收入差异并不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原因,农民在转移过程中将愈来愈关注其转移的成本以及决定其转移成本的政策或制度性限制因素。[36]
在家庭层面上,Hare(1999)发现人均生产性资本对迁移没有显著影响,但是,人均生产性资本每增加100元,可以使转移持续时间增加2%。[37]都阳等(Du,et al.,2005)研究了中国的迁移与农村贫困的关系,结果显示,处于贫困线附近的家庭比那些更富或更穷的家庭更倾向于迁移。[38]杜鹰(2006)在对四川和安徽两省调查资料的分析中,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即中等偏低收入户往往是外出打工的最大受益者。对于最低收入户和贫困户而言,他们主动利用这个机会的能力是有限的。[39]因为,某些基本条件的缺陷制约了他们的迁移。[40]
Zhao(2005)指出,这些发现与Harris-Todaro两部门模型一致。然而,已有的研究没有回答V形的城乡收入差距对于劳动力流动趋势的影响,且目前直接研究收入差距对迁移决策的影响的实证结果还太少。[30]
2. 劳动力流动对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
从现有的文献看,大部分学者认为迁移会缩小收入差距。如段平忠等(2005)认为,中国人口流动地区分布的差距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人口流动对增长差距的收敛作用明显。[41]跨地区劳动力流动会缩小地区差距,其作用主要发生在两个方面:一是中西部低收入地区的劳动力外流,会缓和这些地区农村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和就业压力;二是劳动力流动为中西部地区带来了大量的汇款,对流出地区农民收入的增长起了直接支撑作用(王小鲁和樊纲,2004)。[18]然而,迁移缩小城乡或地区差距并非是无条件的,而户籍制度的继续存在使得这些条件不能满足,以致迁移不能发挥其缩小地区差距的作用。[1]姚枝仲等(2003)也有类似观点,他们认为,劳动力流动除了能使地区间要素收入相等以外,还能改变各地区的需求结构,削平地区间要素禀赋差异,最终实现地区间人均收入相等。他们的经验分析表明,由于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受到较大的限制,劳动力流动还没有对地区差距缩小发挥重要作用。[42]林毅夫等(Lin,et al.,2004)通过估计迁移者对收入差距的反应弹性,认为迁移的确是一种缩小差距的机制,但他们也观察到,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和沿海地区过快的发展速度,目前的迁移规模仍不足以缩小现存的收入差距。[33]
一些学者也有不同的观点。如李实(2003)指出,农村劳动力流动对整个农村收入差距的缩小起到微小的作用。劳动力流动在一些富裕地区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但在一些贫穷地区却起到了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这是因为,在富裕地区外出的劳动力主要来自于一些低收入家庭,而在贫穷地区则主要来自于中等偏上收入家庭。[2]因此,现阶段仅依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并不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张庆等,2006)。[43]同时,迁移并不能通过自身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Du,et al.,2005)。[38]而完全相反的结论是,跨省劳动力流动的结果反而扩大了地区间发展差距(孙自铎,2004)。[44]
3. 为什么劳动力流动没有缩小收入差距
多数学者认为,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因素是中国劳动力流动未能缩小收入差距的决定因素。
Whalley和Zhang(2004)通过一项模拟表明,③一旦取消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劳动力流动的障碍,现存的收入不平等则会全部消失。[45]蔡则更深入地分析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迁移能够缩小城乡或地区差距需满足一定的条件。根据理论分析和世界各国的经验,他归纳了四个条件:一是迁移应反映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这种结构性变化;二是流入劳动力有机会且比较稳定地实现就业转换;三是城乡总产出分配格局应从不均等趋于均等;四是劳动力流动应是不受制度约束的自由流动及长期行为。一旦社会的迁移活动不符合上述四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条件,劳动力流动的扩大就不能保证收入差距的缩小。就中国而言,计划经济时期遗留至今的制度,使暂时性的劳动力流动替代了永久性的人口迁移,其结果是,虽然迁移规模扩大,却没有相应带来收入差距的缩小。[1]
韦伟和傅勇(2004)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导致劳动力流动没有缩小收入差距:一是中国由于存在许多制度障碍,流动成本非常大,使农业劳动者在城市的工资超过农村收入的部分被流动成本抵消。二是,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的工资收入被固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在农村的收入较低,纯收入更低,导致其在城市就业的机会成本很低;另一方面,城市劳动力需求还不足以吸收全部农村剩余劳动力,所以,农业平均劳动生产率及农民收入还未能因农村人口的转移而得到明显提高。这样,无论农民选择进城还是选择务农,其收入都不高。三是撇开流动成本抵消作用来看,农村劳动力无法进入具有高工资和福利的计划控制部门,这部分差距处于制度保护之内,不能通过人口流动或市场机制来解决,这是导致我国城乡差距过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在市场主导部门,农村劳动力因其具有较少的人力资本禀赋而在城市中只能获得较低的报酬,这也是人口流动没能缩小城乡差距的原因。[8]同时,沿海地区过快的发展速度也使得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不能缩小。[33]
四、解决劳动力流动未能缩小收入差距的对策建议
在现有的研究中,大多学者还是主张应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就政府应发挥的作用而言,学者们的观点不尽相同。
在转轨过程中,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同时扩大是一种制度现象,其主要原因在于户籍制度等对劳动力永久迁移的约束,从而不能满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条件。所以,应改革户籍等制度,减少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蔡,都阳,2004)。[29]从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的角度看,最有效的方法是完善政府职能、加强宏观调控,利用政策导向引导流动人口向“后发地区”流动,逐渐消除地区差异。同时,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人口向城市流动,也可成为解决地区差距的最有效办法(段平忠,刘传江,2005)。[41]
Zhang和Song(2003)则认为,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步伐、规模受经济增长和发展水平的影响。由于工业与城市社会服务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有限,以及经济增长导致的大量城乡迁移和城市化等因素带来了一系列失业与贫穷问题,因此,要抑制失业,政府有必要采取控制城乡迁移的措施。另外,政府还应着手解决因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而带来的城市迁移人口增长问题。可以采取两种政策:一是创造更多的城市工业和服务业岗位;二是限制劳动力流动。[34]
韦伟和傅勇(2004)认为,应立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来调整城乡关系的扭曲,在城乡压力逐步释放的同时,改革传统的城乡体制。另外,各级政府应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8]
五、研究的困难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从众多的文献看,真实且充分的数据对于收入差距与劳动力流动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至于更深入的研究,最大的困难莫过于获得适用的数据。目前我国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真实统计数据不仅非常缺乏,[46]而且普查数据与现实不符的问题严重。{4}有关收入差距的数据也不能真实地反映事实。现有研究所讨论的收入差距都是以国家统计局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数据为基础,但是,按照国际规范的个人收入定义,中国官方统计资料中的城乡居民个人收入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低估问题,其中城镇居民收入的低估幅度远远大于农村居民。[2]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对中国收入差距与劳动力流动关系的研究任重而道远。
在经验研究方面,还有很多有关收入差距与劳动力流动关系的问题需要验证。农村流动劳动力进城就业无疑会对收入差距的变动产生多重效应,它会影响到农村内部的收入分配,也会影响到城镇内部非技术工人的工资水平,从而影响到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较大影响。然而,这些效应是随着时间的变化、劳动力管理制度的变化和劳动力市场竞争程度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对这些变化进行经验上追踪验证是完全必要的。[2]此外,对不同地区劳动力流动的跟踪调查,从社会学角度进行研究较多,而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劳动力流动前后城乡与地区差距变化的实证研究较少。试想,如果没有大量的流动劳动力,我们的收入差距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类似于这方面的研究很少。事实上,这是中国收入差距与劳动力流动之间关系最有说服力的研究。
此外,在诸多的实证研究中,研究者们多采用抽样调查和典型调查的方法,因而使用规范的定义和利用合理的调查与分析方法是获得科学结论的关键。由于采用不同的样本,或者使用不同的收入和转移劳动力的定义,或者利用不同的测量方法等,往往都会得出不同的估计结果。正如前述的研究成果,虽然增进了人们对收入差距与劳动力流动之间关系的认识,但仍存在一些假说性的解释未得到经验的验证。而且,有些模型是建立在大量的不切实际的假设之上,[47]因而对问题的解释也受到了一定的制约。劳动力转移会缩小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的理论预期与现实不符,形成了一个悖论。[48]这要求研究者通过获得更真实的数据,借鉴更先进的方法,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推向深入。
――――――――
注释:
① 此处的分析均为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
② 近邻流动是指人口在县内或市内各乡、镇、区之间的流动;中程流动是指人口在省内跨县、跨市的流动;远程流动是指人口的省际流动。
③ 这里,他们的假设是户籍制度是劳动力流动的惟一障碍,或者说,存在户籍制度就意味着劳动力不能流动。参见蔡的《中国收入差距和贫困研究:我们知道什么,我们应该知道什么》(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工作论文系列四十二,2005(b),第1期)。
④ Johnson(2003)通过对中国1990年和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指出,中国省际迁移的数据没有包括数以百万计的只是迁移但未登记的人口。此外,两次人口普查对城市居民定义标准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对迁移的估计。就业的种类没有完全包括在城市就业之内,严重限制了对就业的估计。还有,拥有大量就业来源的中国农村,没有可获得的就业数据来源渠道,其就业数据严重缺乏。
――――――――
参考文献:
[1]蔡.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分析――解释流动与差距同时扩大的悖论[J].经济学动态,2005(a),(1):35-39,112.
[2]李实.中国个人收入分配研究回顾与展望[J].经济学季刊,2003,2(2):379-404.
[3]张昌彩.“十一五”时期我国城乡结构及劳动力变动趋势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04,(27):2-14.
[4]Cai Fang.Rural Urban Income Gap and Critical Point of Institutional Change[R].Working Paper,2003,(37).
[5]Lu Ding.Rural-Urban Income Disparity:Impact of Growth,Allocative Efficiency and Local Growth Welfare[J].China Economic Review,2002,(13):419-429.
[6]陆云航.要素积累、政府政策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J].当代财经,2006,(4):5-13.
[7]刘社建,徐艳.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形成原因及对策研究[J].财经研究,2004(5):93-103.
[8]韦伟,傅勇.城乡收入差距与人口流动模型[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6):16-22.
[9]章奇,刘明兴,Vincent Yiupor Chen.中国的金融中介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A].蔡,万广华.中国转轨时期收入差距与贫困[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82-201.
[10]陆铭,陈钊.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J].经济研究,2004,(6):50-58.
[11]陈秀山,徐瑛.中国区域差距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4,(5):117-129.
[12]林毅夫,刘培林.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地区收入差距[J].经济研究,2003,(3):19-25.
[13]Kanbur,Ravi,and Zhang Xiaobo.Which Regional Inequality?The Evolution of Rural-Urban and Inland-Coastal Ineyuality in China from 1983-1995[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1999,(27):686-701.
[14]Tianlun Jian,Jeffrey D.Sachs,and Andrew M.Warner.Trends in 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 [J].China Economic Review,1996,(7):1-21.
[15]Tsui,Kai-yuen.Decomposition of China’s Regional Inequalities[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1993,17(3):600-627.
[16]Athar Hussain,Peter Lanjouw,and Nicholas Stern.Income Inequalities in China:Evidence from Household Survey Data[J].World Development,1994,22(12):1947-1957.
[17]Fei Zheng,Li Da Xu,Bingyong Tang.Forecasting regional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J].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2000,(124):243-254.
[18]王小鲁,樊纲.中国地区差距的变动趋势和影响因素[J].经济研究,2004,(1):33-44.
[19]蔡,都阳.中国地区经济的趋同与差异――对西部开发战略的启示[J].经济研究,2000,(10):30-37.
[20]魏后凯.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J].经济研究,2002,(4):19-26.
[21]Shangjin Wei and Wu Yi.Globalization and Inequality Without Differences in Data Definition,Legal System and Other Institutions[R].Working paper,Brookings Institution,Washington,D.C.,2002.
[22]沈坤荣,耿强.外国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与内生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计量检验与实证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1,(5):82-93.
[23]Fleisher, Belton M. and Jian Chen.The Coast-Noncoast Income Gap, Productivity, and Regional Economic Policy in China[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1997,25(2):220-236.
[24]Demurger,Sylvie,Jeffrey Sachs,Wing Thye Woo,Shuming Bao,Gene Chang and Andrew Mellinger.Geography,Economic Policy,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J].Asian Economic Papers,2002,(1):146-197.
[25]徐李全.地域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2):5-10.
[26]王德,朱玮,叶晖.1985-2000年我国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均衡作用研究[J].人口与经济,2003,(6):1-9.
[27]叶裕民,黄壬侠.中国流动人口特征与城市化政策研究[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2):75-81.
[28]乔晓春.从“五普”数据分析城市外来人口状况[J].社会学研究,2003,(1):87-94.
[29]蔡,都阳.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劳动力流动――长期性、效应和政策[J].学术研究,2004,(6):16-22.
[30]Zhong Zhao.Migration,Labor market flexibility,and Wage Determination in China:A Review [J].The Developing Economics,2005,XLIII-2:285-312.
[31]Nong Zhu.The Impacts of Income Gaps on Migration Decisions in China[J].China Economic Review,2002,(13):213-230.
[32]蔡.劳动力迁移和流动的经济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33):120-135.
[33]Lin,Justin,Gewei Wang and Yaohui Zhao.Regional Inequality and Labor Transfers in China [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2004,52(3):587-603.
[34]Kevin Honglin Zhang,Shunfeng Song.Rural-urban 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Evidence from Time-series and Cross-section Analyses[J].China Economic Review,2003,(14):386-400.
[35]Zhongmin Wu,Shujie Yao.Intermigration and Intramigration in China: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J].China Economic Review,2003,(14):371-385.
[36]王春超.收入差异、流动性与地区就业集聚――基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05,(1):10-17.
[37]Hare,Denise.“Push”versus“Pull”Factors in Migration Outflows and Returns:Determinants of Migration Status and Spell Duration among China’s Rural Population[J].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1999,35(3):45-72.
[38]Yang Du,Albert Park and Sangui Wang.Migration and rural poverty in China[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5,(33):688-709.
[39]杜鹰.现阶段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基本特征与宏观背景分析[A].蔡,白南生.中国转轨时期劳动力流动[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18-136.
[40]都阳,朴之水.迁移与减贫――来自农户调查的经验证据[J].中国人口科学,2003,(4):56-62.
[41]段平忠,刘传江.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地区差距的影响[J].中国软科学,2005,(12):99-110.
[42]姚枝仲,周素芳.劳动力流动与地区差距[J].世界经济,2003,(4):35-44.
[43]张庆,管晓明.单纯依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并不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J].经济纵横,2006,(3):47-50.
[44]孙自铎.跨省劳动力流动扩大了地区差距――与缩小论者商榷[J].调研世界,2004,(12):31-33.
[45]Whalley,John and Shuming Zhang.Inequality Change in China and (Hukou) Labor Mobility Restrictions[R].NBER Working Paper 10683,2004,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46]Johnson,D.Gale.Provincial Migration in China in the 1990s[J].China Economic Review,2003,(14):22-31.
[47]Thijs ten Raa,Haoran Pan.Competitive Pressures on China:Income Inequality and Migration [J].Regional Science & Urban Economics,2005,(35):671-699.
篇3
关键词:城乡转移 农村剩余劳动力 收入差异
为了探寻我国农村人口大规模城乡迁移的原因,本文主要分析我国农村和城市发展的现状,从中对导致我国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一系列相关因素进行简要的分析,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我国更好解决农村人口的城乡迁移中的问题提供一些的意见。
一、 我国农村人口城乡迁移现状分析
农村建设是当前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措施。“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实质是增收问题,而增收的关键是减少和转移农民,这就使我国农业就业比重明显下降,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迅速上升,从而加速我国城市化进程。向城市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年龄结构较轻,据农业部调查,2005 年全国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平均年龄为30. 8 岁,比全部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年龄低9 岁。二是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未转移的农村人口,据农业部2005 年调查,农村外出就业者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 0年,比留在农村的农业劳动者多1. 5 年;外出就业的劳动力中接受过初中及以上教育的人数占46. 3 % ,比全部农劳动力高出9. 6 个百分点。三是生存发展能力较未转移出的农村人口强,目前相当一部分向城市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常年往返于城乡之间,他们农忙时在家务农,农闲时外出务工,在外面积累了一定的社会阅历和精神财富,这使他们比其他农民具有更强的经济生存能力、社会适应能力和发展能力。特别是很多新一代的年轻农民,外出打工已非完全为谋生计,而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另外,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农民工数量已超过2亿人,占全部就业人口近1/3。我国建筑业的50%、煤矿采掘业的80%、纺织服装业的60%和城市一般服务业50%的从业人员均来自农村,农民工已成为城市劳动者的主体。但是,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逐年增加,就业压力和转移难度越来越大。目前,我国有4.9亿农村劳动力,还有超过1.8亿有待转移。2020年之前,平均每年大约有1000万人需要从农村转移出来。
二、 导致我国劳动力城乡迁移的因素分析
下面我们简要的从城乡收入差距这一因素着手,分析我国的劳动力城乡迁移的主要因素。现阶段,我国人口迁移的主要方向是农村向城市迁移、由西部和中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迁移、有边疆和内地向沿海迁移。
下面,通过统计资料对上述相关收入情况作一个比较:
第一,城乡收入差异:
从上图可以看出,近三十年来,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存在很大的变动。特别是从1986年以来,作为反映一个国家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我国的指标不断的升高。并且已经突破了国际上所公认的0.4的警戒线。
经济转轨过程中,收入差距的扩大是有很多因素造成的,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收入差距主要表现在城乡收入、地区收入、城乡内部收入等方面的差异不断扩大。而其中的城乡收入差异尤其引人注意。
第二,地区收入差异:
长期以来,中国传统对国土进行东、中、西的划分。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东中西部地区各自的经济发展,无论是从经济总量还是经济的增长速度,与以前相比,都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各地区相对的收入差距却日益增大,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很快,西部和中部相对较慢,这也成为我国中西部地区人口向东部迁移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不难得出,由于我国的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存在巨大的收入差异,造成农村人口、中部和西部人口,对于迁移后的收入形成较高的预期(预期收入大于在农村所得的收入),因而形成了目前我国人口迁移趋势。
除了上述主要促进因素外,作为中国这一发展中的大国,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促使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城乡转移。具体来说,有如下几个方面:
1、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
改革开放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在确认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提高了农民的生产效率,同时使大量隐性剩余劳动力显化。过剩的农业劳动力成为城乡迁移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是由于农业产值的下降和农业收入的降低,土地在农民增收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从生产要素转而变为提供保障和抵御风险的资产,土地转而成为农民社会保障的主要依赖。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性质,使得迁移的农民由于担心在新一轮的土地分配中失去土地而纷纷回到农村,“循环式迁移”成为中国农村城乡迁移的主要形式。
2、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
随着各地区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将会释放出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可能会加入到未来城乡人口迁移的大军阻碍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因素。
3、农村青年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与人口城乡迁移存在倒.U型关系,即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禀赋的农村劳动力优先选择的不是异地转移,而是选择在农村的非农产业就业。从迁移人口的文化程度来看,迁移人口的受教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和高中教育水平上,其中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迁入人口又占到迁移人口的绝大多数,即中国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与农村人口城乡迁移倒U.型关系的拐点可能为初中文化程度。
三、结论
综上所述,促使我国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转移是由我国的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的,是由上述几个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本文认为,一方面要调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推进城市化进程。另一方面又要保证这种差距在适当的范围之内, 控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另外,加快城镇化步伐, 提高城市化水平, 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拓展更加广阔的空间。
参考文献:
[1]谭伟.中国收入差距―增长“奇迹”背后的利益分配.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9版
篇4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经济发展;理论综述;国外
中图分类号:F2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4-0124-02
国外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渊源已久。1691年威廉・配第根据当时英国国情明确指出:工业往往比农业、商业往往比工业的利润多得多,因此劳动力必然由农转工,而后再由工转商;1940年英国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在此基础上计量和比较了不同收入水平下就业人口在三次产业中分布结构的变动趋势,并揭示了其演变规律,指出劳动力分布结构变化的动因是产业之间相对收入的差异[1],由此形成配第―克拉克定理。但这个问题直到20世纪50年代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的建立起才开始受到重视,并逐步形成了理论体系。
一、宏观视角
1.刘易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二元结构模型[2]。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二元结构的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化的理论模式。他认为,在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社会里,劳动力供给具有完全弹性,只要工业部门高于农业部门维持生计的固定工资水平,就可获得无限供给的劳动力[3]。工业部门吸收农业部门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资源代替资本,所获超额利润被用于再投资进行新的资本扩张,吸收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过程中,传统农业部门逐渐摆脱剩余劳动力负担,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就会提高,从而得以摆脱低效开始真正发展。此时,二元结构经济转换为同质的一元现代经济。
2.拉尼斯―费景汉模型[4]。1961年,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拉尼斯和费景汉针对刘易斯模型的不足进行修正和扩展,并在合作的论文《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拉尼斯―费景汉人口流动模型,1964年又在《劳动力剩余经济的发展》中对此进行系统的阐述。他们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由一种无阻碍过程变为一种有可能受阻的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农村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零阶段,劳动力转移不会受到阻碍;二是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大于零小于农业平均固定收入阶段,劳动力转移将会受到农业总产出下降的影响;三是农业边际生产率大于不变制度工资的阶段,劳动力转移受到阻碍[5]。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人口增长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阻碍,确立“临界最小努力”的概念和准则,扩大了剩余劳动力的范畴。
3.托达罗的乡村―城市劳动力转移模型[6]。1969年,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发表《人口流动、失业和发展、两部门的分析》,阐述了乡村―城市劳动力转移模型,回答了为什么农村向城市的移民过程会不顾城市失业和隐蔽失业的存在而继续进行,从而补充了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托达罗模型的出发点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移民的决策是根据“预期”收入最大化目标作出的,并指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决策不仅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还取决于城市就业率和失业率,即:第一,如果城市的预期收入超过乡村收入,乡村向城市的流动就会继续;第二,当人口流动迫使城市工资下降,或迫使城市失业率上升,使城市的预期收入等于乡村收入时,流动就会停止;第三,当乡村收入大于城市预期收入,就有可能出现劳动力向农村的“回流”。
4.乔根森二元经济发展模型[7]。1967年,美国经济学家戴尔・乔根森在《过剩农业劳动力和两重经济发展》一文中依据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方法提出农业产量的盈余对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创立乔根森模型。乔根森认为,农业人口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根本原因在于消费结构的变化,是消费需求拉动的结果,当农产品需求被满足时农业发展就会失去需求拉动,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就会转向需求旺盛的工业部门;农业人口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基础是农业剩余而非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虽然大于零但小于实际收入水平的劳动力的存在;农业与工业两个部门的工资水平都决定于技术进步率和资本积累率,由于技术进步率和资本积累率总是提高的,因此工资水平是上升的。
二、微观角度
1.贝克尔家庭经济学[8]。1964年,美国经济学家加里・S.贝克尔在《人力资本:特别是关于教育的理论与经济分析》一文中运用微观经济学方法分析了大量的社会学问题,并引入时间的机会成本概念,研究了广泛的家庭行为,如生育行为、婚姻市场以及家庭劳务分工问题等,形成家庭经济学理论。贝克尔认为家庭跟其他理性的经济人一样,每天都要进行投入与产出相比较的生产决策,合理地分配以试图达到最佳组合,以求得家庭成员在收入和时间的双重约束下获取最大的满足,实现家庭生产效用最大化的目标。
2.斯塔克新迁移经济学。20世纪80年代,奥迪・斯达克等人提出新劳动力转移理论,他们认为迁移决策不是由相互孤立的个人行为主体单独作出,而是由相互关联的人所构成的较大的单位(例如家庭)作出的。在这种单位里,人们集体行动以求预期收入最大化、风险最小化,缓解与除劳动力市场之外的各种各样的市场失败相关联的各种约束[9]。在他们看来家庭成员的迁移不仅能使该家庭的绝对收人有所增加,而且能提高其家庭在当地社会的地位,回避农业生产的风险,减少长期收入的波动。
3.推―拉理论模型[7]。20世纪50年代唐纳德・博格在拉文斯坦和巴格内研究基础上系统提出人口迁移的“推一拉理论”。在自由市场经济中人们迁移是两种不同方向的力作用的结果,一种是拉动人口迁移的积极因素,包括在迁入地有较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工资收入、较好的生活水平、较完善的文化设施和交通条件等;还有一种推动人口迁移的因素,主要包括迁出地的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剩导致失业和就业不足、较低的收入水平等等。这一理论对影响劳动力流动的社会、经济及制度因素做了综合。
4.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1960年,西奥多・W.舒尔茨在美国经济协会的年会作了题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同年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提出人力资本是当今时代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10],并从人力资本投资角度来解释劳动力迁移行为,认为劳动力迁移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形式,由于人力资本投资要支付成本,因此只有劳动力迁移的预期收益大于迁移成本时,其在产业间或地区间的转移才会发生。
三、文献述评
1.国外学者的宏观经济角度分析述评。国外学者的宏观角度分析多在严格假设条件之下对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进行分析,这与中国实际国情并不相符。但随着理论的开展和持续研究,限制条件逐步放宽,虽然仍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却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解决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是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竞争前提下阐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忽视了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但该理论阐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较为接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为研究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和新方法;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强调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需要农业和剩余,这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城乡对立运动的一些客观规律,但它假定农业劳动者的工资不会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这显然与不事实符;托达罗模式引进了“期望收入”的概念来取代城市的实际收入,从而较好地解释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农村人口向城市化大规模转移与城市高失业率持续并存的现象,但该理论假定农村不存在剩余劳动力,这与人多地少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不相吻合;乔根森模型强调农业发展和技术进步,重视市场机制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作用,但它假设在存在农业剩余时,粮食需求收入弹性为零,这个显然与事实不符。
2.国外学者的微观经济角度述评。国外学者的微观角度则多从个人或者家庭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社会生活中的经济行为。贝克尔的家庭经济学合理的分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原因和目的,并为其提供了经济学理论依据,对研究单个个体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该理论以经济人为假设前提,并不符合现实情况;新迁移经济学虽然迄今为止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模型,但却其若干假设和观点为研究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转移问题提供了崭新的思路,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作出了合理的解释;“推―拉”模型从城乡两头考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较好地说明了转移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所需承载的压力和动力,对中国以及各个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政策选择仍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为发展中国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是研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不可或缺的理论。
参考文献:
[1]刘国光,等.现代市场经济实用知识[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2]W.A.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3]Lewis,W Arthur.A model of dualistic economic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4,(36):46-51.
[4]费景汉,C.拉尼斯.劳动力剩余读经机的发展[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5]王萍.国外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理论研究综述[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59-63.
[6]W.P.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
[7]谭崇台.发展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8]加里・斯坦利・贝克尔.家庭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篇5
关键词:劳动力迁移;拥挤成本;公共支出
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3.04.009
一、引 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乡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交流的深化,劳动力在地区之间的流动规模日益扩大。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规模高达2.6亿,占全部人口近20%,其中跨省流动人口8 500万。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东部地区的人口比重上升了2.41个百分点,而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比重都在下降[1]。虽然户籍政策限制了城市户籍人口的扩张,但是城市实际就业和居住的人口显著增长[2]。以上海市为例,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2010年全市常住人口中,外省市来沪常住人口占39%,与2000年相比,10年间增长了159.08%,年均增长率为9.99%[3]。大量的劳动力流入一方面给流入地区带来了丰富的人力资本,另一方面又造成了教育设施、社会治安、城市交通等这些准公共品的拥挤问题,给地方政府带来了潜在的财政压力。
在经典的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理论框架下,劳动力迁移与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收入再分配政策紧密相连。较早的Tiebout模型[4]探讨了居民可流动情况下的公共产品提供过程,认为居民根据地区间的支出-收益组合来选择居住地区,在提供不同公共服务的社区间自由流动可以充分显示他们对公共产品的偏好,通过“以脚投票”实现公共产品的最优配置。然而,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条件下,某一地区执行较有利的再分配政策会激励低收入者蜂拥而至,并迫使高收入者不断外迁,从而导致整个再分配水平的下降。考虑到上述因素,Musgrave和Oates[56]提出应该由中央政府来执行收入再分配职能。Boadway[7]进一步提出一个普遍适用的结论,即只要地方政府预算具有再分配职能,则高收入地区将因财政原因而吸引劳动力流动,从而拥有较多的人口;如果地方政府预算具有累进性,则存在劳动力向低收入地区流动的倾向。Aronson[8]认为这种因财政待遇差异而非要素价格差异所引起的人口流动会扩大原有的财政性不公平,并且还会产生资源配置的效率损失。
地方政府在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和收入再分配能力方面处于两难境地。在现实中,地方政府通常针对大规模的劳动力迁入采取两大类举措:一是使劳动力流动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从而增大他们的迁移成本;二是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对劳动力实行有差别的再分配政策,从而改变了他们的预期收入[9]。因此,劳动力迁移除了受到迁出和迁入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人口增长速度、工资水平、失业率和预期收入等多种因素影响之外,还受到政府公共政策的影响。
政府公共政策从两方面影响劳动力的迁移。一方面,政府的公共支出能够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提高劳动力的工资,劳动力将从流动中获益,增加了对劳动力迁移的激励。当然,随着劳动力的不断迁入,公共服务变得更拥挤[1011],公共支出对产出的贡献下降,劳动力工资水平下降,劳动力流入减少。另一方面,政府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延伸到公共预算的收入方面。迁入劳动力为政府公共支出提供融资,高的公共支出需要高的税率,这就降低了地区间工资(征税后的净工资)的差距,对劳动力迁移产生负向激励。这两种相反的效应同时起作用,哪种效应占优?即分析政府公共支出对迁移的净效应非常有意义。另一个问题是,政府公共政策对迁移率的影响在短期和长期是否相同?
财政分权经典文献主要通过总额税、转移支付和政府支出等工具改变要素所有者的净收入,从而决定劳动力迁移的机制。而本文基于政府在公共健康服务、教育和维修道路等方面的支出对生产率和工资有全局的影响,在迁移模型中把政府支出作为一种主要的生产要素引入到生产函数中,并考虑公共服务的拥挤效应,分析公共支出影响劳动迁移率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以及政府公共支出对劳动力迁移的短期影响和长期效应。
二、模型的基本框架
(一)基本假设
本文主要基于Barro的考虑政府支出的内生增长模型和Clemente等的劳动力迁移模型[1011]进行了分析,提出了4个基本假设。
假设1:一个经济区当中包括两个地区,一个是经济发达地区(本地),另一个是其他地区(外地)①,类似于Baldwin & Forslid给出的中心地区和地区[12]。经济发达地区由于技术先进和生产率水平高等原因,比其他地区工资高,因而吸引外地劳动力迁入。经济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是L,它的增长取决于自然人口增长(一个外生的增长率n)和内生的迁移率(mt=Mt/Lt。式中:M为流入的劳动力数量)②,tLt=nLt+MtLt=n+mi。
假设2:劳动力的迁移面临一定的迁移成本。假设迁移成本与其他地区的净工资(可以看作是迁移的机会成本)成正比,与经济发达地区的迁移率成正比。即:
式中:mc为迁移成本;τf为其他地区政府对工资收入的征税比率,wf为其他地区的工资水平。迁移成本对迁移率是递增的、凸的(ζ'>0,ζ″>0)。这个递增的关系反映了一些没有在模型中明确考虑的因素,例如交通成本、社会成本等。
假设3:资本在地区之间能够完全自由流动,各地区的利率是完全一致的。
假设4:增长是外生的。本文的聚焦点是有关迁移的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政策,而不是增长的机制。为了进一步简化模型,假设除发达地区之外的其他地区经济都达到稳态,经济增长速度更慢rfn。
(二)经济主体决策分析
下面逐一分析厂商、政府、消费者三个经济主体的决策。
1.厂商决策。按照Barro的思路,考虑到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够提高厂商的生产率,将政府的公共支出引入到生产函数中。厂商使用资本(K)、劳动力(L)和政府公共支出(G)这三种生产要素进行生产,采用的是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技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具有拥挤性。总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
式中:Y为产出;A为一个表示产出规模的参数,包含了固定要素(例如土地等)对产出的贡献,A>0;γ为外生的生产率增长;参数α和β分别为资本和政府公共支出的产出弹性,α>0,β>0,且α+β
式中:y=Y/L,k=K/L,g=G/L。
2.政府决策。地方政府通过对工资收入征收τ的比率税和发行公共债券D(赤字)为政府支出G进行融资。地方政府的预算达到平衡:D=G-τwL。
分别用和表示政府的公共债务水平和政府公共支出水平,都以相应变量占GDP的百分比来度量,其中=D/Y,=G/Y。总的工资额为wL=(1-α-β)Y,那么有:
式中:(1-α-β)-1可视为一个考虑了公共债务的更加宽泛的税率水平。
3.消费者决策。假设个人的收入来源于两个方面:工资收入与购买债券的收益。个人将其收入用来消费和储蓄,储蓄全部用来购买债券。根据预算约束,个人选择消费路径以实现福利最大化。由于本文考察的重点是劳动力的流动,因此假设固定要素(把资本和劳动力之外的产出都归为是固定要素带来的)的所有者是不流动的。假设经济发达地区初始的工资水平更高,(1-τ)w>(1-τf)wf,因此该地区的劳动力没有理由外迁(毕竟迁移有一定的成本),因此最优的迁移与其他地区的劳动力相联系。其他地区劳动力的决策不仅意味着消费的最优路径,还包括地点的选择。在时刻t,其他地区劳动力的问题可以归结为:
或者(1-τ)ws+rsbs-mcs=cs+s(如果他迁移到经济发达地区)
式中:u(cs)为效用函数;c为消费;ρ为跨期贴现率;b为债券持有额;为债券持有额的瞬时变化;r为债券的利率。
比较其他地区劳动力留在本地和迁移到发达地区两种情况,两种消费路径之间的差异可以通过工资流和迁移成本的差异给出[13]④。我们定义一个变量B,表示净工资差异的贴现流:
当这个值大于迁移成本时,其他地区劳动力迁移;小于迁移成本时,其他地区劳动力留在本地。因此,迁移的短期流动一直会持续下去,直到迁移成本等于收益:
三、短期、长期均衡和动态分析
假设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因此厂商支付给生产要素相应的边际产品价值。实际利率等于资本的边际产品,实际工资率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根据生产函数,可以得到:
根据式(5)和(6),把工资表示为人均公共支出和人口数量的函数,可以得到:
经济发达地区的工资水平随着人均公共支出的增加而增加,随着劳动供给的增加而减少(因为拥挤成本的产生)。
根据式(2),可以把均衡的工资水平表示为政府公共支出水平和人口数量的函数:
(一)工资比率和迁移率的动态变化
为了分析稳态和迁移的运动路径,首先考虑两大地区工资比率的变化。从式(8)中可以看到,发达地区的工资水平的动态变化为:
/w=[γ-η β(n+m)]/(1-α-β)
假设劳动力迁移不会对其他地区(流出地)的人口增长产生显著影响,则其他地区工资水平的动态变化是:
因此,相对工资比率wwf (发达地区工资比上其他地区工资)的动态行为方程为:
式(3)的迁移收益可以用相对工资比率重新表达为:
式(4)对时间t求导数,综合迁移收益和其他按地区工资水平的动态变化,可以推导出迁移率的动态变化:
式(11)可见,短期迁移率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经济发达地区和其他地区的相对工资率,相对税率,其他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经济增长率和利率、迁移成本、生产技术参数和拥挤效应。其中,工资、人口增长率、经济增长率、迁移成本这些因素在大多数文献中都进行了考虑。而利率、税率、生产技术参数和拥挤效应则是将政府公共支出引入到生产函数,并考虑公共服务的拥挤性后,影响到迁移率的一些新的因素,它们会对迁移过程产生暂时的加速或减速作用。
(二)相对工资和迁移率的长期均衡
相对工资和迁移率的长期均衡值可以根据式 (9)和式(11)在满足・=0和t=0时求解得到:
从迁移率的稳态值中可以得到以下几个结论:第一,长期的迁移率取决于四个因素,一是人口增长率,其他地区较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口增长率越大,迁移率越高;二是经济增长率,经济发达地区较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率越高,迁移率越高;三是生产的技术参数,政府公共支出对产出的弹性越小,迁移率越高;四是公共服务的拥挤性,公共服务的拥挤性程度越低,迁移率越高。第二,公共服务的拥挤程度 η和政府公共支出对产出的弹性β表明了政府活动在迁移中的重要作用。第三,长期的迁移模式独立于公共政策,不论是政府预算变量(公共支出、税收),还是直接针对迁移成本的管理措施,对长期的迁移率都没有影响。
(三)相位图分析
除稳态之外的经济的动态行为可以由工资率和迁移率二维度的微分方程组给出:
在式(14)中,设・=0,关于m求解,得到m=γ-γfηβ+nf-n(・=0曲线的方程)。这个迁移率正好等于长期均衡的迁移率m*,也是唯一的实现工资比率稳定的迁移率。・=0曲线与横坐标轴垂直。
在(15)式中,设=0,关于求解,得到=1-τf1-τ[1+(r-γf-ηβnf1-α-β)ζ(m)](=0曲线的方程)。迁移成本函数对m是递增的,因此=0曲线是一条上升的曲线。见图1。
图1 相位图和稳态
为了找到流水线应该具有的一般方向,对式(9)和式(11)的两个方程求偏导数,得到:
根据式(16),当m增加时,・应经历(+,0,-)的符号序列。所以箭头在・=0曲线左方时应指向上方,而在右方时应指向下方。
根据式(17),当增加时,应经历(+,0,-)的符号序列。所以m箭头在=0曲线下方时应指向右方,而在上方时应指向左方。
按照这种箭头会出的流水线给出了一个鞍点均衡。长期均衡的稳态特征可以通过检验雅克比矩阵得到⑤。它的迹TrJ=rf-γf-ηβnf1-α-β>0;而行列式DetJ=-(1-τ)ηβ*(1-α-β)ζ′(m*)
图1表明,经济沿着斜率为正的稳定分支接近稳态。当经济发达地区初始的相对工资高于稳态值时,导致了比稳态更高的迁移率;而更高的迁移率使相对工资率的增加为负,逐渐削弱了相对工资的优势。当工资的差距下降时,迁移率也下降,直到达到稳态值。相反,一个较低的初始相对工资与一个低的迁移率相对应。然而,经济发达地区的生产率增长更快,使得相对工资率上升,这又加速了劳动力流入。在经济向长期均衡移动的过程中,迁移率和相对工资率都会上升。
经济发达地区增加迁移成本的公共政策对迁移率会有什么影响呢?假设迁移的收益不变,迁移成本的增加使得对迁移的激励减弱,导致迁移率的突然下降。之后,经济沿着新的稳定分支移动,直到达到新的长期均衡。见图2。
图2 迁移成本增加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
增加迁移成本的政策虽然对迁移率造成短暂的下降效应,但是长期的迁移率并没有改变。事实上,最终的迁移是经济结构差异的结果,阻止永久迁移的政策应该着力于消除生产率增长的差距,以及人口增长方面的差距。正如我们从动态系统中看到的一样,提高外地的生产率或者降低人口增长率,降低了其对迁移的激励效应。如果外地最终达到了本地的生产率增长和人口增长,那么迁移的激励就消失了。但是,由于更高的迁移成本,新稳态下的工资比率也变得更高,因此,更高的迁移成本对工资差距和人口规模有永久的效应。
四、政府公共支出政策对迁移和人口规模的影响
前文的分析已经得出结论,长期的迁移率独立于公共政策,不论是政府预算变量(公共支出和税收),还是直接针对迁移成本的管理措施,对长期的迁移率都没有影响。那么,是否意味着可以忽略政府对迁移的作用呢?政府的公共支出政策对短期的迁移率和本地的人口规模是否有影响?
政府支出增加了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因此对劳动力的流入产生正向激励效应。另一方面,给定公共债务水平,更高的政府支出意味着更高的税率水平,从而个人的税后净收入和效用水平更低,对劳动力的流入产生负向激励效应。因此,需要进一步讨论占主导地位的效应,或者净效应。而且,还应该考虑到移民的进入会增加税收总额,因而增加了政府的支出能力。
从式(11)可以看到,提高本地税率τ会暂时产生对迁移的负向激励,这和更高的迁移成本的作用类似。因此,政府公共支出政策确实对累积的迁移流动和本地的人口规模有重要的影响。
为了考察这个问题,可以把稳态下的本地工资的稳态路径表示为:
根据等式=-τ(1-α-β),式(12)的长期工资比率可以表示为:
把式(19)代入到式(8)中,求解L,得到人口规模的方程为:
为了分析税收或者政府规模对人口规模的影响,我们定义标准化的人口规模为L*n=L*te-(n+m*)t。这个变量将稳态下的经济政策效应和人口增长效应分离开来。因此,更高水平的标准化人口规模反映了更多的劳动力流入,反之亦然。结合式(19)中的长期相对工资率的表达式和式(20),我们可以计算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对标准化的人口规模的弹性为:
弹性的符号取决于和β1-α(1-α-β+)之差,而两者的大小关系并不明确。因此,政府规模和迁移之间的关系不是单调的。当政府公共债务占GDP的份额一定时,在政府公共支出较小的地区,公共支出的增加对瞬时迁移率增加有一个激励效应。因为此时公共支出对工资的生产率效应超过了税收效应。在政府规模较大时,公共支出的增加的税收效应超过了对工资的生产率效应,对瞬时迁移率增加有一个负向激励效应。在临界点处,两种效应正好相等,政府规模=β1-α(1-α-β+)时,标准化的人口规模达到最大。政府公共支出水平和标准化的人口规模呈现为倒U形曲线,见图3。
图3 政府公共支出水平和标准化的人口规模
公共债务占GDP的比率越大,说明通过税收融资的政府支出份额越小,税收对迁移带来的负面激励效应更弱,此时临界值就越大。
另外,在其他情况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政府公共支出对累积的迁移的效应与公共产品服务的拥挤程度η负相关。当公共服务高度拥挤的时候,外地劳动力的进入很快降低了,因为政府支出增加带来的生产收益。因此,在早期移民进入之后,其他劳动力进一步迁入的激励就消失了。
篇6
关键词:新迁移经济学;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适用性
农村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转移是各国经济发展中的普遍现象。农村劳动力的乡城迁移更是中国经济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如何理解农村劳动力转移这种行为?许多专家学者对该行为进行了探索与研究,建立了相关的理论或者模型。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新迁移经济学。
一、新迁移经济学分析思路的基本前提
根据Stark(1991)的论述,新迁移经济学建立在四个基本前提之上。
1.迁移决策并不是独立的个体行为,而是更多相关的人组成的一个更大的单位——通常是家族或者是家庭的行为。与新古典迁移理论把迁移决策作为独立的个体行为不一样,新迁移经济学将迁移研究的关注点由独立的个人转向了相互依赖的个人。如此以来,家庭内部的一些行为(如汇款行为)就被纳入了迁移理论的研究范围,而且,在分析劳动力市场时,迁移者的行为和绩效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迁移者家庭的偏好和家庭的约束来加以解释。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主要目标不仅仅是预期收入最大化,同时也为了最小化家庭风险。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城乡之间存在工资收入的差异,还存在着其他能够引起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因素,比如,农业部门受到恶劣的气候因素影响,农产品歉收,家庭的农业收入大幅下降,家庭还可以从迁移者那里获得工资性收入(通常是以汇款的方式)以补偿农业歉收的损失。从根本上来说,劳动力的迁移并不像水的流动那样,必然从高处流向低处。在完善且健全的市场体系和金融制度之下,大量的迁移现象将不会发生。新迁移理论指出,在发达国家,家庭的风险通常由保险公司或者政府项目得到保障,但发展中国家还缺乏完善、成熟的保险市场,这使得家庭不得不通过将劳动力配置在不同的市场以分散风险;同时,发达国家拥有相对发达的资本信贷市场,家庭获得投资启动资金的代价较小,可能性较大,而这在发展中国家是不可能或不能轻易实现的。在现实生活中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的诸如信息不对称、外部性等问题,比如,居住在偏远落后地区的农村居民无法了解到发达地区某项产业的发展状况,那么,对于这样的家庭来说就有了迁移的欲望。决策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人们总是把自己的收入与一定的群体相比较,由此会产生一定的满足或者失落感。新迁移理论认为,家庭决定其成员的迁移,不只是为了提高其绝对收入,同时,也是为了提高相对于其他家庭的收入,也就是为了减轻在某一参照系内的相对贫困感。人总是有与周围的人作比较的心理,如看到邻居迁移到城市后致富了,自己也就有了迁移的动机。
新迁移经济学试图以上述四个前提为基础解释农村劳动力迁移问题。该理论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在更广阔、更复杂、更真实的背景下讨论迁移行为,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其主要思想是:在发展中国家,农户通过家庭成员的迁移,克服了家庭改造、升级生产技术中的两个主要的障碍,即投资资金的匮乏(信贷市场的约束)及风险规避工具的短缺(保险市场的约束)。解释了家庭这样的主体为什么、在什么时候会发现最有利的时机,在若干市场上采取战略性的行为,并在这些市场间进行劳动力分配,使其行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出现。
二、新迁移经济学四大基本前提的合理性及其在我国的适用性
上述新迁移经济学的四大基本前提,与我国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一些特点比较吻合。
(一)关于迁移的决策主体
新古典迁移理论或者模型都将迁移者个人作为迁移决策的主体。这种假设前提,往往是不符合现实情况的。新迁移经济学与其他迁移理论不同的关键点就在于它认为迁移决策不是由孤立的个人单独作出的,而是由相互联系的人所构成的较大的单位(如家庭或家户)作出的。不同迁移决策主体的假设,对于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政策的设计和政策的实施效应是有着直接影响的。
在现实中,农村劳动力的乡城转移决策通常是由转移者和非转移者群体(其他家庭成员)联合作出的。而转移的成本和收益是按照转移者和非转移者群体之间隐含的契约安排中所规定的分配规则在二者之间被共担/共享的。例如,家庭转移成员转移需要的车旅费以及生活费都是家庭非转移成员提供的,而转移成员获得收入后常以汇款的方式寄回家。新迁移理论的出发点由独立的人变成相互联系的人,即它将迁移看作是一种“有意识的战略”,而不是一种绝望的或盲目乐观的行动。
将家庭而不是个人置于迁移决策的中心是一个比较新的思路(当然这不一定非得意味着家庭成员全部迁移)。这种理论并不是忽略迁移个体行为,而是把个体迁移行为作为分析的基础置于迁移框架之内。家庭可以被看作是某种“联盟”——一个由面对周围的世界彼此承诺采取统一行动的单位。而家庭成员的迁移可以被看作是家庭生命力的宣示:用空间或范围经济替代限制相互保障能力提高的规模不经济。
由我国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过程中的一些特点可知,把相互联系的人(如家庭或家户)作为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的决策主体在我国更具合理性。这些特点包括:第一,在我国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人们普遍有强烈的传统家庭观念。第二,我国农村地区的强化了农户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地位。第三,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与其留在农村地区的家庭之间存在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在一项调查中发现,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当中,82%的人定期给农村家庭汇款,95%的人每年至少回农村家里看望一次(蔡昉,1996)。第四,根据近几年许多新闻媒体的报道,越来越多的参与乡城迁移或转移的农民工在城市地区工作一段时间、有了一定的积蓄、学到相应的知识或技术后,纷纷返回家乡创业。这些特点充分显示了转移到城市的农民个人与其在农村的家庭之间密切的生产生活联系,也证明了农户作为决策主体的正确性。
(二)关于迁移的动机
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动机究竟是什么?仅仅是预期收入最大化吗?对此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在家庭里,人们集体行动以求不仅最大化其预期收入,而且最小化其风险并缓解与除劳动力市场之外的各种各样的市场失败相关联的各种约束(Stark and Levhari,1982;Stark,1984;Katz and Stark, 1986;Lauby and Stark,1988;Taylor,1986)。如果迁移者仅仅是追求其预期收入最大化,那么,当城市预期工资收入与农村工资水平之间的差异为零时就不存在农村劳动力乡城迁移。
在我国现实中,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城乡之间存在工资收入的差异,还存在着其他能够引起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因素,转移的目的也是为了分散家庭风险,使其风险最小化。正如投资某个项目一样,人力资本的分散投资也是为了规避风险。从严格意义上说,当个体是风险厌恶型时,他通常宁可接受当前某一确定的工资也不愿意接受与当前收入数额相等的一个含不确定的预期收入,于是工资零差异可能带来农民由城市到农村的回流;而当他是风险中性或者偏好时,并且他对闲暇附加了一定的价值,那么,即便城乡工资差异为零,迁移仍有可能。简单地说,给定一个农村部门的工资水平Wr和一个更高的城市部门的工资水平Wu(假设从事城市部门工作的概率为p),并假设在两个部门中的标准工作时间都是S,更具体地说,假设在农业部门工作S天可获得Wr的收入,而在城市部门工作S天则可获得Wu,即便pWu-Wr=0的情况下,农村部门的闲暇与工资搭配(0,Wr)则取决于城市部门的闲暇与工资搭配的状况[(1-p)S,pWu],从而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迁移就会发生(Stark,1982)。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主要目标不仅仅是预期收入最大化,同时也为了最小化家庭风险。
(三)关于市场制度、金融制度与迁移的关系
新迁移经济学第三个假设前提告诉我们如果市场体系和市场制度是完全的且完善的,大量的迁移现象将不会发生。我国市场制度和金融制度的不完整、不完善是目前经济领域的一个显着特征,这种不完整、不完善对于农村家庭的劳动力使用上、从而对农村劳动力的乡城转移上必然产生一定的影响。具体来看:
1.农作物保险市场
无论什么时候,当一个农户家庭将时间和金钱投入到播种某种作物上时,他们总是寄希望于其投入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以产品的形式得到补偿,他们可以将这些产品卖掉换成现金以购买其所需要的其他物品,也可以将这些产品用于农户家庭的消费。但是由于存在不确定性,比如恶劣的气候因素有可能会导致农产品的减产甚至绝产,从而使得农户家庭面临收入减少甚至难以维持生计的风险。同样地,新的农业技术的引入(诸如高产良种或者新的耕作方式等)也可以改变农户所面临的风险。如果农业技术专家的意见是正确的,使用新的改良种子可以增加农民的产出;如果农业专家的意见是错误的,农户便面临着将来食物或收入不足的风险。在发达国家,这一类的主观和客观风险是通过正规的保险体系来解决的。在这种保险体系下,农业生产者向保险公司或政府机构交一定的费用获得相应的保险,以求在将来农业生产遇到损失时获得相应的补偿。一旦将来在生产过程中农户遇到诸如干旱、洪水、新技术推广失败等风险,保险机构将按照所保险的农作物市场价值赔偿农户的损失,从而确保农户的经济福利不至因此而降低。如果农作物保险无法得到,农户就会倾向于通过将一个或更多的劳动力转移出去的方式来实现自我保障,以确保在即便出现收成下降的情况下家庭收入不致降低。资本市场
许多农村家庭除了追求现金收入、经营收入最大化外,同时也希望增加其资产的生产率,为此他们首先需要获得用于追加投资的资本。比如,农户会希望灌溉农田、施用化肥、购买良种、购买机械等,但他们可能同时缺乏用于购买这些投入要素的货币。非农民家庭会希望投资于家庭成员的教育或培训、寻求获得资本品用以生产某种能够在消费品市场上销售的商品,但是他们也可能缺乏用于这些方面的投入的货币。在发达国家,投资要么来源于私人储蓄,要么来源于借贷。储蓄也好,借贷也好,都取决于你能否顺利进入一个健康的有效率的银行系统。如果收入有波动,借贷还可以帮助抵御消费风险。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储蓄制度是不稳定的或不发达的,借贷也是很困难的。这或者是因为农户家庭通常缺乏获得贷款的担保,或者是因为借贷资本的短缺,或者是因为银行系统的服务范围有限等。对于低收入的农民家庭来说,唯一的能够获得贷款的渠道通常是来自于当地的高利贷者,这种高利贷由于交易费用高昂而令人望而却步。在这种情况下,迁移再一次被视作获得资本来源的一个有吸引力的渠道,以求通过它积累资本用于改善生产效率、稳定消费水平。因此,处在这种处境中的家庭此时具有很强的将其某个家庭成员转出农业生产领域、迁移至城市地区以增加储蓄并通过往回汇款的方式将资本转移回家庭的强烈动机。期货市场
无论什么时候,一个农户在播种时总是期望所播种的作物在将来收获后会按照一个理想的、足以能够获得养家糊口甚至改善家庭福利状况的收入的价格出售。但是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却始终存在着农作物价格跌至期望水平以下,从而导致家庭歉收的风险。在发达国家里,价格风险是通过期货市场加以控制的。通过期货市场,农户可以按照现在确定下来的价格在将来出售其全部或部分农产品。如果未来价格跌至约定价格以下,则投资者承担损失;如果未来价格升至约定价格以上,则投资者获得盈余。许多发展中国家要么不存在期货市场,要么虽然存在但低收入的农户通常无法进入,在这种情况下,迁移就提供了一种农户自我保险、抵御由农产品未来价格波动而导致的收入风险的机制。社会保障
无论是农民家庭还是非农民家庭,都靠家庭成员的收入维持。如果当地的经济状况恶化、就业率下降,家庭的生活状况就会由于收入的减少而受到威胁。在许多国家里,政府设立了相应的保障体系以保护劳动者及其家庭免遭这种风险。但是在发展中国家里,这种针对失业者和伤病者的保险体系往往是不存在的或不完整的,这同样促使农户家庭将其劳动力转移出农村地区以求实现自我保障。而在我国,农民几乎享受不到真正的社会保障,这一因素对于农村劳动力的乡城转移不可能不产生任何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迁移就使得农民减缓了这一风险。
(四)社会环境与迁移的关系
新迁移理论认为,家庭决定其成员的迁移,不只是为了提高其绝对收入,同时,也为了提高相对于其他家庭的收入,也就是为了减轻在某一参照群体内的相对贫困感。即RD(relative deprivation)动机,即相对剥夺、相对经济地位变化、相对贫困(蔡昉、都阳,2002),以下都称做RD。农村家庭之所以将某个家庭成员送出所在的地方、加入迁移的行列,其目的既是为了增加其绝对收入,也是为了改善家庭的相对收入水平(即相对于其他家庭的收入水平),从而降低其与其他参照群体相比的相对贫困程度(Stark,Taylor and Yitzhaki,1986;Stark and Yitzhaki,1988;Stark and Taylor,1989,1991;Stark,1991)。以Stark为代表的新迁移学者首先提出并完善了农村乡城转移的RD模型。他们认为单位i的效用Ui=U(Yi,RDi),其中Ui表示其效用,Yi表示其绝对收入,RDi衡量其因收入低于一定水平而带来的相对失落。由效用对绝对收入、相对贫困的偏导可知,效用随着其绝对收入的增加而增加,随着RD的增加而减少。假设F(y)为累积收入分布, 而h[1 - F(y)]代表一个家庭在y收入水平下由于不能得到稍高于y的收入水平(比如说是y +Δ) 而产生的不满足感,那么,该家庭在收入水平y下的相对贫困程度便可概念性地表示为:
RD(y)=h[1-F(x)]dx,令b=yh
在h[1-F(y)]=1-F(y)的特殊情况下,这一表达式等同于以下两项的乘积:收入水平高于y的家庭的比例、这些较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与y之间的平均差距(额)。
RD模型的核心思想就在于收入给个体带来的效用不仅在于绝对收入是多少,也在于该收入在特定参照群体内的位置,即人们总是把自己的收入与特定群体内的他人的收入比较。该思想更贴近中国的实际。
为了进一步理解相对收入这一概念,我们假设富裕家庭的收入有所增加。如果贫困家庭的收入不变,那么贫困家庭的相对贫困程度增加。如果家庭的效用与相对贫困程度呈负相关,那么,即便贫困家庭的绝对收入和迁移后的预期收入保持不变,只要通过其家庭成员的迁移可以改善其在所处参照群体中的相对收入水平,该家庭参与迁移的动机依然会增强。由此可以说,由于其他家庭的收入水平的变化,该家庭参与迁移的概率会增加。制约了贫困家庭增加收入的机会的种种市场失败也会增加迁移对贫困家庭的吸引力,因为此时通过迁移贫困家庭可以改善其相对收入状况。
相对收入(贫困)因素在我国的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过程中也能够找到相应的佐证。在我国的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过程中,虽然农村地区各类家庭的总体收入水平与城市平均收入水平都有着较大的差距,但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参与转移的农民工中,在参与转移前其家庭在农村中处于低收入水平的人占了大多数。这说明迁移与原本农民家庭在农村的相对收入水平是有着相当明显的联系的,也说明农村劳动力在向城市地区转移时在其转移动机中是有着较强的对家庭相对收入水平(或相对贫困状况)的考虑的。
从上述四个方面的具体分析来看,新迁移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前提与我国农村及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实际情况是基本吻合的。在这些前提下,沿着新迁移经济学的思路来分析我国的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问题,应该说不存在什么难以逾越的理论和逻辑障碍。
三、对待新迁移经济学分析思路应有的态度
在运用一种理论分析我国现实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对它采取科学的态度,既要坚持又要发展的态度。最近几年来,我国劳动力转移势头较猛,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理论或者模型致力于解释这种行为。而新迁移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也就引起了国内外迁移理论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根据以上新迁移理论与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适用性分析,我们在运用这一理论分析我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时,有如下几个方面是需要明确的:
第一,新迁移经济学与新古典迁移理论关键性的区别有两个,一是迁移决策主体的不同,二是迁移动机的不同。其他各方面的差异包括政策含义的不同都是由这两点衍生出来的。其中,迁移动机的假设不同,是导致新迁移经济学区别于其他迁移经济学理论流派的最具决定性的因素。
第二,新迁移经济学在理论前提、相关假设方面与我国国情的高度吻合决定了它对于分析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问题有较强的适用性。但是,它并不是为中国劳动力转移问题提供了具体的分析方法,因此我们在分析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行为时,不能照抄照搬,只能以新迁移经济学提供的分析方法为指导,对我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第三,任何一个经济理论都不能包罗经济世界的全部现象,新迁移经济学也不例外,我们在用新迁移经济理论指导我国的实践时,同时,也要学会借鉴其他迁移理论的科学方面,将此结合起来,用来更好地指导我国的实践。
:
[1] Stark,Oded (1991) The Migration of Labor. Cambridge an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Stark, Oded and D. Levhari(1982)“On Migration and Risk in LDC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Change 31:p191-196.
Stark,Oded (1984) “Bargaining, Altruism and Dmographic Phenome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Review 10: 679-92.
Stark,Oded, J. Edward Ta℡∫∫ylor, and Shlomo Yitzhaki(1986) “Remittances and Inequality” The EconomicJournal 96: p722-740.
Stark,Oded, J. Edward Taylor, and Shlomo Yitzhaki(1988)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Inequality: A Sensitivity Analysis Using the Extended Gini Index”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8: p309-322.
Stark,Oded(1982) “Rural-Urban Migration and Surplus Labour: Reservations on Bhatia.” Oxford EconomicPapers 34:569-73
Stark,Oded, J. Edward Taylor, and Shlomo Yitzhaki(1986) “Remittances and Inequality” The EconomicJournal 96: p722-740.
Stark,Oded and Shlomo Yitzhaki(1988) “Labor Migration as a Response to Relative Deprivation”,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1: p57-70.
Stark,Oded and J. Edward Taylor(1989)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Demography 26: p1-14.
[10] Stark,Oded and J. Edward Taylor(1991) “Migration Incentives, Migration Types: The Rol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The Economic Journal 101: p1163-1178.
[11] Taylor,J. Edward (1986) “Differential Migration, Networks, Information and Risk”. in Oded Stark (ed.) “Rsearch in Human Capital and Development”, Vol. 4,Migration,Human Capital, and Development.Greenwich,Conn.: JAL Press, p147-171.
篇7
关键词:家庭分工;劳动力数量;可替代收入渠道;务工;务农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3-0090-07
从理论逻辑上看,农村居民选择在家乡务农,还是选择进城务工,对于一个国家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农村居民务农是保证农业持续发展,特别是粮食生产稳定的基础性条件;另一方面,农村居民进城务工是工业化生产劳动力需求的主要来源,也是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决定性因素。从社会现实角度看,近年来,中国国内的农民流动又出现了一个近似悖论的现象,那就是,“农民种地不赚钱已经成为一种相对性的社会事实”,但东南沿海工业城市却出现“民工荒”,大量农民工选择返乡务农,出现了农民工“回流”现象。这些都让我们不得不思考: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样的现象?或者说,是什么因素影响农村居民在务农与务工之间作出选择?
一、文献回顾
已有的研究对农村居民务农务工选择的探讨,就宏观层面而言,主要是照搬或沿袭西方学者的研究路径,来讨论和考察影响城乡人口流动的因素。简单地,可以把这些讨论大体上分为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主要强调城乡收入差异对于农村居民城乡流动的决定性作用。如托达罗认为有两点对于农村居民迁移到城市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城市真实收入差距,二是获得城镇工作的概率。这二者相结合可以理解为农村居民迁入城市的预期收入,如果长期预期收入低于农业生产的收入,农民就不会迁入城市,做定居计划,即使是进城务工的农民也不得不像钟摆一样,选择“往返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第二种观点,主要强调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与数量多寡对于农村人口城乡流动的影响,认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是农民进城务工的前提。围绕现在中国农村劳动力剩余数量有多少,或者说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的问题,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的讨论,以蔡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已经不多,刘易斯转折点已经来临。
这些宏观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就近期形势,特别是国内工业化发展水平来看,要想让农村居民迅速市民化还存在诸多的困难,尤其是存在工业化水平相对较低、城镇就业岗位相对不足和劳动力市场分割所造成的务工收入不足问题。所以,避开乡一城移民的视角,直接从微观层面研究现阶段中国农村居民的务农务工选择也许更具有现实重要性。令人可喜的是,国内学者已经开始着手这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虽然采用了不同的理论视角,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但得出了一个相近的研究结论,即务农收入和务工收入差距是决定农村居民选择务农还是务工的关键原因。
综合来看,已有研究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已有的文献研究均未能意识到城乡收入差异仅仅是影响农村居民选择务工还是务农的一个方面,而且,城乡收入差异并不能很好的解释近年来的农民工“回流”现象。第二,已有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个体决策的视角来分析农村居民的务农与务工选择问题,而未能认识到家庭分工对农村居民外出务工的制约;同时,这些研究对农村劳动力剩余数量估算,无论是采用何种理论依据,使用何种估算法,都是对农村总体剩余劳动力数量的估算,而未能从家庭分工的视角,以家庭为单位进行估算。但在中国下,家家有田种,家庭作为一个经济、政治和精神共同体,劳动力的分配必须满足每个家庭分工的需要,所以农村劳动力剩余的计算必须以家庭为单位,即考察家庭劳动力数量的影响。第三,已有的定量研究均采用地方性的,比如某个省市的数据作为数据分析的基础,缺乏利用全国性的大型调查数据作为支持,存在样本代表性不足的问题。
综合已有相关研究的成果和不足,我们需要用一个比城乡收入差异更为宏大的概念来理解农村居民务工与务农的选择,这个概念就是“可替代收入渠道”。本文中,笔者把可替代收入渠道定义为:除了从事农业生产以外,特别是在城市中可能取得的,可以替代农业生产的,为农民提供稳定经济收益和养老、医疗保障的收入渠道。本文将利用全国性的调查数据,采纳家庭分工的视角,主要考察农村“家庭劳动力剩余”和“可替代收入渠道”对于我国农村居民务农务工选择的影响。此外,基于移民健康效应理论,笔者还将考察“移民健康效应”在农村居民务农务工选择中的影响。
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由于每个农村家庭农业生产劳动力需求标准的不确定性,我们不去评估和考察每个家庭在满足农业生产之外的剩余劳动力数量,而是通过考察每个家庭劳动力数量与农村居民务工务农选择之间的关联,来间接考察家庭剩余劳动力数量与农村居民务农与务工选择之间的关联。
二、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
1.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所主持的中国社会综合调查2010年(CGSS 2010)数据。去除“非农业户口”、“蓝印户口”、“居民户口”、“城镇户口”个案,有“农业户口”个案6040个;同时,凡回答“不知道”、“不适用”、“不回答”和“其他应答而未回答的情况”删除,再删除每一变量中的缺失数据值,最终剩余有效个案2044个。基于CGSS 2010采用的是多阶段分层概率抽样方法,分层是外生的,不同省份的居民进入样本的概率是不同的,为此,在本文中我们依据“地区”对数据进行加权处理,处理后的最终有效个案为4763个。
2.变量统计描述
(1)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为“务农与务工选择”。这是一个比城乡人口迁移更为宽泛的概念,它不仅包含那些流动人口,也包含那些固守在农村进行农业生产的居民群体。在CGSS 2010年的调查问卷中有这样一道题目:“您工作经历及状况是?”问卷答案选项情况如表1。
在表1中,我们看到有过或正在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村居民不到1/3,一直在农村务农的居民占绝大多数,这就提醒我们,仅仅分析农民工的务农务工选择,或者说回流现象,不利于我们从整体上认识中国农村居民城市化迁移的困境。
(2)自变量。本研究的自变量主要有两个。一是“可替代收入渠道”。在问卷中有这样一道问题:“您务农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选项赋值情况如下:1=目前务农收入还比较理想;2=务工收入和务农收入差不多;3=没有其他收入渠道,只能务农;4=有其他收入,务农不是主要收入。绝大部分人选择了“没有其他收入渠道,只能务农”,即“可替代收入渠道缺乏”是农村居民选择务农的最重要原因。二是“家庭劳动力数量”。在问卷中:“请您谈谈您家目前的劳动力情况(在这里,家指的是与被访者在同一个户口本上的所有人)”,其中,第一个小问题是:“16~65岁有劳动能力的人有多少人”。这个问题主要用来测量每个农村家庭现有劳动力的数量。基于家庭分工对劳动力供给的制约,“当留守劳动力较多时,家庭劳动可以更多地由其他成员来承担,非市场型劳动对收入的替代作用就会比较强,劳动供给意愿也比较强;相反,如果留守劳动力少,家庭劳动无人承担,劳动供给意愿就会比较弱”。所以,每个家庭现有劳动力数量应该是决定农村居民务农务工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
(3)控制变量。主要是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婚姻状况、身体健康状况等人口特征变量。其中“年龄”和“健康状况”的重要性有必要予以特别强调。就年龄来看,劳动经济学理论认为年龄是劳动力迁移的重要因素,20~24岁是劳动力流动的高峰,劳动者年龄越大,流动性越低。这主要是基于三点:一是把劳动力迁移、进城务工看做是一项人力资本投资,认为年龄越小,其工作时间越长,收益时间也就越长,在这项人力资本投资中所获得收益现值越大。二是迁移的心理成本理论,认为迁移会丧失原有的社会网络、社会资本,年龄越大的人,社会互动的需要越大,这样,与迁移相关的心理成本越大。三是,笔者认为,对于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年轻人生活在改革开放以后,对自己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有着比父辈更高的期望,他们向往城市的现代化生活方式,其向城市迁移和进城务工的愿望也就更强烈。就身体健康状况而言,已有的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存在移民健康效应,即新迁移人口的平均身体健康状况要好于迁入地人口的身体健康状况,“身体更健康(更年轻、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个人更倾向于自我寻求迁移”。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而言,他们背井离乡、缺乏家人邻里的社会网络支持,而且与在家乡务农相比,在城市务工工作强度往往比较高,所以,一个合理的逻辑推理是身体健康是农村居民选择进城务工的基础性条件之一。此外,基于照顾依赖性人口的需要和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社会事实,我们也把“未成年子女数量”、“老人数量”和“地区”作为必要的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具体情况见表2。
三、实证模型与分析结果
1.实证模型
笔者以可替代收入渠道和家庭劳动力数量两个因素作为分析框架,建立模型。由于因变量属于多分类无序变量,且变量赋值分为三类,所以宜采用Multinomial Logistic模型来分析。模型一般形式如下:
其中,P1、P2、P3分别为“目前从事非农工作”、“目前务农,曾经有过非农工作”、“目前务农,没有过非农工作”的概率;模型中以第1类“目前从事非农工作”为基准,P1+P2+P3=1。Xi分别为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婚姻状况、身体健康状况等个体特征变量,以及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老人数量和(东、中、西)地区等控制变量;Xj为“家庭劳动力数量”和“可替代收入渠道”两个自变量;β1t、β2j、θ1j和θ2j为系数;αi为截距,i=1,2。
2.统计检验与结果分析
如表3所示,模型AI中,就“目前务农,曾经有过非农工作”与“目前从事非农工作”群体相比较而言,年龄越大的农村居民,越可能选择回乡务农;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选择务工;女性选择务农的比例更高;未成年子女数量越多,选择外出务工的可能性越高。婚姻状况和健康状况则对务农与务工选择没有显著性的影响。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越多,农村居民越容易选择务工;但家庭老年人数量对于农村居民的选择却没有显著性的影响。就东、西部地区的比较来看,确如理论所推测的那样,西部农村居民务农的可能性更高;但就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比较来看,中部地区的农村居民务农的倾向性却更高,显著性水平小于0.05;这可能是源于中部地区的自然条件更适合农业生产,农业收入较西部地区更高的原因造成的。“可替代收入渠道”和“家庭劳动力数量”对农村居民务农选择都存在显著性的影响。具体来看,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农村居民选择务工的可能性越大;与“务农并非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相比,认为“务农收入比务工收入有优势”和“没有其他收入渠道,只能务农”家庭的农村居民更容易选择回乡务农。
模型AII中,就“目前务农,没有过非农工作”与“目前从事非农工作”相比较,年龄、性别、教育程度、身体健康状况、家庭年收入、未成年子女数量、地区等控制变量的影响与模型AI的影响是一致的,只存在系数大小和显著性水平的差异。但婚姻状况的影响有些不同,“离婚或丧偶”的农村居民更可能选择务工。就自变量来看,“可替代收入渠道”和“家庭劳动力数量”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水平都是与模型AI比较接近的,也只是存在系数大小和显著性水平的微小差异。
综合模型AI和AII,我们不难看出,“可替代收入渠道假设”和“家庭劳动力剩余假设”都得到了证实。可替代收入渠道缺乏和基于家庭分工制约的农村家庭劳动力相对不足才是中国农村居民选择务农和留在农村的关键影响因素。一方面,对于曾经有过进城务工经验的群体而言,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少,他们选择“务农”的倾向越高,这说明农民工选择“回流”务农很大程度上源于家庭劳动剩余条件下的供给不足。同时,与“务农并非主要收入来源”群体相比较,认为“务农收入比务工收入有优势”的群体也更可能选择务农,这意味着城乡收入差异也是影响农村居民务农务工选择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模型AII中“收入渠道”的两个系数值和“家庭劳动力数量”的系数均比模型AI更大,其统计结果显著性水平更高,显著性水平均为0.000。再综合前面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有77.2%的应答者选择“没有其他收入渠道,只能务农”,这充分说明“可替代收入渠道”的缺乏是农村居民选择务农,或者说不能进城务工的最关键影响因素。
同时,只有在“目前务农,没有过非农工作经历”与“目前从事非农工作”的比较中,个体健康状况才有影响,不健康的农村居民倾向于务农,健康的农村居民倾向于务工。个体健康状况对于中国农村居民选择在农村务农,还是进城务工的影响并不是很明确,这可能是由于统计数据误差或者其他不明原因造成的,移民健康效应的存在也还有待进一步的检验。
就控制变量来看,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个体特征值对于当前我国农村居民务农务工选择有着显著性的影响。就年龄而言,年青一代处于个体生命历程的早期阶段,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有着更高的期望,他们期望自己未来能过上城市居民的更优质生活,所以更可能选择进城务工;张同升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就性别而言,女性比男性选择务农的比例更高,笔者认为这可能与“男主外、女主内”的文化传统有莫大关系。就教育程度而言,教育程度高的农村居民,其在城市务工谋生的成本相对更低,在城市获得工作的机会也更多。这与劳动经济学理论的认识是一致的,对于同龄群体中哪些人更容易迁移,更可能进城务工,教育是一个最好的指标。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具有较高的迁移率,即进城务工的可能性更高。但婚姻状况对于农村居民选择在家务农,还是进城务工并没有显著性的影响,这与已有的研究有些出入。有学者研究认为“已婚农民外出打工成本非常高,已婚农民退出或不参与城市农民工劳动力市场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和民工荒并存的主要原因”,但这在本文中并没有得到证实。此外,令人奇怪的是,老人数量对于农村居民务农与务工选择没有显著性的影响;未成年子女数量虽然有显著性的影响,但统计研究发现未成年子女数量越多,农村居民选择外出务工的倾向也越高,这与照料未成年人和老人的需要会制约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理论推测截然相反。这些不一致,可能是由于样本数据的差异造成的,也可能是其他原因造成的,这都需要以后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篇8
关键词:农业劳动力转移;回流;贴现
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建立了二元经济模型。但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与“二元经济模型”并不完全相符,出现了特殊的现象:由于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而城市吸纳劳动力的能力相对有限,带来了大量的城市失业人口。
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诞生了托达罗模型。该模型认为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其他部门的主要动因不是农业部门与其他部门间(或城乡间)的实际收入差距,而是部门(或城乡)间的预期城乡收入贴现值的差(托达罗,1985)。用公式表示如下:
上式中,S表示净的从农业部门迁移到工业部门的劳动力数量,S代表城市现有劳动力数量,VU(t)表示一个典型的非熟练工人在工业部门预期实际收入的贴现值,VR(t)并且表示同一个时期内预期农业实际收入的贴现值。F′>0说明随着预期城乡实际收入贴现值差距的扩大,迁移劳动力速度加快。
根据托达罗模型,农民进城的决策是依据预期城乡实际收入贴现值的差距而不是实际差距做出的。托达罗模型对农业劳动力的迁移提出了新的视角和解释,但是该模型仅仅是一个粗线条的理论模型,没有考虑到特定社会、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制度制约因素和个体的不同禀赋。本文将用托达罗模型的思想,结合个体的不同禀赋、转型时期的制度制约因素对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的动因进行更深层次的剖析。
第一,假设我们的研究对象农业劳动力是理性的“经济人”。假定他们有4种行为方案:α0、α1、α2、α3。其中,α0表示完全务农;α1表示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在农村非农产业就业;α2表示城市暂时性转移,进入城市打工若干年,最终返回农村;α3表示城市永久性转移。结合上述托达罗模型的思想:农民进城决策是依据预期城乡实际收入贴现值差的大小做出的,这里我们假设农业劳动力选择上述4种行为方案的动机完全是由预期收益流的贴现值决定的,他们会选择使自己一生获得最大贴现值的行为方案。假设一共有N个时间段,如果以年为时间段的单位,那么N等于他自身的预期寿命减去目前的年龄。
第二,托达罗模型和以往模型的不同之处是假设城市存在失业。就业概率为π(t),表示如下:
上式中,π(t)表示转移出去的农业劳动力在城市中的就业概率;N(t)表示t时期城市就业人口总规模;S(t)表示t时期城市总的劳动力规模;λ表示工业产出增加率;ρ表示劳动生产率(Labor productivity)。托达罗模型中的π(t)反映的是特定社会总的农业劳动力在城市中的就业概率,或者说假设劳动力同质,每个转移动劳动力所面临的共同的就业概率。而实际上,不同的人以及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以及一定的制度约束下都会有不同的就业概率。我们假设t时期农业劳动力预期自己找到非农产业工作的概率pi,t是其个人禀赋、宏观经济因素、制度因素的函数:
pi,t=g(个人禀赋:年龄,教育程度;宏观因素:λ,ρ......,制度因素:双重就业制度)
i=1,表示在农村非农产业;i=2,表示在城市。这里,我们用p′表示在城市正规部门的就业概率。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我们这里进一步做出假设:农民工预期自己的就业概率pi,t是年龄的减函数,是其教育时间长短(包括在职培训等非正规教育)的增函数。
设务农预期农村非农产业收入为y1,在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预期收入为y2,在城市正规部门就业预期为收入y′2。注意,这里假设农民预期其收入时是根据他个人受教育时间长短来预期的,当他受教育时间越长时,他预期自己的收入就越高,反之依然。假设进入城市的劳动力t失去工作,他可以获得失业救济yr,t。如果不能够获得失业救济,那么就意味着yr,t=0。
第三,设农民通过农业生产从土地中得到的经济收益为e。农民也可以选择放弃e,将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出租出去或者彻底转让出去。将土地出租,获得的租金为γ1e,这里γ1表示租金与农业生产收益e的比率。将土地永久转让,获得一个固定的转让费:E。我们假设农民以利率γ2(如果上述时间段以年为单位,这里表示的就是年收益率)去投资E,在每期获得一定的预期资本利得:γ2E。
农村与城市的界定:是否有制度。农业劳动力进入城市受到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的限制。永久性转移与暂时性转移的界定:暂时性转移出去的农业劳动力仍然拥有土地承包权,永久性转移出去的农业劳动力则将土地承包权转让出去,获得收益E。
设农民预期收益函数为Di=H(αi)。假设农民是风险厌恶者,如果预期未来收益不确定性较大,则他会选择较大的贴现率贴现未来预期收益流。我们设务农收益的贴现率为r0,农村非农产业收益的贴现率为r1,城市中务工收益的贴现率为r2。
做出这个选择的农业劳动力是典型的风险厌恶型,他们认为自己的知识技能、精神状态等方面比较差,对城市了解甚少,所以需要非常大的r2来贴现城市务工收入的预期收益流。另外,由于年龄以及文化程度的限制,使他们没有机会得到较少的机会从事农村非农产业。
选择α1的农民,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在非农产业中就业。那么他的预期收益就是:
设当农民忙时务农、闲时务工时,务工时间占农业劳动力年满负荷工作总时间的比重为t′。这些劳动力占有年龄轻与较高的文化素质的优势,使得他们能够获得从事农村非农产业的机会,从而可以显著提高自己的收入。朱农(2002)通过对迁移者与非迁移者的比较中发现,受教育程度较高者反而更倾向于留在农村从事非农工作,其原因可能是,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人可以从事非农业经营或者进入乡镇企业,而这些非农业活动能显著的提高他们的收入。蔡(2007)认为农村具有高中以及以上文化程度者,一般已经占据了较好的农村就业岗位,因而迁移动机教弱。
选择α2的农民,城市暂时性转移。那么他的预期收益就是:
目前,转移到城市的绝大多数农民工都属于这一类。做出这个选择的农民工一般比较年轻,文化素质较低,没有什么特殊技能。转移到城市之后,受到制度的限制和自身素质的原因,进入正规部门工作的概率p′2,t几乎为零。但是,由于目前城乡差距很大,预期y2,t>>et。尤其近几年,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当地的劳动力已经无法满足快速发展的经济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为了吸引更加优秀的劳动力前来工作,出台了很多优惠措施,p2,t比较大。但是,他们工作流动性很强,尤其是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各种社会保障,当他们失去劳动能力时,将完全失去收入。从风险管理的角度看,如果将务农收益et看作一个无风险收益、城市务工收益y2,t看作一个风险收益的话,农民选择暂时性转移到城市就业是在受到制度制约与自身素质限制的双重约束下,在一生中的不同阶段对自己的人力资本在获得无风险收益et和获得风险收益y2,t中分散投资,在获得最大收益的同时有效规避风险的一个理性决策。
选择α3的农民,即城市永久性转移的农民,他的预期收益就是:
目前,这一类农民工比较少。他们是因为特有的技能、较高的学历等特殊因素被城市接纳,到城市正规部门工作,从身份上变为城市人。另外一类虽然暂时身份不被接纳,但是从事经商等工作中得到了相对于从事农业生产高的多的收益,这些收益足以弥补永久留在城市的风险,他们决定永久留在城市。
参考文献:
1、博迪,莫顿.金融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陈晓华,张红宇.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就业[M].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
4、蔡.人口迁移和流动的成因、趋势和政策[J].中国人口科学,1995(2).
篇9
关键词:农场;人力资本;投资模式
Abstract:AccordingtohumancapitaltheoryandtherealityofXinjiangFarmingCorps,humancapitalofXinjiangFarmingCorpscanbeclassifiedintothreetypessuchasgeneraltype,technologicaltypeandbusinessmanagementtype.Basedonthis,thispaperanalyzesanddiscussesgeneralhumancapitalinvestmentmodelintheaspectsofregulareducation,healthandhealth-care,farmingtechniquecultivation,labortransferandsoon.Presenthumancapitalinvestmentmethodandmodelarestillworthdiscussingandtheproblemisthatthehumancapitalinvestmentishigherbutthereturnislowerinthecorps.Thecombinationinvestmentmodelwhichchoosesfavorableinvestmentmodelbasedontherealityofthecorpsaccordingtohumanresourcesvalueandspecialtyofdifferenthumancapitalscansolvethepresentprobleminhigherinvestmentinhumancapitalbutlowerreturn.
Keywords:farm;humancapital;investmentmodel
经济学家们纷纷揭示和论证了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紧密联系,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领悟。现在,人们的目光已经集中到如何形成和提升人力资本这一问题上,因此,结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实际,对农场人力资本投资模式作深入的分析,对促进兵团农场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兵团农场人力资本的类型划分
兵团农场人力资本,从受教育程度和所从事的工作性质、特点等角度分类,可划分为普通型、技术专长型、经营管理型三类。这三类具有由低到高的层次性,便于我们对农场人力资本投资模式进行分析和设计,有利于提升农场人力资本。
1.普通型
普通型农场人力资本是目前兵团农场人力资本中等级最低,最一般的类型,主要是指身体健康,智力健全,具有小学或初中文化水平,能从事一般性农场作业的劳动力。这类人力资本的形成一方面是完全或部分接受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具备了基本的知识文化素质,另一方面,通过家庭式的传、帮、带,从父辈那里获取一定的农场知识和作业技能,并且在自身实践中形成自己的农场技术。这类农场人力资本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自身的身体素质,对体力的要求较高,所以,在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相同的前提下,男性的人力资本存量比女性高得多。在兵团总人口中仅受过初中教育的人口为81.84万,占总人口的33.36%。受过小学教育的人口为76.02万,占30.98%,尚未受过任何正规教育,但基本具备农场生产技能的人口38.09万人,约占16%,三者共同构成兵团普通型人力资本的主体,占兵团总人口的80%以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普通型人力资本应该力争向下面两种类型转化,否则,此类人力资本有可能在残酷的竞争中被淘汰。
2.技术专长型
技术专长型农场人力资本是农场人力资本的“中间型”,是今后大多数农场人力资本的发展方向和基本类型。它主要是指身体素质好,智力较高,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一般为普通高中、职业高中、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从事技能性农场操作的劳动力。这类农场人力资本经过了较高文化层次的培养,具有扎实的知识文化基础,较强的学习能力,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技能型农场人力资本比一般型农场人力资本具备更大优势。在团场具备上述条件的人口约34.83万人,占14.20%。
3.经营管理型
经营管理型农场人力资本是农场人力资本的最高层次,在农场人力资本中不占多数,但他们所起的作用却不可小视,并且他们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也很高。经营管理型农场人力资本是指身体素质好,思维敏捷,逻辑性强,洞察能力强,具有大专以上(少部分人学历较低)文化程度,熟悉农技知识及农村人文知识,有较强的市场观念,具备管理能力,能在农场中从事管理性工作的劳动力。这类农场人力资本具有很高的知识文化水平,善于抓住机遇,能够把握农产品市场的脉搏,能够管理农场企业。兵团农场的各级管理人员基本可以归为此类。
二、农场人力资本投资的一般模式
在农场,人力资本投资模式归结起来有正规教育、卫生保健、培训、迁移等,对这些模式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既可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也可以辅助农场劳动力作出理性的人力资本决策。
1.正规教育的投资和收益分析
秦伟平,汪全勇,石冠锋,刘文霞:新疆建设兵团农场人力资本投资模式探讨正规教育投资分为两种,一种是农村家庭对家庭成员(一般为子女)个体的投入,一种是政府或社会对教育的投入,前者暂且称为“个人投资”,后者暂且称为“社会投资”。正规教育的收益也分为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个人收益包括精神收益和经济收益,精神收益包括教育可以使人的文明程度大大提高,人对职业的选择能力和满足程度大大提高,人对工作、生活、艺术的鉴赏能力大大提高,人更具有责任使命感,人更具有组织性与社会适应性,甚至更深刻地认识人生的意义。经济收益主要是指个人未来较高的经济回报,这种回报不仅是较高的经济收益,而且受教育的人会合理的安排经济支出,会利用科学文化知识更好地保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从而减少医疗费用。另外,受教育程度高的人会有更多的机会更换职业,以取得更多的收入。社会收益主要是指服务于社会的收益和个人不能独自享有的收益部分,如教育带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风气好转等。
从社会投资角度来看,兵团在切实贯彻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同时,积极调整中等教育结构,重点改革高中阶段的教育结构,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和中等成人教育。农牧团场的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特别是职工子女素质,他们知识水平普遍较高,整体素质较好。但是这些子女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不愿意上岗,造成农场人力资本的现实投入很低,严重影响了农场经济的发展。
从个人投资角度来看,农场人力资本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自身的身体素质,对体力的要求较高,青年男子因进行正规教育而放弃的收益即机会成本较女子大,农村男子的增量投资收益率会低于女子的增量投资收益率,由此推出的结论是对男子进行正规教育投资的可能性比对女子进行正规教育投资的可能性要小,但是现实生活中,因种种因素,如重男轻女思想、男女的生理差异对学习的影响等,结果往往是对男子进行正规教育的投资比对女子进行正规教育的投资多。从而表现出个人投资的非理性。
2.健康投资和收益分析
健康投资也可叫做卫生、保健投资,是指一定时期用于预防和治疗人体病变、维护和保持人们身心健康所花费的所有支出。从内容上看,健康投资包括花费在医药、医疗器械、设备及设施、医务人员服务报酬支付,医疗科学技术研究和情报调查等方面的直接费用;也包括用于公共卫生(包括环境、食品、劳动等卫生工作),地方病、寄生虫病、急慢性传染病的大规模防治,以及卫生检疫和卫生宣传方面的间接性费用。健康投资是一种可以为投资带来预期经济收益的生产性投资。
“十五”时期,兵团卫生事业快速发展,对兵团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保障和促进作用进一步加强。居民健康状况明显改善,到2004年,兵团居民人均期望寿命为75.61岁,婴儿死亡率为12.69‰,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15.4‰,孕产妇死亡率0.72‰,各项综合反映国民健康的主要指标均超过了“十五”计划。“十五”时期兵团卫生公共体系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初步搭建起兵团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医疗救治体系、卫生监督体系和疫情网络体系构建,完成了兵团、师、团三级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职能作用明显发挥。
3.农场技能培训的投资效果分析
如果说教育投资、卫生、保健投资对农场人力资本生产主要是一种间接影响,在于形成知识存量和体能存量,那么,农场技能培训的投资往往直接形成能力,具有很强的专业性、鲜明的层次性、显著的实践性和明显的经济性。
在职培训是克服目前农场职工,尤其是外来劳务工素质下降的一个最快捷、最有效的措施。冬季培训是农场长期以来狠抓的一项大规模的在职培训活动,包括劳动局实施的“职业资格”培训、科委开展的“科技之冬”活动以及教委进行的“扫盲”工作。这些活动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对提高了农场人力资本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条块分割,各自为战甚至相互矛盾的局面,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技能培训的整体性。最好是三家联合,统一指挥,以“技术等级”培训为主要形式,以实用生产技能培训为主要内容,开展培训。让职工在学技术、用技术中提高,在学技术、用技术中脱盲,整体上提高培训的质量和效果。
4.“迁移”的投资和收益分析
现有研究表明,迁移新地后的净现值(即新地区期望获得的收益现值减去迁移耗费的成本现值)超过现在地区的收入现值是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基本条件之一。获得预期较大的收益是劳动力迁移的决定性原因。
兵团劳动力的迁移从形式上可以分为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两类。劳动力的就地转移主要表现为农场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的转移。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1980年到2004年,从事农场的职工从占职工总数的65.7%下降到2001年的47.0%,到2004年刚刚恢复到50.5%;而从事工业、建筑业的劳动力比重由22.6%下降到18.7%;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比重由11.7%上升到30.8%。从事种植业的职工下降速度最快,由从业人员总数的64%下降为43.5%。
农场劳动力的异地转移主要表现为农场高素质职工的流失和内地农村地区富余闲散劳动力的涌入。农牧农场35岁以下的青年职工不安心在农场,通过各种途径向内地、城市、沿海地区流动。出现了大量的外出“打工仔”,使农场、连队失去了“顶梁柱”。为了尽快补充农场一线劳动力的严重不足,各师、团、连三级领导也在有计划地从河南、四川、青海等省引进移民和大量的民工补充职工队伍。有的连队60%是新职工,主要由他们来支撑连队地农场生产。
就劳动力个人而言,劳动力迁移是劳动者在预期迁移收入与成本之间作出权衡选择的结果(图1),是一项理性的投资。图1中的E0表示如果劳动力在原居住地继续劳作以后收入趋势;E1则是劳动力作出迁移决策后预期将来收入,劳动力迁移决策以及迁移的欲望的强烈程度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
(1)在C点以后E1曲线的高度表示变换地区后获得的收入量。如果迁移后的收入较大地增加,并随着工龄的延长而提高,必然对劳动力有很强的吸引力;反之,迁移后的收入较少会减弱劳动力的迁移欲望。
(2)迁移后的工作年限长短直接关系到个人总收益量。劳动力个人在较低的工作年龄段就应该寻找最能发挥自身人力资本作用的地区和职业。
(3)图中的ABC点构成的经济损失计入迁移成本。这一成本将对农民的迁移决策造成负面影响,如果这一成本过大,农民将取消迁移决策。因此,为降低成本,一般应在迁移之前作好工作安排,以避免损失。
就农场而言,劳动力引进则属于一种迫不得已的非理。据90年代中期的一次调查显示,在短短几年中,自治区流向内地的科技人员达6000多人,其中兵团占到4000余人,而且绝大多数是从农牧农场走出去的。近些年来,这种情况越演越烈,“老年职工盼退休,中年职工跳龙门,青年职工不上岗”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当相当数量的职工离开农场而去时,大批内地劳动力涌入,这些人大多来自贫困山区,文化素质普遍较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农场生产上劳动力的不足,然而,有技术、懂经营的人走了,没有技术、不懂经营的人来了,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劳动者走了,较低文化素质的劳动者来了,这不同质的一来一去,使兵团农场职工队伍整体素质下降。
三、几点启示
1.高投资低投入
对兵团这样一个农场人口众多、农场人口总体素质偏低的经济体而言,提升农场人力资本可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对于这一点相信大多数人都不会怀疑,关键在于如何提升农场人力资本,探讨农场人力资本投资模式的目的也在于此。但是,我们同时不能忽略一个问题,投资的对象是谁?相对于地方农村,目前农场人力资本的投资范围不可谓不广、投资力度不可谓深,但与农场人力资本高投资相伴随的是越来越多的层次越来越高的人力资本流失。导致农场人力资本高投资低投入的恶性循环。所以,在进一步探讨农场人力资本的有效投资模式之前,必须认真分析对不同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后的现实投入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将会继续导致农场人力资本高投资低投入情况发生。
2.投资模式的选择
农场人力资本的投资途径存在多样性,投资模式存在差异性,这就决定了投资者在作出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时应考虑“两性”,即投资的理性和多元性。所谓理性,就是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前要进行理性分析,不可盲目地跟随他人,要根据农场实际情况进行可行性分析。既然是“投资”,就应该考虑到投资的风险性,要大致计算投资成本和回报利润,其中投资成本应包括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回报利润也并不仅是货币收入,还应包括生活环境改善、个人家庭的心理收益等等,所谓多元性就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渠道很多,要考虑到投资的多元化。正规教育、专业技能培训、卫生保健、迁移等都是人力资本的形成途径,一些人的学历层次不高却能获得较多的收益,正是因为他们通过非正规教育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存量较多。因此,笔者建议要根据兵团不同类型人力资本的价值和独特性以及团场经济条件的实际情况进行投资模式的组合(如图2所示)。
参考文献:
[1]加里·S·贝克尔.人力资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1987.
[2]梅广明.人力资本增值八法[J].人力开发,2002(11).
[3]安应民.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与管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4]李玮,杜健梅.企业培训效果不佳的原因[J].企业管理,2002(7).
[5]杨宣志.培训效果反馈[J].人力资源开发,2002.
[6]陈丽君,沈剑平.人力资本混合雇佣模型理论评述[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2(3).
篇10
关键词: 二元经济结构;人口流动模型;理论内涵;政策含义
一、引言
随着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活动由传统农业生产为主转变为现代工业生产为主,社会的空间组织形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在社会发展初期,社会经济活动主要是传统的农业生产,它是相对土地密集型的,要求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在大量的土地上分散劳动,所以农民只能分散居住。随着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开始转变为工业活动。由于工业部门的生产活动不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既可以在相对分散的空间范围进行,也可以集中在某一区域空间内进行,但是为了节省不同非农产品之间交易带来的交易费用,从事工业生产的人们就会选择居住在某一个区域内,从而形成城市。经济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农业比重不断下降、工业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中主要的一个方面是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因此我们需要人口流动模型来理解这种结构转型。
刘易斯、费景汉和托尼斯、乔根森的二元模型都是建立在充分就业的隐含假设下。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托达罗为首的一批发展经济学家发现,在许多欠发达国家,城市不仅存在失业,并且在存在高失业率的情况下,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依然存在。因此,他们将人口流动理论的研究重点转向了城市失业问题,试图通过建立新的人口流动模型来更好的解释这一现象。在托达罗模型中,预期收益是潜在迁移者选择迁移的重要动机,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他们迁移的动机就越强烈。1997年,本斯温格和斯密在保留哈里斯-托达罗模型主要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存在逆向选择的简单模型,信息不对称导致了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高于农村部门的工资并诱发人口流动、城市失业问题,但是没有失业工人留在城市非正式部门来使城市部门和农村部门的工资相等。卡林顿等人则考虑到早期迁移的人口对尚未迁移的人口提供外部性,建立了一个简单模型进一步研究潜在移民在城市寻找工作、做出移民决策的前瞻性以及移民过程中的选择性等问题。
二、主要的人口流动模型
1刘易斯模型、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乔根森模型
(一)刘易斯模型
第一个人口流动模型是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刘易斯认为,由于在农业部门还不够发达的时候,优先进行了工业化,建立了现代工业部门,因此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即以农业、手工业为主的传统部门与以制造业为主的现代部门并存的社会组织形式。他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存在着大量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二元经济结构的核心问题就是劳动力由农村流向城市。也就是说,通过工业发展,现代部门获得用于资本积累的利润,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转移到城市,诱使产业结构发生改变,工业化、城市化达到一定水平后经济由二元转变为一元。
(二)拉尼斯-费景汉模型
1961年,费景汉和拉尼斯合作发表的论文中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对刘易斯模型做了大大的扩展,把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的关系清楚地表述了出来。在他们的模型中,经济发展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于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且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并不会影响农业部门的总产出,也就不会引起粮食短缺的问题;第二阶段,此时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但其边际生产率不为零,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会降低农业部门的产出,可能会引起粮食短缺的问题,造成农产品与工资的上涨;第三阶段,农业生产部门的边际生产率大于工业生产部门。费景汉和拉尼斯认为农业部门除了提供剩余劳动力还为经济发展提供必须的农产品,工业部门扩张受到抑制的主要原因在于农业部门发展的停滞。由此,他们提出农业和工业平衡发展的思想,认为要避免经济停滞必须保证农业增长的速度可以满足工业部门对农产品的需求。
(三)乔根森模型
乔根森对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假设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农业部门不存在劳动生产率低于实际收入或者为零的剩余劳动力。乔根森在纯粹的新古典主义框架内建立一个不同于刘易斯、也不同于拉尼斯-费景汉模型的二元经济模型。在乔根森模型中,农业剩余是模型的基础和核心。乔根森不认同边际生产力为零的农业剩余劳动,也就否定了在剩余劳动完全转移到工业部门之前工资水平固定的假说。乔根森模型对刘易斯模型有所补充和发展,但是还存在着以下缺陷:首先,乔根森模型忽视了农业物质投资的重要性;其次,乔根森模型中依赖于技术进步的工资率上升需要进一步讨论;最后,乔根森忽视了城市中存在的失业问题。
2托达罗模型 20世纪60年代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发展迅速,在城市存在高失业率的情况下,依然有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传统的人口流动理论隐含了充分就业的前提假定,无法对这一社会现象进行合理的解释,于是托达罗模型应运而生。托达罗在1969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经典论文《欠发达国家劳动力迁移模式和城市失业问题》中首次阐述了对城乡人口流动与城市失业的看法。次年,他又与哈里斯合作在同一期刊发表了《人口流动、失业和发展:两部门分析》,标志着托达罗模型的正式建立。[JP2]
托达罗模型的基本理论假说是:潜在迁移者是否选择迁移在于预期城乡收入差距而不是实际城乡收入差距,只要预期城市收入水平高于农村收入水平,人口流动就不会停止。除此之外,该模型还做了一些与市场结构比较相符的假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两部门经济,即整个经济系统分为农村的传统农业部门和城市的现代工业部门;2)农业部门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即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为正,这意味着人口由农村流向城市的机会成本大于零;3)农村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在农业部门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工资等于使用最后一个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价值;4)由于工会或者政府政策,城市最低工资水平外生决定并且高于市场的出清水平,城市部门中,企业雇佣一定数量的劳动力使得所雇佣的最后一个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价值等于制度工资;5)存在“非正式的部门”,如果城市居民没有找到工作,他们可以在非正式部门维持生计,在模型的推导中假设非正式部门的生产力为零;6)农产品的价格简单地由两部门的相对产量决定,即哪个部门的产品相对少,其产品的相对价格就越高。
托达罗模型首次将城市失业问题作为分析的前提和目的,认为在发展中国家过于重视工业部门,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过快发展会扩大城乡预期收入差距,进而加剧城市失业问题。只有加强传统农业部门的发展,才能解决城乡预期收入过大带来的城市失业问题。
3本斯温格和斯密的模型
在传统的托达罗模型中,“制度所决定的”城市实际工资高于农村部门的工资水平,导致了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并诱使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最后使得城市部门出现失业问题。但是托达罗模型的工资刚性假设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于是,本斯温格和斯密在保留托达罗模型主要特点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简单的逆向选择模型,试图通过该模型说明工业部门具有较高的工资水平以及出现城市失业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中存在着雇主和雇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与托达罗模型一样,潜在移民者根据预期收入决定是在农村部门还是在城市部门工作。通过建立逆向选择模型,他们得到了与托达罗模型相同的结果,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高于农村部门的工资,并进一步得到了如下结论:城市失业问题是潜在移民对劳动力市场上的逆向选择作出反应的结果;城市的人口规模取决于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工业部门会雇用工人直到边生产力等于工资水平,如果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提高了,企业雇用的工人和非正式部门的工人的数量将会上升。
4卡林顿等人的模型
通过对美国南部黑人迁往北方的“大迁徙浪潮”的研究,卡林顿等人发现,在南北战争数十年后,尽管南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差距,但是黑人并没有由南向北迁移,直到20世纪初,南方黑人开始往北方迁移,并且迁移很快开始加速,尽管此时的南北收入差距较以前已经缩小了。传统人口流动模型能够解释劳动力最终流入相对富裕的地区,但却无法合理解释在这个迁移过程中的时间选择和迁移加速的问题。因此,卡林顿等人建立了一个动态迁移理论模型深入研究人口流动过程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寻找工作的过程、潜在移民对在城市和农村居住的未来预期以及潜在移民基于预期的选择问题。[JP2]
从理论上来说,人们根据预期城乡收入差距决定是否向城市迁移,不同的人对预期收入的贴现值不一样,通常情况下,具有低迁移成本的年轻人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贴现值相对较高,因此他们会首先从农村流向城市。先迁入城市的这部分移民又会对后来移民者产生正的外部效应,首先,先迁入移民可以为后迁入移民提供有关生活以及工作方面的信息,这为后来的迁移者降低了迁移成本与找工作的难度;其次,由于城市中已经有了很多移民,他们已经为后来迁移者创造了相对较好的社会环境,使得后来者可以更快地适应城市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最后,城市中已有移民所组建的社区可以将新移民者推荐给潜在的雇主和放贷人。因此,卡林顿等人建立的模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迁移一旦开始便会形成某种势头,尽管收入差距开始缩小,迁移也会持续进行甚至开始加速;迁移先由迁移成本较低的人开始,但是后来的迁移者会有较高的迁移成本;由人口流动引起的劳动力重新配置不仅将导致农村并将导致整个经济中的人均收入增长。
三、简要评述
[JP2]
相关期刊
精品范文
10劳动实践过程